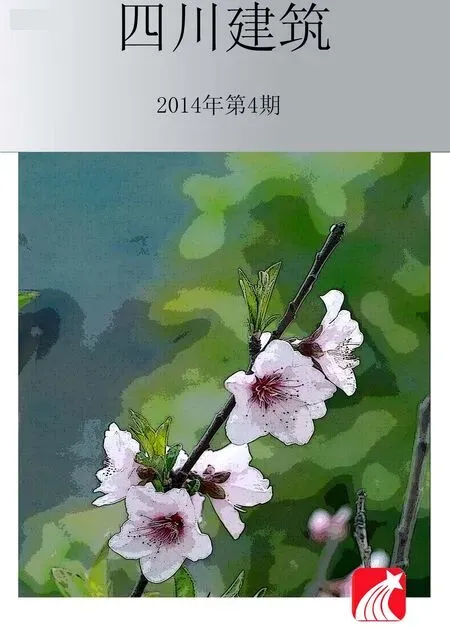淺析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結(jié)構(gòu)參數(shù)的影響
王 豐
(重慶市市政設(shè)計(jì)研究院,重慶 400020)
1 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簡(jiǎn)介
門架式雙排抗滑樁是從20世紀(jì)50年代開始研究的一種支擋結(jié)構(gòu)。他是在滑坡地段的適當(dāng)位置設(shè)置前、后兩排鋼筋混凝土樁,并在樁頂用剛性連梁把前、后兩排樁聯(lián)結(jié)起來,形成一種雙排支護(hù)的空間結(jié)構(gòu),其形狀與傳統(tǒng)的門框相似,所以稱為門架式雙排抗滑樁[1],結(jié)構(gòu)形式如圖1。

圖1 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示意
該結(jié)構(gòu)為一空間結(jié)構(gòu),可以不需要內(nèi)支撐(如錨桿等),僅靠自身的空間組合效應(yīng)來抵抗滑坡推力;在滑坡推力的作用下,后排樁向滑坡前緣運(yùn)動(dòng),由于結(jié)構(gòu)自身的空間性,將使得樁間土體受壓縮;因此后排樁就要受到樁間土體的抗力作用,而前排樁也將受到由樁間土體傳遞的滑坡推力作用;前排樁埋入穩(wěn)定基層中,通過穩(wěn)定基層提供的抗力來維持樁體的穩(wěn)定。
2 計(jì)算模型
為了更好的模擬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的受力機(jī)理,本文在傳統(tǒng)的平面剛架模型[2]、平面桿系模型[3]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一種新的計(jì)算模型,如圖2所示。

圖2 門架式雙排抗滑樁有限元模型
該模型將前后排樁嵌入穩(wěn)定基層中,利用接觸單元來模擬滑動(dòng)面以下樁—土之間的相互作用,利用彈簧模擬滑動(dòng)面以上的土體對(duì)前后排樁的作用,利用等參四邊形單元模擬穩(wěn)定基層的土體,利用梁?jiǎn)卧M門架式雙排抗滑樁,從而分析門架式雙排抗滑樁在滑坡推力作用下的變形,確定其合理的結(jié)構(gòu)形式。
為了更好的模擬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的受力情況,針對(duì)該模型提出以下假定:
(1) 假定滑動(dòng)面為平面;
(2)連梁和前后排樁剛性連結(jié),但連梁不是絕對(duì)剛體,可以發(fā)生變形但不發(fā)生轉(zhuǎn)動(dòng)。
3 結(jié)構(gòu)參數(shù)影響分析
根據(jù)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的結(jié)構(gòu)特性,本文認(rèn)為影響其結(jié)構(gòu)受力的主要參數(shù)有排距、連梁的剛度以及樁間土的作用。本文將利用有限元模型及軟件,結(jié)合工程算例對(duì)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的結(jié)構(gòu)參數(shù)影響進(jìn)行分析。
工程算例:
(1) 土的指標(biāo):滑體為碎、塊石土的堆積層,自上而下變形增大,φ1=25°,γ1=21kN/m3, 滑動(dòng)面以下的滑床為密實(shí)黏土層c=20kPa,φ=25°,泊松比μ=0.3,重度γ=19.0kN/m3,變形模量E=10MPa。
(2) 樁體采用C30鋼筋混凝土,彈性模量E=3×104MPa,樁長22m,其中受荷段h1=12.0m,錨固段h2=10.0m,樁間距(中至中)L=6m,樁的截面尺寸b×h=2m×2.5m,梁長度可以變化。

3.1 排距對(duì)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的影響
排距是指前后排樁形心主軸之間的距離,合理的排距不僅關(guān)系著支擋效果,而且直接影響著工程造價(jià)。本文將利用計(jì)算模型,在保持結(jié)構(gòu)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取排距分別為1.5d、2d、2.5d、3d、4d、5d、6d、7d、8d(d表示樁徑,若樁為矩形樁則為短邊長度)進(jìn)行分析;通過計(jì)算,其前后排樁樁身的最大位移、彎矩如表1、表2所示。

表1 前后排樁最大位移Smax mm

表2 前后排樁最大正負(fù)彎矩Mmax kN·m
由表1可知,隨著排距的增大,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的整體位移呈先減小后增大的趨勢(shì)。當(dāng)排距在1.5d~2.5d時(shí),前后排樁的最大位移隨著排距的增大而急劇減小;當(dāng)排距在2.5d~5d時(shí),前后排樁的最大位移值隨著排距的增大也逐漸減小,但減小速率較慢;以前排樁為例,從表1可以看出,當(dāng)排距由1.5d增大到2.5d時(shí),樁體的最大位移由25.01mm減小為19.95mm,最大位移減小了5.06mm,減小速率為20.2%;當(dāng)排距在2.5d~5d時(shí),樁體的最大位移由19.95mm減小到19.07mm,最大位移減小了0.88mm,減小量可以忽略;當(dāng)排距在5d~8d時(shí),門架式雙排抗滑樁前后排樁的最大位移又逐漸增大,但增加的趨勢(shì)較緩。以前排樁為例,從表1可以看出,當(dāng)排距由5d增加到8d時(shí),前排樁的最大位移由19.07mm增加到19.72mm,增加了0.65mm。
此外,將門架式雙排抗滑樁換算成等截面的普通抗滑樁,其他條件不變,得到普通抗滑樁的受力情況。當(dāng)排距為1.5d時(shí),前后排樁的最大位移基本相同,其值為25.1mm;而普通抗滑樁的最大位移為48.1mm,此時(shí)的門架式雙排抗滑樁基本上就相當(dāng)于將兩根普通抗滑樁疊加在一起共同抵抗滑坡推力;隨著排距的增大,門架式雙排樁的整體位移又逐漸減小,前后排樁之間的最大位移也將有所不同,此時(shí)的門架式雙排抗滑樁又不是簡(jiǎn)單的將普通抗滑樁疊加在一起;由于連梁的存在,門架式雙排抗滑樁又具有了一定的空間性,結(jié)構(gòu)的整體剛度增大,其結(jié)構(gòu)的最大位移將遠(yuǎn)小于普通抗滑樁。
綜上,當(dāng)排距約小于1.5d時(shí),門架式雙排抗滑樁就相當(dāng)于將兩根普通抗滑樁簡(jiǎn)單的疊加在一起而承受滑坡推力的作用;隨著排距的增大,其結(jié)構(gòu)自身的空間性也逐漸體現(xiàn)出來。當(dāng)排距大于1.5d時(shí),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結(jié)構(gòu)具有一定的空間性,樁身的最大位移逐漸減小,當(dāng)排距在2.5d~5d時(shí),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的樁身位移最小,樁身位移的變化趨勢(shì)不明顯,其結(jié)構(gòu)的空間性最好;當(dāng)排距大于5d時(shí),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的空間性將隨著排距的增大而逐漸減弱。
由表2可知,當(dāng)排距約小于1.5d時(shí),前排樁的最大正彎矩大于后排樁,而當(dāng)排距大于1.5d時(shí),后排樁的最大正彎矩大于前排樁;造成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結(jié)構(gòu)自身的空間性,當(dāng)排距大于1.5d時(shí),后排樁主要承受抗拔力,而前排樁主要承受抗壓;而后排樁的最大負(fù)彎矩大于前排樁。當(dāng)排距約小于3d時(shí),前后排樁的最大正彎矩變化較快,而前后排樁的最大負(fù)彎矩變化相對(duì)較慢;當(dāng)排距大于3d時(shí),前后排樁的最大正負(fù)彎矩變化均較慢。此外,從表2還可以看出,前排樁的最大正負(fù)彎矩隨著排距的增大而逐漸減小;后排樁的最大正負(fù)彎矩隨著排距的增大而逐漸增大。
同時(shí),利用ANSYS分析樁體兩側(cè)的土壓力的分布情況說明:當(dāng)排距大于2.5d~5d時(shí),前后排樁體受到的土壓力比較合理,但當(dāng)排距大于6d時(shí),前后排樁的最大位移又將隨著排距的增大而增大。
綜合前、后排樁的最大水平位移和最大正、負(fù)彎矩的對(duì)比可以發(fā)現(xiàn),樁體的最大水平位移發(fā)生在后排樁,且排距大于2.5d時(shí),前后排樁的位移變化較緩,且前后排樁的位移相差較小,這樣能充分發(fā)揮前后排樁的材料性能;當(dāng)排距為5d時(shí),前后排樁的最大位移取最小值;同時(shí)當(dāng)排距在(3~5)d時(shí),前后排樁的負(fù)彎矩相對(duì)較小,工程造價(jià)相對(duì)較低。因此,通過對(duì)比分析,當(dāng)排距為(2.5~5)d時(shí),門架式雙排抗滑樁自身結(jié)構(gòu)的空間性較好,能充分發(fā)揮其結(jié)構(gòu)的優(yōu)點(diǎn);從經(jīng)濟(jì)和安全角度考慮,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的排距一般為(2.5~5)d。
3.2 連梁剛度對(duì)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的影響
連梁是指將前后排樁聯(lián)結(jié)起來的樁頂橫梁,它和前后排樁組成一空間結(jié)構(gòu),因此具有很大的剛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對(duì)前后排樁的受力進(jìn)行調(diào)整,減小樁頂位移;實(shí)踐證明[4],門架式雙排抗滑樁和連梁之間存在著良好的協(xié)同工作能力,在協(xié)同工作下,能使前后排樁充分參與工作并提高整個(gè)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性和安全性。本文將利用計(jì)算模型,在保持結(jié)構(gòu)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根據(jù)算例取排距為4d,連梁剛度分別為0.25EI、0.5EI、1.5EI、2EI、2.5EI、3EI、4EI來進(jìn)行分析。通過計(jì)算,其前后排樁樁身的最大位移、彎矩如表3、表4所示。

表3 前后排樁最大位移Smax mm

表3 前后排樁最大正負(fù)彎矩Mmax kN·m
由表3可知,隨著連梁剛度的增大,前后排樁的最大位移逐漸增小;當(dāng)剛度小于1.0EI時(shí),減小速率較快,當(dāng)剛度大于1.0EI時(shí),減小速率較慢。以后排樁為例,從表3可以看出,當(dāng)連梁剛度由0.25EI增大到1.0EI時(shí),樁身的最大位移由24.23mm減小為19.43mm,減小了4.8mm;當(dāng)連梁剛度由EI增大到2EI時(shí),樁身的最大位移則由19.43mm減小為18.48mm,減小了0.95mm;從這可以看出,當(dāng)連梁的剛度大于1.0EI時(shí),其值的變化對(duì)后排樁樁身位移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jì)。
由表4可知,后排樁的最大正負(fù)彎矩隨著連梁剛度的增大而減小,前排樁的最大正負(fù)彎矩隨著連梁剛度的增大而增大;當(dāng)連梁剛度小于1.0EI時(shí),前后排樁的最大正負(fù)彎矩變化都比較明顯,而當(dāng)剛度大于EI時(shí),其變化趨勢(shì)逐漸減慢。以后排樁的最大正彎矩為例,當(dāng)連梁剛度由0.25EI變?yōu)?.0EI時(shí),其最大正彎矩由25 789kN·m減小為23 964kN·m,減小了1 825kN·m;當(dāng)連梁剛度由1.0EI變?yōu)?EI時(shí),其最大正彎矩由23 964kN·m減小為22 377kN·m,減小了1 587kN·m。
綜上,當(dāng)連梁剛度大于1.0EI時(shí),其剛度的變化對(duì)樁身位移和彎矩的影響都不明顯,在工程中,并不是連梁的剛度越大,其樁身位移和彎矩就越小,一味的提高連梁剛度只會(huì)造成資源的浪費(fèi);從設(shè)計(jì)和施工角度來說,為了考慮安全和經(jīng)濟(jì)的因素,本文認(rèn)為連梁剛度、截面尺寸應(yīng)和樁身一致。
3.3 樁間土的作用對(duì)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的影響
門架式雙排抗滑樁樁間土通過與前后排樁的位移協(xié)調(diào)影響土壓力在前后排樁間的分配,進(jìn)而影響前后排樁共同工作的能力。本文將采用土彈簧來模擬樁間土的作用,通過改變土體的變形模量來改變土彈簧的剛度,從而分析樁間土對(duì)前后排樁的作用。本文將利用計(jì)算模型,在保持結(jié)構(gòu)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取排距為4d,樁間土的變形模量分別為5MPa、10MPa、15MPa、20MPa來進(jìn)行分析。通過計(jì)算,其前后排樁樁身的最大位移、彎矩如表5、表6所示。

表5 前后排樁最大位移Smax mm

表6 前后排樁最大正負(fù)彎矩Mmax kN·m
由表5可知,當(dāng)樁間土的壓縮模量由5MPa變?yōu)?0MPa時(shí),前后排樁身位移變化比較明顯,當(dāng)樁間土的壓縮模量由10MPa變?yōu)?0MPa時(shí),樁身位移變化不明顯。以后排樁為例,當(dāng)樁間土的壓縮模量由5MPa變?yōu)?0MPa時(shí),后排樁的最大位移由21.28mm變?yōu)?9.43mm,減小了1.85mm;當(dāng)樁間土的壓縮模量由10MPa變?yōu)?0MPa時(shí),后排樁的最大位移由19.43mm減小為18.69mm,減小了0.74mm。
由表6可知,隨著樁間土的壓縮模量逐漸增大,后排樁的正負(fù)彎矩逐漸增大,而前排樁的正負(fù)彎矩逐漸減小,表明當(dāng)改變樁間土的壓縮性可以改變樁間土對(duì)前后排樁的作用。
在設(shè)計(jì)過程中,若忽略滑動(dòng)面以上的樁間土作用,則門架式雙排抗滑樁的有限元模型變?yōu)閳D3所示。
經(jīng)計(jì)算分析,若忽略滑動(dòng)面以上的樁間土作用,將使前后排樁的位移稍大于考慮樁間土作用時(shí)的情況。從而說明門架式雙排抗滑樁滑動(dòng)面以上的樁間土體對(duì)前后排樁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前后排樁的樁身位移變化并不大;若忽略其對(duì)前后排樁的作用,則既可以簡(jiǎn)化設(shè)計(jì)過程,又對(duì)最后的計(jì) 個(gè)排序基本一致。通過工程實(shí)例分析,驗(yàn)證了所編制的事故樹的合理性。
3.3 主要影響因素和相應(yīng)的改善措施
(1)X5(溶洞填充沉積大量介質(zhì))、X10(地表水有較好的條件下滲)、X9(與暗河連通,補(bǔ)給范圍廣)等都屬于不良地質(zhì)條件,要降低其對(duì)工程施工的影響,應(yīng)加強(qiáng)地質(zhì)勘探和超前預(yù)測(cè)預(yù)報(bào)工作,爭(zhēng)取對(duì)前方地質(zhì)情況有較詳細(xì)的了解。
(2)X1(施工組織混亂)、X2(超前預(yù)測(cè)預(yù)報(bào)存在盲區(qū)、X3(注漿加固方案存在缺陷)等應(yīng)加強(qiáng)施工人員的培訓(xùn)和管理,增強(qiáng)安全意識(shí),及時(shí)監(jiān)測(cè)和支護(hù)。
4 結(jié)論
通過以上對(duì)隧道突水突泥的事故樹分析,可得出如下的結(jié)論:
(1)巖溶隧道突水突泥發(fā)生的原因復(fù)雜,影響事故的因素眾多,通過一般方法難以對(duì)導(dǎo)致突水突泥的各種因素及其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做出系統(tǒng)的闡述。直觀、邏輯性強(qiáng)的事故樹是分析隧道突水突泥事故比較有效的方法。
(2)隧道突水突泥事故樹中考慮17個(gè)基本事件,通過對(duì)事故樹進(jìn)行定性分析,明確了事故發(fā)生的主要潛在因素,并對(duì)相關(guān)影響因素進(jìn)行重要度排序。最后結(jié)合工程實(shí)例,統(tǒng)計(jì)出各基本事件發(fā)生的概率,求出各基本事件的概率重要度和臨界重要度,使相關(guān)的分析更加準(zhǔn)確和可信,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議和改進(jìn)的措施。
[1] 周建昆.巖石公路隧道塌方風(fēng)險(xiǎn)事故樹分析[J].地下空間與工程學(xué)報(bào),2008,(12):991-998
[2] 孫偉亮.棋盤石隧道溶洞突水成因分析及技術(shù)處理措施[J].鐵道建筑,2010,(10):54-56
[3] 王雙龍.八卦山隧道突水突泥段處理技術(shù)[J].山西交通科技,2009,(4):54-60
[4] 曾強(qiáng)云.宜萬鐵路馬鹿菁隧道水文地質(zhì)分析及涌水預(yù)警[J].土工基礎(chǔ),2012,(4):35-37
[5] 仇海生,楊春麗.煤礦水災(zāi)的事故樹分析法[J].煤礦安全,2008,(6):126-128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shè)部.地鐵及地下工程建設(shè)風(fēng)險(xiǎn)管理指南[M].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