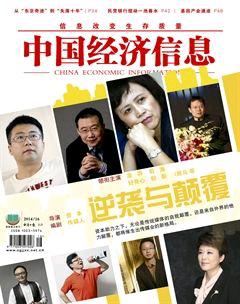從“東京奇跡”到“失落十年”
陳杰

政府指導促進了日本的產業轉型,卻未能有效防止資產泡沫。
從1894年到2014年,120年兩個甲子,中日兩國間的恩怨糾葛從未如此激烈。時至今日,再回首這一個多世紀,我們卻可在歷史迷霧之下,看到隱隱脈絡浮現。拋卻戰爭與和平的周期律,日本從革新自強到自我毀滅,又從廢墟中昂然成長的歷程,不吝是我輩的最佳鏡鑒。而這其中,1954年的甲午年再到2014年的甲午年,又是日本經濟最具解剖意義的六十年。
貿易保護與產業升級
在上世紀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日本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目的是扶植國內新興產業。早在1950年5月,日本政府分布布《外資法》授權政府成立外資委員會,對外國投資者進行審查,后來,這一權力轉移到了通產官僚佐橋滋掌握下的通產省企業局。他謹慎地注意外資引進,對外資在日本設立制造廠進行嚴格審批,鼓勵引進技術而不是制造好的成品,特別是那些會和國內產品形成競爭的制成品。
人們稱佐橋為死硬的排外派。他用“行政指導”的方式手把手地告訴企業該怎么做,他想盡一切辦法把外國大企業排斥在國內市場外,通產省不允許外國人在合資企業中占據50%以上股份,未經通產省首肯外國公司不得購買日本企業,限制外國人在日本公司董事會的人數和投票權。佐橋的強硬在IBM專利事件中令日本大獲其利,當時,IBM掌握著計算機技術的全部基礎專利,佐橋滋直接告訴IBM:“除非你們授權日本公司使用專利,并收取不超過5%的使用費,否則我們會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你們在日本的成功。”這句話迫使IBM不得不接受了通產省的條件,把計算機生產轉移到日本國內。而佐橋為了和IBM競爭,在1961年又以日本開發銀行注資的形式成立了一家日本計算機公司,任命前商工省官員為社長。
另外,汽車工業、石油化學工業、精密機器工業等當時的新興產業在日本的發展也受益于通產省“貿易壁壘”的嚴密保護。按通產省的觀點,產業結構調整就是努力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為技術密集型產業,著力發展石油化學、汽車、金屬、機械、電力、半導體等新興產業,“以投資帶動投資”,比如要發展石油工業,必然需要廠房和設備,那建筑和機械行業就會被連鎖帶動,要運輸產品,管道和重型汽車行業也會被帶動,再擴展開去就是電力、橡膠、煤炭等一大批產業的振興,這種以新興產業為引領呈現連鎖化發展的模式就是日本經濟在60年代實現高速增長的秘密。
與此相伴的就是出口結構的調整,在50年代后期,日本的外匯預算有20%是花在原棉和羊毛進口上,同時大量出口纖維制品。由于日本和美國的特殊經濟關系,日本的纖維制品大量出售到美國,1960年開始,美國決定對廉價的日本制衣服下手,要求限制日本紡織品進口,優先購買美國制品。此舉引起日本和美國的第一輪貿易摩擦,“一美元一件襯衫”的廉價出口戰略遭到嚴重打擊。日本人立刻認識到,單純依靠紡織業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出口大頭不現實,經濟發展歸根到底還得重視新興行業。很快,日本汽車、石油化工制品等新出口熱點就開始取代廉價襯衫,日本公司也開始轉向技術出口。
貿易保護政策為初起的日本企業提供了一套防波堤,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企業得以順利崛起,到60年代中期,以貿易保護和產業扶植為理念的通產省“民族派”凋落,通產省在完成經濟騰飛筑基任務以后結束了一個時期的歷史使命。1964年4月,日本經濟自由化率達到92%,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理事國之一并且加入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為先進國家的一員。通產省此前一度擔心在貿易自由化擴大后國內工業遭到巨大沖擊,但該現象其實并沒有出現。
“證券不況”到“廣場協議”
日本經濟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快速增長后,于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下滑,其后進入“失落的十年”。重新拉動經濟增長就成為日本政府反復嘗試且至今始終不得其解的課題。盡管現任政府大玩“安倍經濟學”,試圖推動數字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并似乎初見成效,但其深層次問題和趨勢并未得到扭轉,“少子高齡化”的陰影揮之不去。
實際上,日本經濟的下滑,癥結就出在金融和地產市場。金融市場的問題其實在60年代已經開始,在1964-1965年期間,日本就出現了一次短暫的經濟危機,稱為“證券不況”。這乃是經濟過熱帶來的副作用,隨著池田內閣“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逐步實現,老百姓口袋里閑錢多了,證券股票市場突然熱鬧了起來,1961年,證券市場的投資總額較四年前已經增長了10倍。這其實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因為證券市場說穿了是經濟的一張晴雨表,企業發行股票其實就是一種募集資金的方式,股票交易額的高低,歸根到底和企業的經營狀況密切相關,但又很容易受市場的影響。過多熱錢的涌入可能把一些本身沒有那么好的經營狀況的企業股票炒熱,這時,某些企業看到有利可圖,就會過多地發行股票。一旦經濟景氣過去,一些碰到經營困難的企業就很可能因為之前的大肆發行股票而負上重債導致破產。
1965年,山陽特殊制鋼就因為負債500億日元被迫申請破產,這家日本特種制鋼的大型企業在奧運會期間由于建筑用材的大量需求,在證券市場上募集大量資金投入到特種制鋼行業里。奧運會結束后,建筑用材的需求量立刻減少,山陽特殊制鋼這才發現他們出現了大量的生產過剩,為了維持股票價格,他們又在年度決算表上做手腳,試圖掩蓋企業經營的問題。直到企業無法支持以至破產后,這一問題被揭露出來,從社長以下的7名公司干部因為違反《證券取引法》以金融欺詐罪被逮捕,有14名公司職員被要求負責并賠償14億日元,引發了戰后日本金額最大的企業破產案。
而從50年代開始的日美貿易摩擦使日本與美國的經濟關系更進一步緊張,美國把日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歸結為日元價格不夠高,要求日元升值。在1985年要求日本簽訂《廣場協議》,這一協議將美元兌日元由當時的1:250上升到1:200,使得日本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遭到重大損失。出于救市的需要,日本政府調低利率,這一政府導向使更多的熱錢涌入了國內證券和地產市場,特別是政府主導的地方基礎建設和都市開發計劃,以及日本國鐵民營化以后為平衡收支大量拋售地產,日本的地產股票市場在80年代被瘋狂炒熱,隨后在90年代嘗到了泡沫破裂的苦果。
與此同時,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企業得以用“廉價資金”大舉進行海外投資,隨后卻在亞洲金融風暴中損失慘重。而始于20世紀末的信息技術革命中,日本的硬件廠商雖然由于其深厚的電子工業底蘊而在零部件方面仍處供應鏈前端,但其軟件和互聯網行業卻徹底被美國乃至拋在了身后。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日本各傳統電子巨頭經營紛紛告急,更是凸顯其產業升級困境。
近年來日本國內政治勢力日趨右傾化,試圖重整軍備,與其國內經濟上的困境不無關系。站在今日回望過去,在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之時,吸取對手的教訓對我們的未來意義匪淺。
(作者系日本史普及作者,著有《幕府時代》、《明治維新:改變日本的五十年》、《日本味兒》等著作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