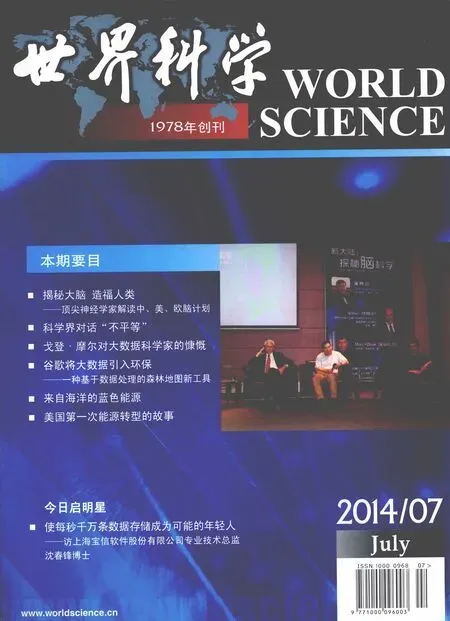疾病預(yù)防:未雨綢繆
邢鴻飛/編譯

某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大腦(右)比正常的大腦萎縮更快
●關(guān)注風(fēng)險(xiǎn)因素和警告信號可能避免一些精神分裂癥的發(fā)作,或者,至少能讓人們更好地應(yīng)對未來。
和所有的母親一樣,法雷爾·亞德里安(Farrell Adrian)擔(dān)心她的孩子,馬特。馬特原本是個(gè)快樂、討人喜歡的男孩,但在五歲的時(shí)候卻表現(xiàn)出異常的難過,當(dāng)時(shí)他的父親離開了家。在學(xué)校里,他出現(xiàn)了思考和注意力方面的問題,十幾歲的時(shí)候變得憂郁,并吸毒上癮。此后,法雷爾帶著孩子去看心理醫(yī)生和其他的各類專家,希望醫(yī)生們能解決她認(rèn)為的父子關(guān)系的情感問題,這樣老馬特或許會回來。
馬特17歲的時(shí)候,被確診為精神分裂癥。二十年的時(shí)間里,生活顛簸不定,住院、治療,服用各種抗精神病藥物。馬特獨(dú)自一人居住在西雅圖,在一家露天足球場有一份兼職工作,離家很近。盡管耗費(fèi)了十幾年才弄明白到底哪里出了問題,法雷爾表示她還是覺得挺幸運(yùn),她說:“我們比其他很多人更早得到救助。”
一些研究者日前提議,只要對在精神疾病出現(xiàn)前數(shù)月甚至數(shù)年前就顯現(xiàn)出來的癥狀引起警覺的話,其他患者也可以盡早得到救治。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針對早期出現(xiàn)的隱性信號進(jìn)行治療,可以減少一半的病人,防止他們之后的疾病發(fā)作。研究者們也一直在尋求大腦、血液和唾液中出現(xiàn)的更具體的危險(xiǎn)信號,以更準(zhǔn)確地識別潛在的危險(xiǎn)。先發(fā)制人的治療可以延緩甚至避免精神分裂癥的發(fā)生,并將精神病療法引入預(yù)防醫(yī)學(xué)領(lǐng)域。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xué)精神病學(xué)家帕特里克·麥戈里(Patrick McGorry)提倡早期干預(yù),他說,“傳統(tǒng)的精神病治療法實(shí)施得太遲,效果甚微。但目前我們明白,解決精神病的方式對于干預(yù)的敏感度比我們以往認(rèn)為的要強(qiáng)得多。”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xué)精神病學(xué)專家、美國精神病學(xué)會會長杰弗里·利伯曼(Jeffrey Lieberman)認(rèn)為,如果找到更優(yōu)的危險(xiǎn)預(yù)測因子,小型治療試驗(yàn)的成功能大規(guī)模復(fù)制的話,干預(yù)治療有可能成為精神病學(xué)中的公認(rèn)的做法。他說:“那么,這有可能會是一次大轉(zhuǎn)折,將改變游戲規(guī)則,降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負(fù)擔(dān),以及他們的家庭和社會的負(fù)擔(dān)。”
精神病的萌芽
逃避精神分裂癥并非是個(gè)新鮮主意。流行病學(xué)研究已經(jīng)明確了環(huán)境風(fēng)險(xiǎn)因素,會在大腦發(fā)育早期出現(xiàn)問題,從而后期轉(zhuǎn)發(fā)成精神分裂癥。例如,改善營養(yǎng),懷孕期間避免感染可以防止一些疾病的發(fā)生;研究人員正在考慮在幼年時(shí)期攝取適量的維生素D是否有可能減少患精神分裂癥的風(fēng)險(xiǎn)。即使已經(jīng)患上了該疾病,第一階段的精神病發(fā)作后的早期治療可以控制疾病的惡化,并增加治愈的機(jī)率。
澳大利亞布里斯班昆士蘭大學(xué)流行病學(xué)家約翰·麥格拉(John McGrath)和其他人考慮在早期治療方面再向前推進(jìn),提出在精神病初露苗頭的時(shí)候就進(jìn)行干預(yù)。一個(gè)人可能變得疑神疑鬼,或者開始出現(xiàn)幻聽,但仍然承認(rèn)這些并非事實(shí)。他們可能背離朋友和家庭,或者不好好上學(xué)上班。所謂的“有風(fēng)險(xiǎn)”類型的標(biāo)準(zhǔn),不同的科學(xué)家們之間略有差別,但有一點(diǎn)相同,就是一個(gè)人極度沮喪,各種癥狀均顯示他必須要獲得幫助。
這一高風(fēng)險(xiǎn)人群中有三分之一在三年左右出現(xiàn)精神病,大多數(shù)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高風(fēng)險(xiǎn)人群的另一個(gè)版本,叫做輕微精神病綜合征(APS),一度被人們考慮是否可以作為一種新的診斷結(jié)果,列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tǒng)計(jì)手冊》最新的第五版中。該手冊是心理疾病方面被業(yè)內(nèi)最廣泛使用的目錄指南。然而,多數(shù)患有APS的人并不一定會發(fā)展成真正的精神病,因此經(jīng)過一番討論,該病征并未被列入該手冊中。
盡管在診斷方面還有很多不確定性,被認(rèn)為有精神病風(fēng)險(xiǎn)的人們主要看他們大腦中反映出來的行為標(biāo)記的脆弱程度。例如,有人認(rèn)為,大腦中被稱作紋狀體部分的化學(xué)遞質(zhì)多巴胺如果過量,會促進(jìn)精神病的發(fā)作。2011年一項(xiàng)研究發(fā)現(xiàn),與健康組相對比,有精神病風(fēng)險(xiǎn)的人紋狀體中多巴胺過量,而含量最高的人在接下來三年中患病的風(fēng)險(xiǎn)也最大。其他研究發(fā)現(xiàn),有風(fēng)險(xiǎn)的人的前額皮質(zhì),即大腦的監(jiān)管中心,在老齡化過程中比一般情況下收縮地更明顯,盡管這一程度不及精神分裂癥患者。
耶魯大學(xué)神經(jīng)科學(xué)家蒂龍·坎農(nóng) (Tyrone Cannon)曾經(jīng)主持過對大腦前額皮質(zhì)的研究。他說:“我們認(rèn)為我們正在探索和研究精神分裂癥過程一樣的早期的、顯著的指標(biāo)。”
實(shí)驗(yàn)療法
迄今為止,11項(xiàng)隨機(jī)的對照實(shí)驗(yàn)發(fā)現(xiàn),治療高風(fēng)險(xiǎn)人群在一年中會減少出現(xiàn)精神病的幾率。多數(shù)情況下,實(shí)驗(yàn)規(guī)模較小,檢測一些干預(yù)手段,比如低劑量的抗精神病藥物、認(rèn)知行為治療(CBT),以及歐米伽-3脂肪酸補(bǔ)劑。
出生風(fēng)險(xiǎn):母體內(nèi)的預(yù)防
精神分裂癥的發(fā)病率約為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對一部分人的影響力遠(yuǎn)超過對其他人。例如,冬天出生的人患精神分裂癥的幾率比夏天出生的人高。住在北方國家的深膚色的人患病的幾率是淺膚色人的三到四倍。澳大利亞布里斯班的昆士蘭大學(xué)流行病學(xué)家約翰﹒麥格拉(John McGrath)說,“這些線索表明,肯定有可變的風(fēng)險(xiǎn)因素支撐那些梯度,而且我們需要弄清楚它們究竟是什么。”
麥格拉一直在研究深膚色移民,他提出的假設(shè)是,他們更高的風(fēng)險(xiǎn)是由于缺乏維生素D所造成的,而維生素D對于大腦正常發(fā)育非常重要,但在北部國家居住的深膚色人群往往缺乏維生素D。他發(fā)現(xiàn),在丹麥,出生時(shí)維生素D的異常水平與精神分裂癥的高發(fā)率息息相關(guān)。麥格拉認(rèn)為,如果目前正在進(jìn)行的一項(xiàng)更大的研究能夠證實(shí)這一關(guān)聯(lián),那么監(jiān)控維生素D的含量就值得去做,尤其是針對深膚色的移居人群。
周期性感染,例如流感,可能某種程度上能解釋冬天出生人群更高的患病風(fēng)險(xiǎn)。孕婦可能會將這些傳染性病原體帶給她們未出生的胎兒,從而影響到他們大腦的發(fā)育。哥倫比亞大學(xué)精神病學(xué)家艾倫·布朗(Alan Brown)發(fā)現(xiàn),只要媽媽腹中的寶寶出生后患精神分裂癥,她們的血液中會出現(xiàn)對流感病毒異常高水平的抗體。
這些發(fā)現(xiàn)均說明了營養(yǎng)狀況以及懷孕期間避免感染的重要性,這在發(fā)達(dá)國家早已是優(yōu)生優(yōu)育的前提條件。在發(fā)達(dá)國家,這些基本原則或許已經(jīng)在減少精神分裂癥的發(fā)病率,而將它們推廣到發(fā)展中國家將進(jìn)一步降低那里的患病率。麥格拉表示:“很多重要的醫(yī)藥成果,如針對心血管疾病或者癌癥方面,都在我們的飲食和行為習(xí)慣方面產(chǎn)生了變化。我們沒有理由去想心理疾病會有什么不同。”
最早的實(shí)驗(yàn)發(fā)現(xiàn),抗精神病藥物具有較好療效,但它們不再被認(rèn)為是治療高風(fēng)險(xiǎn)人群的首選療法。馬里蘭大學(xué)的精神病學(xué)家威廉·卡彭特(William Carpenter)表示:“坊間有很多擔(dān)心,認(rèn)為對于那些其實(shí)并不會發(fā)展成完全的精神病人的人群來說,抗精神病藥弊大于利,對此我是贊成的。”威廉本人監(jiān)督了是否將APS寫入手冊的討論。

包含歐米伽-3脂肪酸的魚油膠囊或許可以延緩精神錯(cuò)亂的發(fā)作
相反,過去五年的研究一直強(qiáng)調(diào)更安全的治療方法,例如CBT,這種方法教導(dǎo)人們要認(rèn)識自己的思維模式并重新評價(jià)所處的環(huán)境。比如,接受某些不懷好意人的結(jié)論的APS病人,會從CBT療法中明白,不去相信他們最初的懷疑,而是找到對某種行為的解釋。2012年,迄今最大的CBT實(shí)驗(yàn)確認(rèn)可以延緩201名高風(fēng)險(xiǎn)人群的精神病:接受CBT療法的受試群體中,12%在此后的18個(gè)月里出現(xiàn)了精神錯(cuò)亂,而沒有接受CBT的人群這一比例是24%。
另一更獨(dú)特卻剛起步的發(fā)現(xiàn)指出,歐米伽-3脂肪酸魚油補(bǔ)劑具有較好療效。歐米伽-3脂肪酸中包含神經(jīng)元細(xì)胞膜,它們可以抑制炎癥和氧化性應(yīng)激,這兩者疑似會導(dǎo)致精神分裂癥。由奧地利維也納醫(yī)科大學(xué)的精神病學(xué)家保羅·安明杰 (Paul Amminger)和墨爾本的麥戈里共同主持的2010年一項(xiàng)研究報(bào)告:連續(xù)12周每天服用四粒魚油膠囊的高風(fēng)險(xiǎn)人群中只有5%患上精神病,相比之下,服用安慰劑的人中有28%患病。未公開發(fā)表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這種方法至少可以將患病時(shí)間延緩六年,目前另一個(gè)更大的實(shí)驗(yàn)正期望能再一次重現(xiàn)這一研究結(jié)果。
“人們總是問我,歐米伽-3脂肪酸是否和抗精神病藥效果一樣好,但似乎它們甚至更好。”安明杰說。他強(qiáng)調(diào),與早期抗精神病藥實(shí)驗(yàn)不同,服用補(bǔ)劑的人群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xiàn)更佳。
卡彭特說:“如果他們能夠復(fù)制該研究,那么這可能成為自氯丙嗪問世以來最重要的事。”卡彭特此意是指氯丙嗪,上世紀(jì)五十年代問世的首例抗精神病藥。
識別風(fēng)險(xiǎn)
為了進(jìn)一步弄清楚治療的受益群體,研究者們正在尋找其他風(fēng)險(xiǎn)因素,可以精確地識別有精神病發(fā)展趨向的患者。其中之一是來自認(rèn)知能力的調(diào)查,準(zhǔn)確預(yù)測91%精神病人和89%非精神病人。大腦成像和腦電圖也顯示出后來發(fā)展成精神病人和那些非精神病人之間的不同模式。
除了大腦,應(yīng)激激素皮質(zhì)醇的水平,血細(xì)胞中基因表達(dá)和蛋白質(zhì)豐度也是可考慮的因素。例如,2013年北美前驅(qū)癥狀的縱向研究(NAPLS)發(fā)現(xiàn),皮質(zhì)醇水平越高,患精神病風(fēng)險(xiǎn)越大,尤其是那些后來發(fā)展病癥的人。該項(xiàng)研究主要針對精神病早期征兆及預(yù)防。在未來,有APS的人會使用一種計(jì)算機(jī)化的認(rèn)知測試、唾液拭子和血液測試。NAPLS的負(fù)責(zé)人坎農(nóng)說:“基于這些多種類型的信息,有一種算法會得出一個(gè)數(shù)字,這樣臨床醫(yī)生就有足夠的預(yù)測能力,從而更好地幫助病人。”
至此,專業(yè)醫(yī)護(hù)人員對于精神病風(fēng)險(xiǎn)早期的行為征兆的意識不斷提高,提供的幫助就越來越大。鑒于大多數(shù)精神疾病始于12至25歲之間,麥戈里已率先在澳大利亞創(chuàng)建了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為年輕人提供一個(gè)關(guān)愛的場所,為各類問題給予支持幫助,而不僅僅只在精神病初期階段。
即使在美國,人們只有達(dá)到一個(gè)危機(jī)點(diǎn)才接受心理衛(wèi)生保健,但凡事都在發(fā)生變化,這多少源自最近被認(rèn)為是有精神障礙的人實(shí)施的槍支暴力引發(fā)的恐懼。2012年康涅狄格州紐鎮(zhèn)悲慘的槍擊案,使得馬里蘭州最近出資成立了類似于澳大利亞的青少年心理健康計(jì)劃。卡彭特說:“我希望類似的早期識別和干預(yù)中心能夠越來越多,他們的成立等不了科學(xué)研究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