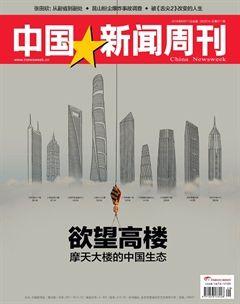高雄氣爆前后24小時
邢新研
暑氣逼人的高雄,7月31日晚顯得極不平靜。消防局20時46分接獲一通報案電話,指前鎮區二圣路與凱旋三路口水溝冒白煙,消防車緊急出動,雖聞到異味,但不知是何種氣體。消防隊員依慣例灑水稀釋,并判斷若是煤氣、天然氣,比空氣輕,應會四處飄散,地面上冒著一大團白煙卻與之不同。大約過了半小時,附近瑞隆路也傳出水溝蓋冒白煙的消息,情況似有些不尋常。消防員依舊查不出氣體外泄源頭,時間分秒流逝,絲毫沒有人察覺埋藏在地底下錯綜復雜的石化管線早已破損、失火,危機迫在眉睫。
高雄市環保局視察陳恭府率領稽查員,于22點19分分別到二圣路、凱旋路口檢測,采鋼瓶采樣,檢驗出是丙烯單項化合物,濃度為13520ppm,而人體在丙烯濃度68ppm以上時即可察覺有異味,這個數值已超出人體忍受范圍近兩百倍。丙烯是一種是無色、無臭的易燃氣體,一旦在空氣中濃度達到2%~11%且溫度達485℃就會燃燒。由于丙烯為高度揮發性物質,因此其燃燒時使用水是無法完全澆息,只能待其完全燃燒分解為水和二氧化碳才會消失。這種有機氣體就是這場災變的罪魁禍首。
23時22分﹐崗山西街三0一巷水溝蓋爆開冒出火花,燒傷一名在路邊擺攤的婦人。高雄市環保局隨后到場采樣,無功而返,但火勢的濃煙很快沖出地表,地下的氧氣愈來愈少,二氧化碳氣體濃度愈來愈高,一場震動天地的爆炸一觸即發。
23時55分,環保局確認外漏氣體是丙烯,正要協調相關管線業者查明,2分鐘后,二圣一路和凱旋路以及三多路、一心路等地接連發生了威力巨大的第一次氣爆,頓時如大地震,地面震動、房屋搖晃,烈焰直竄十五層樓高,民眾驚駭莫名。
當時正在凱旋路、二圣一路口指揮救災的消防局主任秘書林基澤和消防員、記者都被炸飛,掉落塌陷壕溝,到處是哀號求救聲。接著在凱旋路、一心路、三多路發生連環氣爆,凱旋路整條路被炸毀,三多路更是一片慘況狼藉,原本熱鬧街道被炸成深達三公尺的大壕溝,長到看不見盡頭。一部汽車被炸飛掛在三樓屋頂,另一部摩托車被炸飛掛在了民宅鐵皮屋上,爆炸瞬間濃煙、火舌四處亂竄,民眾嚇得奔逃。
在拍到的畫面中,一輛正在行駛的汽車遇到爆炸,眼看著前方著火,想要掉頭,后方又竄出火苗,汽車被困在火海中進退不得。
消防車第一時間趕到了現場,還沒來得及救人,卻因承載量過重陷入了被震壞的柏油路大洞中,前后總共6輛消防車相繼陷落,造成20余消防隊員不同程度受傷,在救災中又有4名消防員被死神吞噬。
這場臺灣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大氣爆,災區包括凱旋路、一心路、二圣一路、三多路等,方圓兩公里盡成廢墟,已造成28人死亡、290多人輕重傷,令人怵目。
誰該負責?
凌晨一點,即爆炸后2個小時,高雄設立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臺灣經濟“部長”張家祝任指揮官,“行政院長”江宜樺指示全力救災;高雄市政府擴大管制區,開設一級應變中心,市長陳菊坐鎮指揮,在臺北的中油總公司成立緊急應變中心,高階主管進駐。
以往民眾熟知的氣爆﹐都只是點狀事件,多半是家庭煤氣使用不當。但這次高雄氣爆在鬧市區呈帶狀及網狀爆發,埋藏在市區馬路底下的石化管線密密麻麻﹐牽涉到好幾家公司﹐高雄市政府一時也搞不清楚是哪家的氣體外泄。從居民聞到臭味到引發連環爆炸,其間長達三小時以上,高雄防災單位像無頭蒼蠅,始終找不出禍源,也未照會相關管線單位關閉閥門、劃警戒區、拉封鎖區,導致氣體愈積愈多,任由大禍發生。
罹難者蔡美金家屬向媒體泣訴,事發前就聞到煤氣味,但是通報了卻沒人理睬。另有網友在PTT論壇上爆料指稱,在晚上八時許聞到臭味就打電話給高雄市民服務專線,“只得到敷衍且事不關己的回復,告訴我們情況已經獲得控制”,并叫他回家睡覺。結果卻發生意料之外的嚴重災難。他在網上怒批,“如果回家睡覺一覺不起,是誰能負起這個責任”。
家住前鎮區竹東里的陳清鑫指控高雄市政府,查泄漏源頭的時間拖太久,導致“人禍”演變成大災難;他停在騎樓下的兩輛汽車、一臺摩托車,被氣爆火勢燒個精光,幸好一家大小及時逃生。
這個過程中, 煤氣公司推給“中油”,“中油”也推說不知情,市政府則眼睜睜看各單位互踢皮球,近4個小時就這么浪費掉了。
氣爆前,高雄市環保局已在現場采得丙烯單一氣體。環保局長陳金德表示,高雄輸送丙烯有三條管線,其中兩條是中油輸往中石化及李長榮化工(下簡稱榮化),但這兩條管線前晚未輸送丙烯,唯一一條輸送丙烯的是華運倉儲輸往榮化,榮化直到當晚23點40分才關閉管線。
陳金德接受采訪時指出,經環保局稽查,氣爆發生前兩個多小時榮化丙烯管線每小時減少3.77公噸,工廠應能判斷有漏氣,卻知情不報,導致丙烯持續外漏。
根據輸送原理,如果輸送方與接收方有壓力差,表示當中管線應有泄漏或破裂。可榮化堅稱管線并未外泄,直到高雄地檢署8月2日進入爆炸現場下水道勘查,找到榮化管線有破洞,疑是重要漏氣點。榮化董座李謀偉才在輿論壓力為“造成社會不安”鞠躬道歉,但否認自己是元兇,強調氣爆的四吋丙烯管線,都是委托“中油”定期維修檢測。雙方互咬,最后的真相仍有待檢方厘清。

臺中逢甲大學都市計劃與空間信息學系副教授劉曜華痛斥:“怠惰殺人!以重工業起家的高雄市地下還有多少危機?‘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有責任,不能坐視不管!”劉曜華指出,高雄市前鎮區下方的油管、氣管不計其數,管線單位應與地方建立緊急養護機制。臺科大化工系教授劉志成也表示,政府應全面檢視老舊管線,或考慮遷移管線、遠離都會區,才能避免再釀巨災。
國、民兩黨難得捐棄成見攜手合作
這并不是高雄第一次發生氣爆。
18年前, 前鎮區亦曾爆發氣爆事故。當時“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委托必生工程公司在當地興橋進行管線切割換管工程,在更換瓦斯管線鉆孔,測試管線內是否有殘存的液化天然氣時,突然有大量液化石油氣溢出,引起大火爆炸。大火沿著油氣竄燒,附近二十三戶民宅被燒毀或玻璃被震碎,造成工作人員、附近居民、路人、消防隊員14人死亡,11人受傷,現場百余公尺內受損民宅超過20余戶,汽車、摩托車燒毀超過50輛,火勢延燒13個小時才完全撲滅。事后“中油”賠償受災戶金額共約4.14億臺幣。
這場氣爆事件造成數百人無家可歸,死傷最慘重的三多路是高雄知名商圈,鄰近光華夜市等觀光景點,大爆炸將整條路炸開,整個路面翻起來,許多人車被彈飛,路上滿是碎玻璃、石塊。
陳菊在臉書上發文道歉,并當即承諾發給每位罹難者300萬新臺幣(相當于60萬人民幣),每位受傷住院者都得到10萬新臺幣醫療費。這也讓亟欲在年底市長選舉翻盤的國民黨找不到見縫插針的機會。代表國民黨參選高雄市長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楊秋興在第一時間前往氣爆嚴重的前鎮區,但畢竟不是執政者,資源有限,只能口頭致意。
高雄市發展格局特殊,港灣、都市和工業區交織發展,歷經多年的發展,不僅工業區和住宅區日益交迭,許多工業用管線也在市區底下錯雜穿梭。此次高雄丙烯氣爆引發民眾恐慌,全臺灣各縣市立刻開始全面稽查瓦斯等地下管線安全。目前除了高雄外,臺灣新北市、桃園、云林等地都有石化相關產業,對于各縣市乙烯、丙烯等工 業用管線,經濟部能源局竟沒有統計管理,連全臺共4060.5公里的油管,也拒絕公布管線分布狀況。民眾不滿,在網上直言:“管線經過我家,不讓我知道,什么道理!”要求政府應讓管線的路線、維修透明化,更應將分布混亂的地下管線整合管理。
陳菊指令“經濟部”重新配置石化管線,避開人口密集區。但“經濟部”又把責任往外推,強調若地方政府不準在某處設置管線,業者也不可能去架設,雙方都不愿承擔管線遷移的責任。
高雄氣爆意外,現場滿目瘡痍,損失數十億新臺幣,估計要花半年時間重建。平常斗得你死我活的國民兩黨,難得在這場意外中捐棄成見,攜手合作。
事發第一時間,國民黨執政的彰化消防特搜隊45名隊員即接獲指令統統回隊上,裝備、服裝、救災儀器統統準備齊全,隨時待命出發高雄氣爆意外現場,加入救援。桃園縣消防局也組成救難隊伍共3車、8人及2只搜救犬,1日上午8時出發前往高雄災區協助救援。
一向熱心協助鄰縣救災的臺北市長郝龍斌也指示臺北市政府的特種搜救隊南下,接受高雄應變中心的統一指揮調度。特種搜救隊包括四輛搜救車、12名搜救人員、4只搜救犬、及生命探測器等儀器,全力協助高雄失蹤人員搜救。另外臺北市社會局長王浩,也已經將20多位罹難者,每人20萬新臺幣的救助金,正式捐給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也在胡志強的指揮下,各局處紛紛支持人力及物力,包括一支23人的特搜隊、7輛救災車與設備、捐款200萬元并成立專戶募款等,希望善盡一分力量。
臺灣人民一向有人溺己溺精神,對于這次高雄大氣爆,民眾紛紛為災民祈福,并伸出援手。除了送物資、提供住宿外,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不少企業、政界、藝人也慷慨解囊捐款助重建,不到4天,社會捐贈總金額已突破7億新臺幣。
高雄氣爆事件傷亡慘重,為免引起民眾反感,原本藍綠為年底七合一選舉的造勢活動也戛然而止。但在氣爆所掀起的全臺捐款熱潮中,代表藍綠參選臺北市長的連勝文和柯文哲仍隱隱有較勁意味。
連勝文競選辦公室8月1日率先捐出3日競選經費新臺幣10萬元,以連家富可敵國的財力,立刻被炮轟捐太少,“太小氣”。連陣營隨即發新聞稿否認捐10萬的非連勝文本人,而是競選總部主委陳炯松。
為了擺脫負面批評,連勝文于8月3日宣布以“個人名義”捐款給氣爆事件中傷亡的警消及環保人員。
目前在臺北市長選舉民調領先的柯文哲﹐沒有連勝文“官后代”的包袱,身為臺大醫師的他和同是醫師的太太陳佩琪合捐一個月薪水共40萬新臺幣。
石化產業產值占臺灣經濟的三分之一,重要性不亞于電子業,而高雄更是石化廠的重鎮。1990年9月位于后勁的“中油”高雄煉油總廠接二連三的工安意外,當地居民發動圍廠抗爭,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承諾25年后遷廠。如今,距遷廠大限的2015年只剩1年,又發生如此大事故,“中油”高雄煉油廠遷廠勢在必行。
在臺灣,環保意識日益高漲形勢下,容易造成污染的石化業幾乎已是人人“喊打”,此時發生氣爆,對臺灣石化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氣爆不僅對于民眾帶來了傷害,也給業界沉重打擊。一位石化業者無奈地表示,“在臺灣,擴產很難、擴廠更困難,唯有出走,留在臺灣只有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