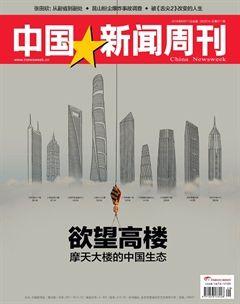航班延誤背后的空管難題
席志剛

7月31日,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證實:目前國家和軍隊有關部門正在研究推進空域管理體制改革。2010年10月,空管體制改革被寫入了“十二五”規劃。時隔4年之后,這是關于此項改革的最新表述。
而與此同時,關于航班大面積延誤的爭議話題正在沸沸揚揚。
多年來,空域管理體制改革一直是個難以言說的話題,也是民航的“切膚之痛”。空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空域體制改革的決策權在中央軍委,只有獲得該層面的支持方有效。”
誰在延誤航班?
7月中旬起,華東地區航班大量延誤或取消。因航班晚點、延誤而備受指責的民航再次陷入尷尬的境地。直至7月22日,官方發布消息稱,因受到軍演的影響,華東地區的航班將持續26天大量取消。
“空中流量管制”是民航航班延誤時使用頻率最高的解釋,而“空中流量控制”則被市場認為是航班延誤的“罪魁禍首”。
“民航廣播延誤情況時,這樣解釋不會引起太多麻煩。”前民航空管局辦公室主任劉文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航班的運行牽涉到機場管理、航空管理、航空公司管理、機場公安管理等諸多方,任何一方都會影響航班運行。
一般而言,飛機從起飛到降落,一直處在空中交通流量管制之下。“空中流量管制”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民航自身管理上的原因、突發事件、軍事演習、軍方飛行管制,還有重要人物專機保障等。
令民航乘客頭痛的是,軍事事務屬于國家機密,機場何時會突然關閉根本無法預知。比如上海浦東機場關閉時,飛行員可以猜到這和軍事演習有關,但乘客卻無從得知飛機轉而降落在一個陌生機場的真正原因。隨后的軍方報紙會在不起眼的位置上報道說,“演習是成功的”。
其實,導致航班延誤的因素很復雜,將很多延誤都歸為是“空中流量管制”很不合理。從數據統計分析來看,空管原因引起的延誤大概在20%左右。
“空中流量管制”導致的大部分延誤,多集中在大機場終端起降區。劉文棣亦形容說,這就像汽車在高速公路上流量很大,到了收費口容易擁堵。“那么多航班排著,特別是前面有航班積壓過來以后,后面等候的就會加重流量的控制。”
“在整治延誤方面,機場挖掘潛力的能力已經沒有了。”劉文棣表示,僅僅增加機場并不能使航班延誤的情況得到多少改觀,因為機場上空的空域得不到開放,建機場毫無意義,無非是增加停機坪而已。
機場擴容與機場飛行空域相關,如果空域無法增加,僅是機場跑道、航站樓增加,只能讓更多飛機停留在機場等候流量控制。在劉文棣看來,可用空域無法滿足機場建設,沒有足夠、分布合理的空中通道,即使有先進完善的機場設施,也無法充分發揮其效能。
“飛機趴在地上的管理理念,怎么可能提高效率?”民航局人士認為,現在“航班延誤”已超出空管效率能夠應付的范疇,“空中流量控制”的后果,往往是飛機大面積地在地面排隊等待,擠不進被劃定的天空。
面對航班延誤導致來勢洶洶的指責,民航頗感委屈,但軍方面臨的壓力亦很大。
軍航和民航,誰給誰讓路?
軍演或其他軍事活動是不是導致航班延遲的主要原因?對此,軍方也無法保持沉默。軍方承認“軍事活動一定程度影響航班運行”,但強調“軍演不是造成航班延誤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又感謝“國內外航空公司、廣大乘客和社會各界給予的理解和支持”。
與民航動輒談及“空域概念”不同,在軍方眼里,頭頂的天空并不僅僅是“空域”,他們更習慣于稱之為“領空”。這意味著“空域管理”上升到了國防安全戰略層面。因此,軍方把領空劃分為可航空域和不可航空域。
分散在七大軍區的空軍飛行管制室的首要任務,是確保部隊飛行訓練正常進行和軍機飛行安全,其次才是監督飛行活動,維護飛行秩序,做好軍民航協調。由于部隊常年擔負戰備值班任務,一旦有空情,須盡快與地方民航部門協同,調整空中航線,必要時則直接通知民航飛機緊急避讓。
“在東南海前沿,這種情況極為平常。”不愿意具名的空軍有關人士表示,這個空域正是民航最為繁忙的區域,但東南沿海空軍飛行管制室指揮塔臺一等轉進的警報隨時都會響起,民航接到軍方流量控制的指令極為頻繁。
東海、黃海、南海等海域的軍事活動較多,空軍占用空域資源相應增加,是流量控制增加的主要原因。此外,保障專機飛行,也會影響民航班機。軍航、民航經常會在誰讓誰的問題上爭吵不休。
“軍航一直在給民航讓路,特別是京滬、京廣航路。”前述不愿意具名軍方人士表示,大連周水子機場外海特別開闊,是軍航、炮兵訓練的最佳靶場,但民航一直在爭,后來靶場遷走了。
“軍方的通知下達后,民航就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證軍航飛行,無論是軍事訓練、演習、訓練、調防還是專機飛行。”民航的說法是,民航一直在為軍航無條件讓路,諸如1998抗洪、2008年的冰雪災害、汶川地震、國慶閱兵、玉樹地震救災,只要軍方的飛機飛起來,民航就無條件讓路。
2007年,民航曾看到空域管制松動的一線曙光,為保奧運和春運,軍方通融了許多,軍航絕對毫無條件地給民航讓路,但僅限于此。直至現在,空管體制仍堅如磐石。于是,民航提出了疑問:既然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春運能讓,為什么平時就不能放開?
盡管呼吁和推進空域體制改革的人士堅持認為,和平時期,空域管理應該更多地為經濟建設讓位,但在軍方看來,現行的平時與戰時空域管理已經最大限度地向民航開放。“和平與戰時的轉換或許瞬間就會完成。”軍事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的領空并不安全。對于此次持續軍演對民航造成的影響,公眾應給予理解。
軍方人士透露,此番軍演是在“做好軍事斗爭準備”的總體要求下展開,以“提高戰斗力才能遏制戰爭”為目標。演練科目不乏電子對抗和實彈射擊,出于對安全的考慮,民航延誤在所難免。
上述軍方人士表示,各型空空、空地、地空導彈智能化程度很高,具有自動尋找目標的能力,而民航班機不具備抗干擾能力,如果不嚴格實施空管,誤擊誤傷的概率就會大增。
空域資源分配難題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境內實行以軍方為主體的空域管理體制,對和平時期民用航空發展的制約越來越嚴重。近十年,民航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關于空域體制改革的呼聲不絕于耳,但始終無法撼動軍方對空域管制的傳統體制。
中國民航脫胎于空軍。在建國后30年間,中國民航管理機構均在軍方領導之下,空管權限亦如此。直至1980年3月5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關于民航總局不再由空軍代管的通知》,民航系統才逐漸從軍隊獨立出來,但空管權限始終在軍方手中。
軍民分家后,空管體制改革也逐漸提上議事日程。由于一直缺乏一個總體協調機構,民航的地方色彩越來越濃厚,直接與軍方探討協調空域體制改革存在諸多不便。為此,在1986年,國務院、中央軍委空中交通管制委員會成立,意在推動空域體制改革,促進中國民航業的發展,簡稱國家空管委。

這個空域管制、協調機構由國務院副總理級別的領導掛帥,在1994年、2000年的空管制度改革中取得一定成效。但除此以外,在深層次改革上幾乎沒有太多建樹,在協調軍民航發展矛盾時作用也不明顯,因此被認為形同虛設。
實際上,國家空管委確實是個虛設機構,其辦事機構設在軍方的總參謀部,辦公室主任由總參作戰部部長兼任。此外,總參作戰部下設總參空管局,局長仍由總參作戰部部長擔任。總參空管局負責中國大陸境內軍、民航及其他飛行器、包括導彈在內的空域使用管理。
2000年8月1日正式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飛行基本規則》,確定了國家空管委領導全國飛行管制工作,全國境內的飛行管制由空軍統一組織實施。在“統一管制,分別指揮”體制下,空軍兼有空域管理者和使用者的雙重身份,而民航作為空域用戶申請和使用空域。這種制度設計導致空域資源分配和使用欠缺公平和效率,造成軍民航使用空域時必然產生矛盾。
在空軍看來,飛行管制任務十分繁重。平時,空管既要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保障提供高效、快速、安全的航空運輸,又要為國家領空與國防安全服務,完成國土防空的任務;還要為軍事訓練、專機飛行、國家和軍隊的重大活動提供空域和安全保障。戰時,空管成為軍事指揮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空中戰場使用和戰區空域管制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民航局公布的資料顯示,中國大陸臨海上空劃分為11個區行情報區,空域總面積約1081萬平方公里劃設空中危險區66個,其中39個全天限制使用,3個每天限制14小時,8個每天限制18小時,6個提前一天通告限制時間,5個其他分時限制,5個限制時間不定;劃設空中限制區199個,其中102個全天限制使用,4個每天限制16小時,7個每天限制17小時,77個每天限制18小時,5個每天限制21小時,4個限制時間不定。如此嚴格的空域劃分和使用管制,把民航飛行壓縮在20%左右的空域。
只有20%的空域對民航開放,這一比例使中國成為世界上航空管制最為嚴格的國家之一。這種處于軍方的強勢控制、效率低下的空域管理體制,在國際上已不多見。空軍方面亦有人士認為,現在的空管體制存在“一統就死”的弊端。
而民航發展勢頭強勁,2008年中國民航在20%的空域飛了80%的飛行量,凸顯了民航流量增長與空域容量的矛盾,在壓力之下,空軍加大了對民航的支持力度,至2010年,民航日常使用空域達到可用空域面積的32%。
然而矛盾還在加劇——近兩年來,國家領導人出訪時簽回來了數百架飛機。
“領導人一簽單,民航就哆嗦。”劉文棣稱,民航支持國家出于政治、經濟、外交需要所簽署的大單,但現有的空域容納不了那么多飛機,民航不增加空域,只能讓飛機在地面上趴著,承受很大損失。
并不只有民航的流量在增長。大國空軍的建設目標,也使得空軍(包括陸航、海航)裝備的各型戰機數量大大增加,且大多部署在東南沿海一線,而戰機形成戰力需要必要的訓練時間與訓練空域,無疑與繁忙的民航在此空域使用上形成交叉。
而在軍方看來,從1081萬平方公里空域而言,分為可航空域和非可航空域,并不都是可用的。
國家空管委特聘專家空軍少將陳志杰此前解釋說,中國空域面臨的現實是,要保證軍隊各級管制區、民航28個高空管制區、37個中低空管制區所有軍民機場高效運轉,讓通信、導航、情報、氣象保障各種系統協調運行,讓軍事飛行和民航飛行互不干擾,確實很難。
據了解,民航航路航線網絡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形成,三十多年來尤其是近十幾年,民航快速發展只能依靠對航路網絡修修補補維持下去。民航局和國家空管委辦公室都相繼開展了航路網絡規劃研究,但付諸實施時,卻仍然受到軍方影響而難以推進。
從近年軍民航使用空域協調情況來看,難度在不斷加大,矛盾也在無休止的協調過程中進一步加劇。固定航線劃設越來越少,臨時航線日趨增多。軍航由于自身使用空域需求的增長,釋放永久性空域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
因此,在現實環境下,陳志杰提出了以“融”為主的頂層設計思路:軍方空域并沒有24小時在用,軍民兩方可以協調使用。但這種協調在民航看來實在是艱難。
空域體制改革需獲得軍方支持
民航謀求空管體制改革的想法一直存在,但囿于體制之困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轉而通過空管技術來解決有限空域內民航發展的矛盾。然而,民航近年來年均兩位數的發展增速,使得在幾乎窮盡技術挖潛的民航,已無法在京滬、京廣、滬廣航路上塞入一架飛機。
幸運的是,空管體制改革被納入了“十二五”規劃,算是給民航呼吁多年未果的痛楚一些安慰。但談及“空管體制改革”,民航局官員總是欲言又止,未來“空管體制改革”的路徑、方向,民航和軍方的位置怎么擺放等等,仍是一個禁忌話題。
“民航使用空域無法增加,無法與軍方角力,體制束縛的原因更多一些,技術層面問題很容易解決。”接近民航局核心的人士說,民航局對于空域緊張的問題,毫無辦法,只能向軍方申請、協調。
熟知國家空管體制的資深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曾在20世紀90年代試圖建立既不是軍隊的,也不是國務院的,而是國家層面的“國家空管局”來管理空域。
“原計劃把軍方和民航捏在一起,但最終一山不容二虎,不到一年便夭折了。”不愿具名的民航空管局的人士透露,軍方和民航雙方未能在新的空管局架構下達成妥協與合作,在國家層面建立空管體系的計劃就此宣告失敗。
這個被視為與軍方平起平坐的想法終因“時機不成熟”半途而廢,對民航的打擊頗大。“國家空管局”1994年后劃歸民航局,其影響力十分有限,直到今天,民航在空管上的權限仍不能與軍方平起平坐。
隨后,民航企業“要么民航不發展,要么不知道哪天就會發生撞機”的表態,迫使民航局再次觸碰“改變一下空管體制”的議題。有軍方背景的前民航總局局長楊元元曾專門上書國務院,但這次觸碰幾乎使民航局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楊元元那封信后來轉到軍方,軍方很重視,來來回回折騰了好幾次,也就無聲無息了。此后,民航再與軍方協調航路、申請航線,過程極為痛苦。民航局人士每談及此事,莫不耿耿于懷,“一份飛行調研報告形成的建議,怎么就變成告御狀了?”
據了解,就中國目前空管體制構架和協調機制存在的問題,國家空管委、全國政協、國家發改委等單位先后對民航進行了專題調研,就空域使用情況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議。
在民航空管局副總工程師文立斌看來,應建立國家空域的統一管制體系,將國家空域的管理權限由軍方轉交給政府,并組建下屬國家空管公司,統一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務。考慮到中國國情,軍方仍保留相關管制部門,負責航路航線以外特定使用空域的飛行指揮工作。
這是民航系統提出的最大膽的改革設想,但這個想法也只是在民航系統內不超過十個人的范圍內交換意見而已。
分析人士認為,空管體制改革涉及到被視為飛行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飛行基本規則》的修改,該項改革面臨是否獲得軍方最高層級支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