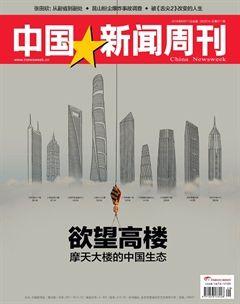1973:一個華裔美籍教授的漫長歸鄉路
滑璇
1972年2月底,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美籍華人、紐約州立大學物理學系教授林多樑感到,回家的機會來了。
這一年,林多樑已離家23載,家鄉的父母無時無刻不讓他魂牽夢縈。但中國閉關多年,與美國更是處于敵對狀態,能不能回家、怎么回家,林多樑心中毫無把握。這時,他想到了在耶魯大學做研究員時結識的楊振寧。
1971年7月,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人楊振寧首次回國探親。當時,他已回國兩次,可算“大陸通”。他給林多樑出了一個主意:要想知道能不能回家,可以先給父母寫信。只要父母回信應允,就表示中國政府批準了;如果連回信都沒收到,一定不行。
對此,林多樑十分不解:“父母回信怎么能說是政府批準?這完全沒有關系嘛。”
電話里,楊振寧說出了一個生僻的中文詞匯:單位。“在中國,每個人都有一個單位。你說你要回家,父母根本沒法決定,他們一定要經過單位向上匯報。”楊振寧向他解釋,“他們最后告訴你的,其實就是政府的指示。”
如今,84歲的林多樑已滿頭華發,但仍然鄉音未改。盡管已在中美之間往返幾十次,他都沒想出一個與“單位”完美對應的英語單詞。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他只知道,“單位”似乎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種特殊產物,代表著一種體制,包羅萬象,包含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各種內涵。
1972年年中,林多樑寫了一封信,填上20多年前最后一次通信時的家庭住址,寄了出去,投石問路。
一入臺灣歸不得
1948年,國共內戰步入白熱化階段。1月,林彪、羅榮桓率領的東北民主聯軍完成整編,總兵力達到70余萬,正式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3月,在第四次四平街戰役中,東北軍殲滅和俘虜了全部14000余名守軍,大獲全勝。
盡管東北戰事緊張,但在南國的魚米之鄉瑞安縣(現浙江溫州瑞安市),仍是一片太平景象。
那一年,林多樑還叫“林松濤”(林多樑,表字“松濤”,時人多以表字互稱以示尊敬),18歲,剛從溫州中學高中部畢業。他尋思著,先游玩數月,再回鄉報考大學不遲,遂只身赴臺。四平街戰役,是他赴臺前對這場戰爭最后的、也是最清晰的記憶。
到臺灣時,正趕上“雙十節”,他頗有興致地參觀了臺北舉辦的“臺灣博覽會”。讓他做夢都想不到的是,此時正是國共大決戰的階段,“三大戰役”先后展開,形勢急轉直下,不足三個月,已是山河易幟。
林松濤被困在了臺灣。瑞安,再也回不去了。
在那段風雨飄搖、無依無靠的日子里,糊口謀生,成為他每天唯一的想法。他在政府里做過職員,卻因為大批國民政府人員撤退抵臺,很快被裁掉;到臺南投靠過堂叔林成槐,住了兩個多月便匆匆離開。1949年春,在同鄉的介紹下,他來到鳳山“陸軍總司令部”任職。
1950年7月,他在未經“陸軍總部”批準的情況下,私自報考臺灣師范大學物理系。如果不是上級認為“求學上進是好事,不予追究”,他的主管組長馬上就要發出通緝令了。報考大學時,他使用了20年的名字林松濤,恢復成了國民身份證和族譜上的本名——林多樑。
1956年,臺灣清華大學復校,并創辦了原子科學研究所。林多樑大學本科畢業,在這一年考入清華,成為該研究所的第一屆研究生。
1958年,他赴美留學,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理論原子核物理專業攻讀博士。
初到臺灣的幾年,他一直靠通信與家中聯系。信件經由一位親戚從香港轉寄。家人收到信,要原封不動地拿到公安局,由公安人員拆開;回信時,也要先送公安局審查并當場封印,才能到郵局寄出。父親林祝清從來不在信中訴說家中遭際。每次通信時,只簡單寫寫家中成員的健康狀況。
1950年代初,中國大陸“三反五反”運動開始,林多樑聽說了很多聳人聽聞的故事,主動停止了家信往來。
雙方從此不通音訊。他完全不知道的是,家人因為他而多受牽連。弟弟林松炫雖然學習成績很好,但是沒被大學錄取。50年代中期,林家大妹妹也下放到云南林場勞動,直到1975年才調回溫州。
1958年,為了修路,家里的老房子被推倒。還好,新址不遠,就在100多米之外。
家信
大約一個月后,這封漂洋過海而來的家書輾轉到了林家。
突然收到美國來信,林家多少有些驚慌。“當時,哥哥和家里失去聯系20年了,我們都以為他在臺灣,從沒想過他已經去了美國。”林多樑的弟弟林松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林多樑的母親陳鳳柳拿著尚未拆開的信封,直奔派出所。民警告知,信是其子寄來的,陳鳳柳激動之余,放下心來。
很快,林祝清執筆給兒子寫了回信。這一次,信件沒有經過派出所,直接從郵局寄往美國。
1972年底,在把信投進郵箱半年之后,林多樑收到了來自瑞安的家信。他知道,他可以回家了。
簽證成為下一道難題。
其時,中美尚未建交。林多樑按照楊振寧的建議,向中國駐加拿大使館遞交了入境申請。有了家信,手續辦得相當順利。但從第一次給大使館寫信說明情況,到簽證到手,又花去小半年時間。
在這半年中,中方也完成了對林多樑一家的政治審查。林家最早得知林多樑真的要回來了,并非通過書信,而是“上面”通知的。“他們比我們知道得早。”林松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973年5月,一切手續終于齊全,買張機票就能走人了。
正在這時,林多樑的長子林世康在水牛城出生了。這個人生中的巨大變化,使他一度想要放棄努力一年才得到的機會。不過,妻子的幾句話重新堅定了他的決心。她說:中國的情況誰也說不準,這次錯過了,或許再也沒有下次了。

合肥探親
從美國啟程前,林多樑以為從香港入關后第二天便能到瑞安,因此與妻子約定,一個月就踏上歸途。未曾想,一個月后,他才從瑞安向第二個目的地——安徽合肥進發,去探望妻子的姐姐和姐夫。
寄信慢如蝸牛,長途電話不通,他根本無法與大洋彼岸的妻子聯系,只好既來之則安之,依照既定路線旅行。
他乘火車前往合肥,一路走,一路玩兒。
在中國,林多樑真正領教了什么叫做人多。他從上海國際飯店十幾層的房間里往下看,南京東路上,人頭攢動,全無空隙,為其生平所僅見。
縈繞在這座城市間的氣息,與1949年前形成了巨大反差。白天,街頭弄尾的男女都穿著藍、綠、灰的粗布衣服,款式相同,千篇一律。夜幕落下,曾經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十里洋場迅速趨于黯淡,被黑夜吞噬。
路過南京時,林多樑去參觀了中山陵。入口處的孫中山銅像,是他入境以來見到的第一座毛澤東像以外的雕塑。游覽南京長江大橋時,導游張嘴便說:“南京在1949年前是國民黨的偽首都。”林多樑很想問問“真首都”在何處,不過想了想,終于還是忍住了。
妻子的姐夫孫良方在中國科技大學任教。本在陜西藍田的中國地質研究院(現中國地質科學院)工作的姐姐錢寧,也在合肥探親。
為了響應中央的“戰備疏散”決定,中科大從北京遷來合肥,時已三年。然而,破敗的教學樓、正在建設的宿舍樓、散布在校門外田野中的大木箱……一切都還百廢待興。
自從接到妹妹的家信,得知妹夫要回國探親,孫良方便向上級作了匯報。
在林多樑之前,錢家在美國的朋友曾受托前來探望。“外事無小事”,為了體面,中科大借給了孫良方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個三只腳的立式衣架。后來,錢寧歸還了衣架,“扣留”下了桌子和椅子。
得知林多樑要來,中科大黨委專門向安徽省委打了報告,省委批示,做好接待工作。蝸居在一間十來平方米的平房里的孫良方馬上分到了一套單元房,三四十平方米,一間15平方米左右的臥室,一間小門廳,帶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如果不是林多樑來,分房根本輪不到只是副教授的孫良方。“排隊等著的人多著呢!”83歲的錢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中科大對林多樑的接待頗費心思。文革時期,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看樣板戲,林多樑看過兩三部便不覺新鮮。有一次,中科大學生會放映電影《紅旗渠》,林多樑因故未能觀看,頗感遺憾。第二天晚餐后,一輛面包車專門將他和孫良方一家四口接到安徽省電影管理處,為他們補放了這部電影。
1949年,錢家幾乎舉家遷臺,在清華大學讀書的錢寧孤身一人留在了大陸。現在,錢家人多在美國。一天,見四下無人,林多樑壓低聲音問錢寧:“你想不想去美國?”一句話把錢寧問懵了,她下意識地搖搖頭。對于去美國,錢寧一直認為那是“太天邊的事”。此前,留在中國大陸的姑父悄悄叮囑過她幾次:你可千萬不能走,你走了連累我們都倒霉。
在中科大,林多樑為數十名休課多年的老師作了一次講座,講西方現代物理的發展趨勢。他感覺,當時中國大陸在物理理論研究方面的水平,似乎還停留在抗戰時的西南聯大階段。
空蕩蕩的校園
離開合肥之后,林多樑飛赴第三站——北京。他想見見北大和中科院的物理學同行,還想看看大陸的清華校園。
林多樑搭乘的,是一架只有十幾個座位的小飛機。飛機上沒有服務的空姐,不提供食品和飲水,中途需專門降落吃飯。
在北大一座中國傳統建筑樣式的會客廳里,林多樑與物理學教授周培源、江澤涵、王竹溪等人會面漫談。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他與核物理學家趙忠堯會談。在清華,他硬闖紅衛兵把守的校門,大搖大擺地參觀了空無一人的破敗校園。
無論在哪里,校園都是靜悄悄、空蕩蕩的,既沒有老師,也沒有學生。
離開美國整整兩個月后,林多樑從北京離境,坐上了飛往香港的航班,踏上了返程。
1974年,他寫了一篇《從小事看中國大陸》的文章,以“松濤”的名字,發表在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10月1日、2日,北京的《參考消息》連續摘登了這篇文章。
在文中,他寫道:“在我兩個月的國內旅程中,到了許多城市,接觸了各種各樣的人們。我覺得國內既不是地獄,也不是天堂……如果一定要問與原來的舊社會或者與其他國家有什么不同,則最顯著的就是既看不到紙醉金迷的銷金窩,也看不到流離失所的流浪漢。”
這些年,林多樑往返中美之間,已成家常便飯。如今的林家,早已子孫滿堂、生活富足。但林多樑認為,中國大陸離真正的現代化,還有待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