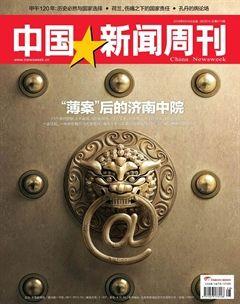大學“國際化”的豪情與尷尬
任鋒
這個七月,由北大燕京學堂引發的“國際化”熱議,更像夏火一般灼炙著北大人與公眾的神經。
先說說我這個月的國際課堂經驗。
因緣際會,參與了一些國際課程和講座的設計、講授。一個項目圍繞中國文化、經濟、政治諸問題,把一個個獨立講座“串燒”起來,對象是來自北美某大學的本科生。當我登上講臺,發現在座清一色南亞北非族裔,不禁慨嘆北美的多元融合當真厲害。后來向協調老師調侃,再過幾年,來的可能都是華裔了。后者云,這個項目提前已把這個潛在群體給屏蔽了。
課上是中國經典與文化導論,學生聽得還算認真,提問也比較靠譜,比如中國的天與其他宗教至上神的區別、道德一元論與相對主義。聽說下午講的是茶道,形而上與形而下安排得相得益彰。協調人說這個項目不全是學習,還得有體驗,大概是“田野調查”的意思吧。據講,有個學生一落地,從北京機場打車到學院路,被收了整整五百RMB。之后,學生們要求,外出都包車。我向他們推薦,可以去雍和宮,還有旁邊的孔廟國子監,不知是否成行。而協調人轉告,他們對京城的捏腳(足浴)相當地感興趣。
另一個課程是儒家傳統。教務老師提前知會,同學們報名踴躍,最后需擴容。課程由幾位教授合上,畢竟用英文講這題目不易。輪到我講,不知什么緣故,發現教室里坐著的,并沒有名單上那些來自馬德里、愛丁堡的國際友生。倒是有幾位新加坡人,從姓名字母拼寫看得出曾經有大陸背景。余下的學生,大部分本校,還有幾位來自“學院路高校共同體”——孤陋的我第一次聽到這么高大上的名詞,算中國的常春藤?
講課我還是精心準備,必恭敬止,學生們也聽之如儀。只是偶爾產生某種荒誕感:中文母語的老師和學生,為了那幾位不知到何處“田野”的國際哥們兒,不得不操他邦之言解圣賢之文。權當為將來的國際普及儲備人材吧。不過,還是有一些細節耐人玩味:講課伊始,從學生那里接收到的不是“老師您好”,而是一張張精明的面孔在問“老師這課怎么考”。那一刻,我有些失落,想起了“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想起了頗為國際化的芮成鋼同學。
對于國際生的“失蹤”,一位主事者解釋,與中國優秀生源的輸出相比,這類國際學校想要吸引國際的相應匹配,還是比較困難。來的人,獵奇開眼的動機更盛,有幾個能坐得下來?
說到這里,我對于北京大學推出燕京學堂項目,圍繞靜園搞出那樣的設計規劃,倒是產生幾分同情。要與哈佛、牛津爭奪國際優秀生源,似乎不得不拿出更為優厚的待遇和條件。要從智識上真正讓國際生坐下來,呆在住宿制學院,似乎不得不提出一套別樣的中國學課程。
再考慮到這個項目背負的國家文化戰略意圖,整個事件更顯得有些緊要了:已然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能再滿足于向外輸出Made in China的鞋子、圣誕樹、高鐵,也應該輸出文化、智識、還有價值。至少,應培養一批具有潛在戰略價值的“知華愛華”人士。
這倒也無可厚非。只是,如何推動這樣壯麗的事業,避免成事不足,或欲速不達?
若仔細檢討北大燕京學堂這一項目的出臺,又能看到這十多年來中國大學教育改革的一般癥候: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匆匆上馬,野蠻拔長。這次的國際化進軍,依然是沖擊世界頂峰的豪情,掩飾不住中國一流大學你爭我搶的劣質競爭心態。
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的“中國學”究竟在智識和精神上有無根底和積累?目前涵蓋人文與社科的課程設計,能否端出在歐美漢學、中國研究以外真正體現中國文明精神的知識產品?“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的國際化儒者辜鴻銘早在1883年,是的,1883年的《中國學》文中就強調,研究者需用所研究民族的最基本原則和概念武裝起來,才能研究該民族的社會關系,然后再觀察這些原則如何運用推行,從經義哲學一步步到其歷史知識、政治構建。這些批評乃針對西方漢學家所發。近百年前在一戰首次追求國際認同受挫后,學運領袖們把辜夫子驅逐出北大。面對眼下這套中國學規劃,他是否能欣賞其中的中國人精神?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緩不應急,能否趕上趟?
想想孔夫子,終生棲棲惶惶,涵育來自遠方各國的英才人杰,國際化可謂厥功至偉。今日,我們是否還有基于仁、禮的普遍主義抱負?在暑期講座末了,我曾語于國際友生,去看看孔廟吧,那里并無門檻(雖然有門票)。因為,我們服膺于一個根植人性深處的信念:有教無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