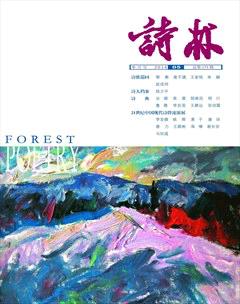給黑夜的情詩 (組詩)
唐不遇,1980年生,廣東揭西人。客家人。2002年畢業于中央民族大學。著有詩集多本,譯有W.C.威廉斯、W.S.默溫等詩人作品。曾獲柔剛詩歌獎、詩建設詩歌獎等獎項。作品收入《中國新詩百年大典》《當代先鋒詩30年:譜系與典藏》等多個選本。現居珠海。
給黑夜的情詩
我還活著。我還熱愛
生活。此刻
你抱著我,曾被燈光的蝴蝶結
綁住的長發
傾瀉著。鏡子
突然變成柔軟的被子
映照著你的雙乳。
約會
你覺得孤獨,無所事事,
想知道墓碑上刻了些什么。
哦,那只不過是一張便條,
上面寫著:我等你。
即使死后也得有耐心
等待一個姍姍來遲的人。
等 候
我使勁拔草,山突然變
矮了。我捧起黃土,
它被洞穴吸走,
就像風吹走爐中的香灰。
我順著泥濘的腳印走去,
雨已經下了很久。
天空中,
幾只眼睛找不到臉。
途中,在簡陋的雨棚下
有許多人在避雨,
我擠到他們中間,
而他們仿佛在等我。
我一定還活著,否則不會痛苦地
感覺到:我已死去很久。
第一祈禱詞
世界上有無數的禱詞,都不如
我四歲女兒的禱詞,
那么無私,善良,
她跪下,對那在煙霧繚繞中
微閉著雙眼的觀世音說:
菩薩,祝你身體健康。
最好的鄰居
在我的左邊是一朵云,
在我的右邊是一條河,
早晨,我們談起了天氣
和許多可愛的東西。
我們總是坐在門口
從日出談到日落,
我們常常開心大笑
或者相對哭泣。
從我們的聲音里
飛出許多魚兒和鳥兒。
我們沒有談到的事物
在黑暗中靜默著。
我們是最好的鄰居,
誰也不愿意自言自語。
夜深了,星星墜落大地
變成馬和荊棘;
另一條孤獨的河流
在心窩上打了一個旋
又漠然地離去,
就是我們告別的時候。
我們各自擺擺手,
云彩回到天堂,
河流回到故鄉,
而我回到死亡。
活 棺
關于樹,我想它們更適合成為
活的棺材,而不必被砍倒,
被雙手靈巧的木匠精心制作,
被莽夫橫著抬進狹窄的洞穴。
死,只是對世界的垂直感受。
它的皮膚看上去那么孤獨,
那么粗糙,樂意被人用小刀刻上
他人的名字或動人的表白。
每次遇見一棵樹,我都看見
那里面站著一個人
正踩著年輪那越來越窄的旋梯上升
直到和每一片葉子融為一體。
有時我渴望打開它們的身體,
比如,在一棵蒼老的樹里
挖一個比樹洞更深的洞穴,
然后活著走進它,走到最深處,
和它一起感受風中那神秘的戰栗,
一起度過漫長的彌留時光。
我甚至把斧頭也帶進去,
讓斧柄和人世的鋒芒提前腐爛。
致八十年代的無名詩人
在你的名字中蘊含著
奔跑,和消失。最后的夜晚
像一條痙攣的尾巴
掃過上世紀八十年代——
所有的時間被攝入毛孔。
天空收集著漂浮的眼睛,
你漆黑的腦袋拐了一個彎
只有尖角回頭盯視。
當時代消費著自己的后代,
忽閃的靈魂停止在那一刻,
你在日月湖邊飲水
直到辭去人馬座的教席。
如今,你在隱匿的詞語深處
孕育另一個宇宙:
每一顆星星都在夜的腹中
用裂開的蹄子敲打大地。
波 浪
當史蒂文森說惠特曼
“像一只沒戴狗鏈的
粗毛大狗,在世界的沙灘上
嗅來嗅去,然后對著月亮吠個不停”,
我就感覺大海仿佛患了精神病
正聳起全身的耳朵
煩躁地聽著。而我也
朝著波浪洶涌的窗外狂叫。
我叫了一百五十年——
古老的月亮是我的主人,
一條明晃晃的狗鏈拴住我的脖子
沾滿了亮晶晶的口水。
我吠個不停,一口氣也沒喘,
直到誰從沙子般密集的黑暗中
向我扔來一根死亡的骨頭。
米沃什百年誕
在地平線那邊,有人在焚燒落葉。
火光僅僅使地平線亮了一會兒。
而在這邊,落葉堆在地上
高過樹,和房子。
點燃它們
太危險了。火太危險了。
人類如黑暗的葉脈掉在床上。
屋頂上一陣鳥鳴,
灑下透明的灰燼。
對你來說,死亡就是
把飄散的火光聚攏,再度焚燒。
一年的最后一天
今天,我感到無比恐慌
想寫一首永恒的詩
結束這一年。毫無安慰的陽光
跌落在我發抖的身上,
我甚至咳嗽著抽了一根煙。
早晨的夢化作一截灰燼——
我以賴床對抗新的一年,
然而脹裂的膀胱逼迫我
以一泡尿哀悼迅速流逝的時間。
我抬頭仰望卷著泡沫
遠去的藍色天空,就像曼德爾施塔姆
在饑餓、寒冷和遼闊的流放地
凝視卷起鋪蓋的屋頂。我的雙眼后
有一股徹骨的寒風
像狗一樣趴著,隨時會
怒吼著沖出去,
帶著一個窮人的痛苦
還有忠誠的恐懼與憂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