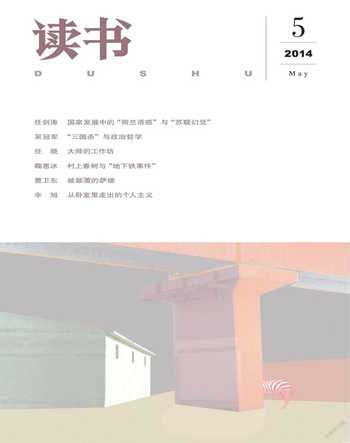從融合的視角看世界
葉雋
世界應該怎樣?丁尼生(Tennyson Alfred, 1809-1892)曾如此展望人類未來:“直到戰鼓不再敲擊,戰旗不再飄舞/ 在人類的議會、世界聯邦中。/ 那里,常識會約束人們煩躁的心靈/ 世界應在普世法則下安靜地思索。”這種描繪是多么理想,這或許就是世界人所共享的“夢”,一個不再紛爭的大同之夢。可問題是,操控戰旗者不是我們,操縱戰爭者更不是我們,當權者為了自己的個人、家庭乃至集團利益,就可以掀起讓人家破人亡、世界滿目瘡痍的殘酷戰爭。“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世界何時就變成這樣了呢?或者,世界本來就一直如此,只是我們太過理想主義了?但丁尼生給我們描繪的這個詩意和平秩序真的讓人心向往之,人類議會、世界聯邦、普世法則,真的能將權力關入牢籠,馴服這千百年來無所不在的“魔”?又或者是,事物的發展過程已經到了走向世界、趨同普適的時候?
信然,即便不說康德、歌德、黑格爾等的世界理想,馬克思對于世界市場的揭示已經可以振聾發聵,“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可這又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層面,“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如此則印度哲人拉達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 Sarvapalli, 1888-1975)的預言可謂恰當:“所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將首次形成一個整體。地球上的每個人、每個地區都會受到其他人和其他地區局勢的影響。”這或許已經是對全球化的明確意識,但他又不無悲哀地感嘆:“然而,人類應該成為一個整體的意識仍然只是個偶發的奇想,是個茫然的熱望。它還沒有成為被人們普遍接受的明確理想或者迫切的實踐需要,這種需要讓我們感覺到共同身份的尊嚴以及共同責任的呼喚。”這不僅符合世界經濟、政治與文化發展的整體趨勢,而且預見了人類走向大同的必由之路。可即便考慮到“條條大路通羅馬”,也仍然有一個路在何方的問題。
新加坡人馬凱碩(Mahbubani Kishore,1948- )于是提出了“大融合”,他強調“世界一體論”,那是因為他堅信“萬物歸一”,這自然讓我們想起了老子那著名的《道德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反向用之,則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歸三,三歸二,二歸一,一歸道”。總結之,正是馬凱碩這里強調的“萬物歸一”。無論如何,我們需要承認,“我們這個世界正經歷著不可逆轉的大融合”。融合之后會怎樣,現在還很難展望;但至少我們需要有這樣的意識,世界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無論是所謂的“第三次浪潮”,還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甚或“新工業革命”,都意味著世界正面臨一個大轉折的關頭。
或許,更為重要的是馬凱碩為這個時代的精英人物布置的“作業”,“對于這個星球的偉大思想家而言,除了聚焦于我們如何管理既有的這個小而密且緊密相連的地球村之外,沒有任何別的選擇”。 是啊,我們不僅需要仰望星辰,也還需要腳踏實地。對于生活在現實場域和地球空間的人類來說,生存資源和制度局限,乃是不得不首先面對的基本問題。舍此現實層面考量,則不足以論大勢與策對。對于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及其對人類文明的意義,世界大國的領袖似乎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克林頓認為:“我們在這個變得越來越小的星球上,擁有共同的未來。”戈爾、布萊爾、布朗諸君也都有相當精彩的論述,戈爾指出:“出現了一種錯綜復雜的全球經濟,越來越以完全交融的一體化形式運作,與資本流動、勞動力、消費市場和各國政府有著完全不同于過去的全新關系。”他強調“數字網絡連接全世界所有國家大多數人民的思想和感情—是最大的希望來源”。相比較以上政治家的敏銳和信心,馬凱碩則顯得更為感性:“我們對這個星球上的其他七十億居民的道德同情感將會繼續擴大。世界將會不斷壓縮。技術將會消除地理距離。在我們曾經生活于小村莊的時候,我們在村莊里會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個道德社會,一種村莊道德同情感,一種對待所有其他村民的道德同情感。在未來幾十年中,我們會越來越多地認識到,我們的村莊是一個世界,但我們的世界絕不是一個村莊。”這段話講的真是形象,正如他當初將全球各國譬喻成一艘大船的若干船艙而缺乏船長一樣,充滿了對人類發展的憂思同情,真有悲天憫人的情懷。馬凱碩的思考值得引起重視,為什么是新加坡人能夠發出如此深刻的思考?或許這尤其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泱泱大國如中華,且不說其傳統文化資源豐富,即便在現時代,也因日益崛起的經濟力量而受到重視,不管是G2的呼吁,還是金磚國家的期許,都使得中國刻不容緩地在走向世界。但我們真能有足夠的知識力來支撐嗎?我們有這樣深刻的哲思追問嗎?我們有多少真正有風骨、有學殖操守的學者,有幾個有思想有原創力的思想家?新加坡是亞洲史上一個獨特的存在,不僅是說它的經濟成績和國富民安,而且也因為這么小的彈丸之國居然有這樣的聲譽和思想。這又怎能不讓錢學森問出那天問式的“錢學森之問”呢?
無論是 “誰若了解自身與他者,自當能明白。東方與西方,永不再分離”,還是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所說“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 這一對永不相遇。/直至天地并立/ 于上帝偉大的審判之位前”,甚或亨廷頓所謂“文明的沖突”的必然性,這些,無疑都值得深入探討。相比較這種執著于東西方之爭,乃至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之爭的思維模式,馬凱碩提供的大融合理念無疑值得深究,在此,全球化、全球倫理(global ethic)、全球秩序(global order)、全球治理(global goverance)形成一組有效的概念。“在全球環境中,給新萌芽澆灌更多的水,施更多的肥:這個新萌芽就是‘全球倫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社會在規模和復雜性方面不斷增加,我們對其他人的道德義務感,從家庭到更大的氏族,從氏族到部落,從部落到領地,從封地到嶄露頭角的民族國家不斷延伸。當然,這種演進不是直線前進的,且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道德感的規模也在穩步擴展。” 雖然,要想將這樣理想的途徑落到實處,而不被人簡單地指為“烏托邦”,還需要大量細致的具體工作要去做。但只要我們想一想德國古典時代精英的思考,就可以明白錢鍾書所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實在不虛。我們只需要稍稍舉證即可,康德就明確指出:“大自然迫使人類去加以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起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而“在經過許多次改造性的革命之后,大自然以之為最高目標的東西—那就是作為一個基地而使人類物種的全部原始稟賦都將在它那里面得到發展的一種普遍的世界公民狀態—終將有朝一日會成為現實”。經歷過跨越時代的大融合之后,席勒借波沙侯爵所表達的那個理想或許不再虛幻:“對于這個世紀來說,我的理想過于早熟。我只能做,未來時代的公民臣屬。”大融合的時代已在行進之中,公民身份將指向未來之大同,世界理想或許也未必就是虛空!當然路也正長,正在世界上每個人的腳下!
(《大融合:東方、西方,與世界的邏輯》,〔新〕馬凱碩著,豐民等譯,海南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