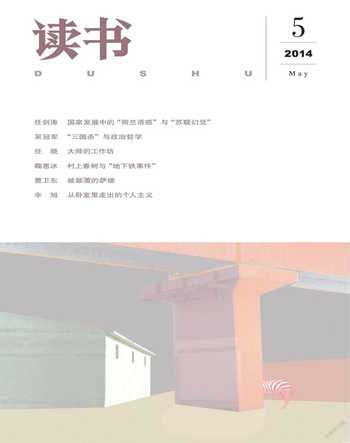西方“文學”概念考略及訂誤
方維規
曾任英國駐寧波領事、一八九七年成為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的翟理斯(H. A. Giles)著《中國文學史》(一九零一),曾長期被誤認為這一領域的開山之作,或曰第一部以西方語言寫成的中國文學史。后來,有學者將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推至俄國漢學家王西里(В. П. Васильев,瓦西里耶夫)的《中國文學史綱要》(一八八零),開拓了該領域研究的視野(李明濱:《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的發現》,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零零二年一月,92—95頁)。然而,“雜文學”意義上的早期中國文學史編纂,委實“山外有山”;西人修中國文學史的時間還要早得多,可推至德國漢學家肖特(W. Schott)的《中國文學論綱》(一八五四)。就迄今所發現的文獻資料而言,該著當為世界上第一部中國文學史。王西里著作之結構,基本上與之相仿。視肖特而非翟理斯在西方著人先鞭,在于翟氏論著并未走出歐洲傳統的文學史框架,亦未在文學觀上完成從文章流別到現代意義之文學概念的轉化。十九世紀末效仿西方文學史纂的諸多日本制中國文學史也大抵如此。這很能讓人看到時人對文學概念以及文學史編纂體例的“共識”,亦能見出外國早期中國文學史纂的一些共有特征。
人們常會對歐洲早期中國文學史纂之“無所不包”、經史子集均歸文學而納悶,或詬病其舛誤。這顯然緣于缺乏對彼時歐洲“文學”概念本身的深入辨析。毋庸置疑,這里所說的不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文筆”之辨(如劉勰《文心雕龍·總術》所言:有韻有文采者為文,無韻無文采者為筆);自然也不是后人對“純文學”(“文”)與“雜文學”(“筆”)的區分,以理解經史子集一應俱全的雜文學觀。作為一個源于西方的學術門類,文學史纂有其自身的發展歷史,離不開“文學”概念的沿革。對于相關研究來說,十九世紀歐洲“文學”概念是一個必須厘清的問題;對此概念的清醒認識,是所有討論的必要前提。
中國學界的不少相關研究在論及西方“文學”概念史時,喜于征引某些西方“權威”著作(尤其是譯成漢語的英美著述)中的說法,這么做當然無可非議。然而,有些被人盲從的一家之見,本身不是沒有問題的;對于概念嬗變至關緊要的某些年代、文獻、人物等,有些陳述顯然缺乏必要的勾稽;有些考據不足的論點或判斷,卻被當作不刊之論。鑒于“信手拈來”是不少人的習慣,亦由于常見的“人云亦云”現象,這篇短文主要從歷史語義學(概念史)的角度,提綱挈領地解證西方“文學”概念的產生、發展及其十九世紀的運用狀況,同時對當下中國學界流行的個別西方參考文獻做一些必要的辨謬工作。下面,筆者先簡要梳理一下西方“文學”的詞語和概念小史。
在古拉丁語和中古拉丁語中,“文學”(litteratura)一詞源于“字母”(littera),多半指“書寫技巧”,即希臘語的γραμματικ?(文法),表示作文知識及其運用。這個詞語的重要語義移位,發生于十六世紀;Lit(t)eratura擺脫了它同“字母”的固定關系而指向“學識”,獲得“學問”或“書本知識”之義,后來擴展為“知識整體”。由于拉丁語長期作為學者語言,“文學”一詞進入十八世紀之后,依然具有濃重的、無所不包的“百科”傾向。然而也在十八世紀,“文學”逐漸變成多層面的同音異義詞:其一,“學識”或“博學”(拉丁語:scientia litterarum,斯時“博學”非今之“博學”,只是“知文達理”而已);其二,研究修辭格和詩學,兼及語文學和史學的學術門類;其三,文獻索引;其四,所有書寫物。在所有書寫物中,又細分出“美文學”,即法語belle littérature;這種向“美文學”的傾斜和詞義收縮,尤其發生于十八世紀下半葉。最遲至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學識”、“學術門類”、“文獻索引”等含義逐漸走下坡路,后來的“文學”詞義初現雛形。昔日之“所有書寫物”,隨語境而轉化為“分門別類的所有書寫物”;而在語文學或文學史語境中,則指“所有文學文本”:凡基于文字的記錄、寫本、書籍等皆屬文學。今人所理解的“文學”一詞,是進入二十世紀之后的產物。以上為西方“文學”(英:literature;法:littérature;德:lit(t)eratur)詞語的語義變遷概略。
從概念史的角度來說,將當今“文學”概念用于前現代或中世紀作品,乃后人之建構。彼時探討所謂“文學”文本,不管其稱謂如何,均未形成與后世“文學”概念相匹配的概念。對不同門類和形式的文學文本之諸多稱謂中,尚無囊括所有文學文本的概念。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上半葉,英、法、德之poetry、poésie、poesie,仍然集“詩作”和“作詩”于一詞;唯創作和作品被區分之后,即十八世紀中期之修辭學與美學的分離,poetry才被看作詩作品,作為創作客體的近代文學概念才隨之產生。嗣后,“文學”這一客體概念具有兩個向度:其一,書寫物之總稱,囊括所有“文獻”,這一范疇見之于里維(A. Rivet)、代庸狄埃(Ch. R. Taillandier)、克萊曼斯(Ch. Clémencet)著《法國文學史》(十二卷,1733/63);其二,富有詩性亦即文學性的作品,見之于胡貝爾(M. Huber)的《日耳曼文學作品選編》(四卷,1766)及借鑒此著的埃貝林(Ch. D. Ebeling)著《德意志文學簡史》(1767/68),沃頓(Th. Warton)的《英國文學史》(三卷,1774/81),尤其是德意志土地上的第一部重要文學史著作、蓋爾維努斯(G. G. Gervinus)著《德意志民族詩性文學史》(五卷,1836/42,自第五版〔1853〕起更名為《德意志文學史》)。這便凸顯出“文學”的廣義和狹義之分;然而,二者的劃分界線常給時人帶來麻煩。在整個十九世紀,狹義文學概念的關涉范圍,依然模糊不清、游移不定。于是,歐洲各種文學史的考查對象,既有虛構作品,亦有許多其他類型的著作,取舍由文學史作者對作品之重要性的看法而定。模糊的界線導致兩種取向:哲學領域的美學探討,多半避免“literature”一詞,而是采用相對明確的poetry(這在黑格爾《美學》中一目了然),即今人所理解的“詩學”、“詩藝”概念,盡管它無法涵蓋所有富有詩性或文學性的作品。語文學和文學史編纂的取向,則是實用主義的,由趣味、習慣和傳統來決定狹義文學概念的范圍。
中國學界新近主要從英語文獻獲得的西方“文學”之詞語史和概念史,因其主要以literature概念在英國的發展為例,存在不少缺漏和明顯的不足之處。威廉斯(R. Williams)《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三聯書店二零零五年版)中的“文學”條目,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尤其是不少例句很能說明literature概念的某些發展階段。然而,或許因為該書條目的篇幅所限,有些問題和重要環節的論述過于簡單,甚至沒有抓住重點。例句過多也帶來瑣碎之弊,從而妨礙了對概念嬗變的宏觀把握,比如“文學”概念在十九世紀的總體狀況以及重要蛻變幾乎未說清楚。中國學者時常津津樂道于卡勒(J. Culler)《文學理論》中所說的現代意義的“文學”概念,說其“才不過兩百年”歷史:“一八零零年之前,‘literature’這個詞和它在其他歐洲語言中相似的詞指的是‘著作’或者‘書本知識’”(卡勒:《文學理論》,李平譯,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1頁)。這種說法其實只是泛泛而論,不能說完全不對,卻嚴重忽略了“literature”在整個十九世紀諸多含義同時并存的現象,尤其是現代“文學”概念遠未占有主導地位這一事實。在彼時《牛津英語詞典》中,它也只能是幾種含義中的最后一個義項,且明確說明這一義項為晚近出現的含義。卡勒的“不過兩百年歷史”之說,最終給人留下“已有兩百年歷史”的不準確印象。
卡勒之說多少也見之于威德森(P. Widdowson)的《現代西方文學觀念簡史》(書名原文:Literature)。作者從其論述策略出發,以小寫的literature和大寫的Literature來區分歷史上的廣義文學概念與晚近出現的現代文學概念(威德森:《現代西方文學觀念簡史》,錢競、張欣譯,北京大學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4頁),自有其合理之處。另外如題旨所示,該著主要以書寫現代西方文學觀念的來龍去脈為重點,這也是無懈可擊的。然而,該書第二章論述literature“曾經是什么”,并號稱“一部概念史”,雖然也追溯了literature的詞源和歷史語義,但同樣以敘寫現代文學概念的源頭和發展為主,這就很難稱其為完滿的literature概念史。該章主要以英國為例來論述現代文學概念的發展,這就難免忽略“西方”文學概念發展史中的有些重要過程,并得出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判斷,例如(在世界語境中)把阿諾德(M. Arnold)及其弟子看作首先強調文學之“民族”屬性的人(34—35頁)。威德森稱,“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一個充滿審美化的、大寫的‘文學’概念已經流行起來”(38頁)。正是這類表述會讓人產生錯覺,以為現代文學概念當時已經真正確立并取代了literature概念中的其他含義。事實當然并非如此,否則就不會出現諸多產生于十九世紀下半葉、并非現代意義的“文學史”著作,這類著作甚至在二十世紀早期也不鮮見。
這里的關鍵問題是,盡管poetry概念與literature概念有著緊密聯系,但它們在概念史上不是一回事兒,公認的西方概念史研究是將這兩個概念分而論之的。威德森的舛誤是,在“一部概念史”中,干脆把poetry概念當作literature概念來論述,如他自己所說:考究“文學”概念史,“稍好一點的做法也許是把‘文學’換成‘詩藝’(poetry),道理很簡單,這是因為至少是整個古典時期直到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浪漫主義時代,‘詩藝’這個詞才是普遍使用的術語,就像我們今天理解的‘文學’一樣”(26頁)。于是,威氏所論述的literature“曾經是什么”,便成了一部很不規范、張冠李戴、引發誤解的“概念史”。道理很簡單,存在已久的literature概念,彼時仍在廣泛使用,且有多種含義。它既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文學”概念,也不是當時的poetry概念所能替代的;poetry是指詩作亦即高雅創作。威氏把“poetry”當“literature”解,故在文中大量引用阿諾德的觀點(“如今主要是詩藝在陪伴我們,因為宗教和哲學將要為詩藝所替代。”“只有最好的詩歌藝術才是我們想要的”,因為只有在詩歌里,“我們的種族將會隨著時間的延伸發現什么叫永駐常留”,等等〔39、40頁〕),以滿篇“詩藝”亦即poetry概念史來證實所謂“大寫的‘文學’概念”(Literature)亦即狹義文學概念之流行;混淆概念的結果是結論的模糊不清。正因為廣義文學概念和狹義文學概念的混淆,才使威氏把阿諾德關于廣義文學的名言“文學一直是為全世界所熟知和談論的最好的事物”(4頁)嫁接于所謂“大寫的‘文學’概念”,即現代文學概念。應該說,“純粹的”、“排他的”現代文學概念,只有一百多年歷史;現代文學概念所理解的文學現象,遠古以來一直存在,而概念本身卻是后來才有的。
根據十九世紀的歐洲對“文學”概念的寬泛界定,它是體現人類精神活動之所有文本的總稱。赫爾德(J. G. V. Herder)和施萊格爾兄弟(A. W. V. Schlegel,F. V. Schlegel)都認為,詩學意義上的(狹義)文學能夠展示人類文化史,一個民族的文學能夠展示其民族精神。人們因此而常把“文學”定格于“民族文學”(上文的《英國文學史》和《德意志文學史》均屬此類),文學史被視為民族史亦即國家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概念在十九世紀的明顯變化,使不少科學史家干脆將十九世紀視為現代文學史纂之開端,且首先體現于如下三個重要方面:(一)在整個科學體系中細分出具有藝術性的美文學,這就出現了“文學”概念的重大變化;(二)新的“歷史性”觀念在黑格爾那里達到頂點,視歷史為發展過程,其意義見之于過程,文學的發展及其意義同樣如此;(三)隨著研究對象的變化,文學史纂的接受者也出現了從學者到一般讀者的變化,文學史的書寫形式和風格也隨之而變。在二十世紀的發展進程中,文學史越來越多地被看作文學史編纂之建構品,并依托于不同的方法選擇。由此,文學史便逐漸從根本上同其他科學門類或科普著作區別開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