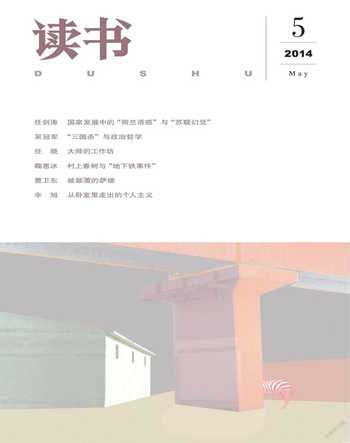故事背后有故事
陶郁
沈艾娣新著《傳教士之詛與一個中國天主教村莊的其他故事》可讀性極強。此書不僅生動,更以關于一個村落歷史的故事傳說作為線索,串起了許多錯綜復雜的事件,并通過介紹和分析這些事件,生動地揭示了天主教作為一套制度安排—而不僅僅是一個信仰系統—如何在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不斷被塑造和改變。不僅如此,通過刻畫晉中天主教被塑造和被改變的過程,沈艾娣又在對于若干關鍵事件的分析中,回顧并探討了鑲嵌在中國近代歷史中的種種趨勢和沖突,并對這些趨勢和沖突在過去三百年間晉中天主教發展史上留下的投射做出了精彩解讀,可謂以小見大,見微知著。
認真翻閱過本書的讀者,當不難發現,題目中的所謂“故事”,雖對本書至關重要,但它們本身只在每個章節的開頭占據了很小一部分篇幅。沈艾娣雖也常用簡短但犀利的段落去簡要分析這些故事所反映出的深層次意義,但主要篇幅卻貢獻給了與這些故事密切相關的歷史背景和真實事件。而且,沈艾娣并未局限于簡單的考據,甚至沒有對這些故事所發生的村莊及其歷史進行全景式深描。相反,她以若干故事作為切入點,分析了晉中天主教在明末清初、清朝前期、鴉片戰爭之后、義和團運動前后、二十世紀上半葉、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和改革開放以來等幾個重要歷史時段發展變化的主要特征。
可以說,在沈艾娣筆下,每個關于天主教的“故事”都是一個晶核,而這些故事的發生地洞兒溝村,則將“故事”與“故事”按照時間先后順序串聯為一條鎖鏈。隨著沈艾娣的敘述,這條由晶核構成的鎖鏈被緩緩放入了飽含信息的歷史溶液之中。于是,豐富、龐雜但又高度關聯的事件與語境,就在敘述的延展之間,凝結為一串致密、清晰而又豐碩的結晶。通過這些結晶,有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天主教在晉中的發展過程,即是一系列因素及其相互關系和力量對比發展變化的復雜結果,又是這些因素和變化的映射。
承載所有故事的洞兒溝,雖然只是位于晉中平原與呂梁山區交界處一隅的偏僻小村,但天主教會的存在,卻將這小村的歷史與國家和世界的歷史緊密聯結起來。
在沈艾娣記錄下的第一個故事背后,關于村莊祖先的傳說雖然晦暗不清,卻很可能與晉商在明清之際遍布全國的貿易網絡不無干系。正是依靠這些網絡,位于內陸省份山西腹地的一些村落,得以和包括首都北京及東南沿海在內的全國各地聯結起來;隨著晉商將天主教隨著銀子一起帶回家鄉,這些村莊早在傳教士造訪之前,就已在某種程度和萬里之外的南歐建立起了聯系。
在第二個故事中,傳教士終于現身亮相。然而,在帝國的強大壓力之下,他們為了生存自保,卻必須依靠鄉紳型教徒的資助和庇護,甚至必須為此在教規上進行妥協。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必須努力適應中國人的文化與習俗;而帝國高層與地方之間的罅隙,又給天主教提供了生存發展的空間。而隨著千里之外的帝國大門被堅船利炮所叩開,傳教士和教徒間同舟共濟的關系也走到了終點。
在第三個故事中,不平等條約已將中華帝國拖入了由西方制定游戲規則的近代歷史,也改變了傳教士與官府的關系。擁有外國資金與司法豁免權撐腰的傳教士,終于積攢了足夠底氣,不再讓教義向習俗妥協。教會投資帶動了洞兒溝的繁榮,主教贏得了村民的擁戴,但他的強勢作風,卻使那些深受民族自覺時期意大利南部新興宗教觀點影響的神父們強烈不滿。而主教的頭號宿敵,竟是一位曾在那不勒斯接受神學教育的中國神父。這位今天已被塑為愛國主義標桿的神父,當年沒有去尋求中國官府的幫助;相反,他只身前往羅馬“上訪”,最終迫使主教黯然離職。
傳教士拒絕讓信仰向習俗妥協,使天主教社區與其他中國人逐漸隔離開來。這種隔閡在義和團運動期間達到頂峰,也引出了第四個故事。隨著義和團運動被鎮壓,新的不平等條約與賠款,又給天主教社區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可是,這種繁榮卻建立在非天主教社區凋敝的基礎之上,它進一步將天主教社區從它所根植的中國社會中孤立開來。
在第五個故事中,意大利統一、墨索里尼上臺和法西斯擴張所帶來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感染了身居中國腹地的意大利傳教士;而歐洲列強之間的齟齬,也投射到了不同國籍的傳教士身上,意大利傳教士就與法國和荷蘭傳教士之間矛盾重重。同時,帝制覆亡與國民革命也塑造著中國神父的民族主義情緒,天主教社區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裂痕與沖突,終于逐漸浮出水面。當侵略者到來的時候,一些傳教士選擇與日本人合作,而另一些則與國民政府并肩抗爭。
中國神父希望自行掌管教會的愿望,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上世紀中葉成為現實。人民共和國勒令所有外國傳教士離開,但整個天主教社區不久也在風雨飄搖中難以立足。沈艾娣記錄下的最后一個故事,就是后來者許是為了減少痛苦而對那段往事的浪漫復讀。但在故事之外,歷史卻很少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對弱者顯出憐憫,也從未像故事那樣在最具喜感的地方戛然而止。幸存者所經歷過的苦難以及他們所做出的妥協,像是結痂的傷口,讓人不忍觸碰。
最后,在隨著全中國一起走向新時代的洞兒溝,天主教社區蘇醒起來,并一如既往地見證并經歷著社區內外各股力量的碰撞與互動。在方興未艾的全球化浪潮中,這個社區的年輕一代,又像他們傳說中的始祖那樣,正在將這個晉中小村與那個遍及全球的信仰網絡重新聯結起來。
可見,洞兒溝雖然貧窮而偏僻,但作為天主教徒聚居形成的村莊,這個位于晉中平原邊緣的聚落,其發展歷程從一開始起就不單純只受本土國家與本地社會的影響。皈依天主教的晉商,不僅與本地官府聯系密切,他們的子孫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繼續通過參與科舉而與帝國的正式權力結構勾連互動,而他們在京城與沿海商埠的人際網絡,不僅帶來了天主教,還帶回了傳教士。
傳教士們深受自己成長的西方社會環境影響,他們遠渡重洋又深入內陸,在建設宗教機構、提供宗教服務和傳播宗教信仰的同時,既要與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在內的中國正式制度互動,又要協調天主教社區內部以及天主教社區與周邊其他社區的關系。而在這些傳教士身后,天主教會和它的政策也在不斷發展變化。影響這些變化的因素,既包括教會看待禮儀之爭的態度,又包括中國在世界舞臺上地位的起伏,還包括作為天主教會腹地的意大利所發生的種種社會變革。
在傳教士與天主教徒之間,中國神職人員對于塑造天主教發展歷史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他們中的一些人曾在天主教會的腹地接受訓練,也深為意大利南部的新興宗教思想所影響;他們中的另一些人,則由傳教士在中國培養,也忠實地繼承著傳教士的衣缽。而隨著時代發展,還有一些人在教會之外又受到席卷全國的現代化浪潮影響,他們立志讓中國人掌管中國的教會,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進展有限。
而天主教社區所在的中國社會,也始終發生著劇烈的變遷。帝制在到達極頂后走向衰亡,又在崩潰前造成了瘋狂的混亂。民族主義思潮風起云涌,殘暴的侵略者又不期而至。最后,人民政權帶來了社會革命,它以將傳教士驅逐出境的方式,直截了當地切割了中國天主教社區與西方的聯系。但風浪過后,一切又似乎回歸到了最初的原點。
洞兒溝的歷史、晉中天主教的歷史,既是上述不同力量及其相互關系發展變化的結果,又反映著其中每種力量及其相互關系發展變化的過程。這些力量及其相互關系的變化,改變了它們自己,也改變了晉中一個遙遠山村的天主教社區。它們創造了歷史,又在歷史進程中被其他參與共同創造歷史的力量所影響和改變。而洞兒溝的天主教社區,不僅見證過歷史、創造過歷史,更用其自身發展變化的經歷,記錄和保存了歷史。
沈艾娣的高明之處,在于她選擇了一個大有深度的小切口。她以一個村莊的歷史和“故事”作為學術求索的出發點,卻沒有讓這個村莊和這些故事限制住自己的視野和思緒。所以,這本《傳教士之詛與一個中國天主教村莊的其他故事》雖然內容異常豐富,線索卻十分清晰;敘事雖然跨越了三百年,但又取舍得當、詳略分明。看來,微觀史要想寫得蕩氣回腸,作者得首先做到胸中有丘壑。
沈艾娣曾提到過對故事的喜愛,這當然是本書成功的必要條件。但是,在此之外,如果沒有她多年來對于中國復雜現代化進程的持續研究和深入思考,此書便遠遠不會如此好看和耐看。
(傳教士之詛與一個中國天主教村莊的其他故事〔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加州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