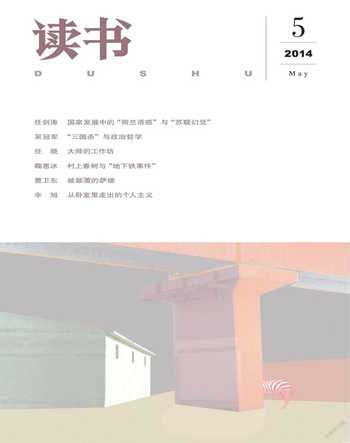鄉關何處
楊煉
當代中國現實的詭譎詩意,時時凝聚在造詞上。例如,“農民工”。這個詞,在中國誰不耳熟能詳?可當我在國外說起,老外們卻一臉茫然:什么是農民工?細想想,這個詞確實造得突兀:農民和工人,一鄉村一城市,本來隔行如隔山,現在就那么直接“堆”(duǐ)在了一起,它是什么意思?既農又工?半農半工?時農時工?農、工之間,全無語法關聯。我猜,這讓老外們的想象,變得頗為浪漫:田野中,人們身著工作服,背后是綠樹、遠山、地平線。嘿,說白了,就像一張“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文革”宣傳畫。
“農民工”的造詞者,雖然語法觀念淡薄,卻顯然直覺敏銳。這個詞,如此簡潔而直接地,一把抓住了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變遷。“農民”—“工”,一個詞,一部濃縮的歷史。它包含了凋敝在身后的鄉村,冷硬陌生的城市,低廉得令人咋舌的工資,千萬顆盲目茫然流亡的內心。對親歷者,甚至“歷史”一詞都太輕飄飄了,它必須換成血淚、生死、滄桑,才能接近于傳達那內涵。一種延續數千年的生存方式,在短短幾十年里,被徹底抹去。一個滲透過無數代人的文化,在一代人眼前,猝然煙消云散。整個過去被一刀切下,埋進水泥地面和林立的樓群深處。只有一雙留著記憶的內心眼睛,能看見那“昨天”。每個人,正如這片土地,只能生吞活剝地咽下這變化。讓一切口腔來不及品味的,交給身體、內臟去品味。由是,滄桑的深度,正在一個人之內、一生之內。我畫在“農民”和“工”之間那個破折號,是一條地平線、生死線,虛虛細細懸起,倒掛著無數無家可歸的鬼魂。
郭金牛就是這鬼魂之一。他使用網名“沖動的鉆石”,直到獲得北京文藝網國際華文詩歌獎第一部詩集獎。網名幾乎等于匿名,這反而更好。我們看不見詩人時,卻真正看見了詩—“某位”農民工的詩。他的聲音,因此裊裊飄出當代中國無名者、無聲者的茫茫人海,使“他們”發出了聲音。《龐大的單數》,詩題就是一幅圖像,或甚至一部紀錄片的片頭。昏暗(出工前或下工后?)中黑壓壓的人群,每個有個人形,卻模模糊糊辨認不出面孔,就那么無邊無際地站著(或活著)。那么多單數,無邊無際時,只剩下一個總數。一種無意義的重量,壓在被抽空了的個體上,不僅形成巨大的反差,干脆輕輕把他們抹去。和這種越龐大越不在的處境比,是否連存在的痛苦,也像一種奢侈了?再看詩:
一個人穿過一個省,一個省,又一個省
一個人上了一列火車,一輛大巴,又上了一輛黑中巴
下一站
這么多“一”,速寫白描般讓我們看見了那“一個”農民工的經歷:離開故鄉,北漂或南漂,從火車換大巴換中巴,惶惑的眼里,只有一個個“下一站”,可那意味著什么?希望?幻滅?闖出的天下?虛擲的青春?或什么都不是,僅僅一張警告你不該存在的“暫住證”?
祖國,給我辦了一張暫住證
祖國,接納我繳交的暫住費
詩句如此簡捷,一個“祖國”,已把那無數“我”只能暫住,還得為此繳費的酸甜苦辣寫透了。“我”該感激這張暫住證,也感激能被接納繳交暫住費嗎?暫住在哪?這城市?這國度?這生命?詩沒有說,不必說。你讀下去,就知道結論了:
哎呀。那時突擊清查暫住證。
北方的李妹,一個人站在南方睡衣不整
北方的李妹,抱著一朵破碎的菊花
北方的李妹,掛在一棵榕樹下
輕輕地。仿佛,骨肉無斤兩。
是的,“我”應當慶幸,和李妹比,還能暫時住下,不必被逼上吊。暫住意味著可能打工,無論工資多微薄,那意味著可能還上親友們攢湊的“盤纏”,不辜負他們眼巴巴的盼望。詩里說了:“車票盡頭 / 二叔,幺舅,李妹,紅兵哥和春枝 / 眼里 / 落下許多風沙。/ 薄命的人呀,走在紙上。”“紙”在這兒是什么意思?寄回家的信紙?還是活人為鬼魂燒的冥紙?又或是接住所有亡靈的一首詩?“命如紙薄”是中國古話,但在這里,被二十一世紀狠狠翻新了。那個“李妹”,最普通的姓氏,甚至沒有自己的名字,卻如一根針,刺進“龐大的單數”們最疼處—比貧窮可怕得多,是命運。一種淪落到底的恥辱,借一張薄薄的暫住證,就能壓碎一個生命。
我曾多次強調,當代中文詩必須寫出深度。因為我們直接生存在深刻的現實中,寫不深等于沒寫。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當代中文詩忽悠了世界幾十年,天文數字的詩作量中,力作佳作卻屈指可數?又一個令人瞠目的反差!說到底,病根很簡單:詩人欠缺真經驗,詩作欠缺真語言。真經驗來自真人生。詩人活得是否到位,端看是否能剖開生存、說出獨特敏悟的東西。無數詩作先天是死胎,因為一讀便知,那里致命的毛病是空洞。所謂詩意,只在照抄套話,那這首詩壓根兒白寫了。要記住的是,詩歌絕非自今日始。每個題材,很可能早被千百位詩人寫過,且寫得更好,那要自問的就是,我這首詩意義何在?我是否真有話說?是否說出了哪怕一丁點兒更深而新的東西?就是說,真經驗只關乎詩思對人生的發現。發現的程度就是經驗的深度。郭金牛用《龐大的單數》,給了我們一個啟示:詩,可以無比具體,讓你聞到“二叔,幺舅,李妹,紅兵哥和春枝”們身上的土腥味,同時又極為抽象,甚至形而上。這讓我想到我用過的兩個命題:一曰“重合的孤獨”,一個個孤獨,又重合得認不出自己,才夠絕對了;二曰“無人稱”,明明“有人”,卻無力無法指認出那人,一種活生生的被抹煞、被忽略,比簡單的無人更慘痛—以此透視存在,我們誰不是農民工?
真語言也與此異曲同工。這里的“真”,相對于膚淺裝飾性的“假”。真語言,是詩歌技巧和深層現實的合一。詩不描述現實,而是打開它,讓我們看見一個原本隱藏著的世界,一種我們沒發現的深層自我。由是,只談技巧、風格,離詩還遠。一位大詩人的一生,是不停從內向外翻出語言、重建自身的歷程。
郭金牛的農民工經歷,很容易讓他靠題材討巧。僅僅“底層”一詞,已經有了足夠賣點。但什么是“底層”?誰代表“底層”?我注意到,郭金牛對此頗為警覺。對于他,“底層”不是商標,而是思想。誰能鉆透自身的處境,觸及存在之根,誰就能構建一個“底層”。所以,不是職業,而是生命,讓我們每個人都在底層。能否意識到這個底層,寫出這個底層,且寫出它的深與廣,則端看一個人的能力。在詩集《紙上還鄉》中,很多“逼近”的白描,讓我們認出郭金牛辛酸的自傳。這當然精彩。但更難的,他還能“拓展”那經驗,以筆力超出一般描寫農民工的套話,賦予他(他們)一個深刻包容的世界。我注意到這首奇妙的《羅租村往事》,開頭直接寫實:
羅租村,工業逼走了水稻,青蛙,鳥
沒錯,我們都認得出這村子。但接著,不同的聲音來了:
李小河咳出黑血
周水稻失去雙親
趙白云患有肺病
陳勝,飛快地裝配電子板;吳廣,焦慮地操作打樁機。
“羅租村”有多大?“往事”要“往溯”至何處?郭金牛一發不可收拾:
唐,一枝牡丹,過了北宋,過了秦川
她,一身貴氣
又過了秦時月,漢時天,至少過了八百里
南宋
以南
怎么,郭金牛要加入過氣的“尋根”派?且慢,看啊:
經羅租村。
經街道,經卡點,經迷彩服。
經查暫住證。
經捉人
我在杜甫的詩中,逾墻走了
好一個“經”字!經歷的經?經過的經?經常的經?或干脆,《詩經》的經?渺遠的和貼近的,抽象的和切實的,典籍的和活生生的,千古傳誦的和當下呻吟的—命運,已“經”凝在一起,如血泊,如噩夢。
這只是此詩開端,后面,我們還讀到“夏。古典的小木匠……明。六扇門的捕快(穿迷彩服的?)……隋 一路哭著去樟木頭收容所……晉哥哥 / 他打鐵,彈《廣陵散》……清。/ 努爾哈赤的小格格,愛新覺羅的小妹妹 / 小童工”,他們在哪?比成吉思汗帝國還遼闊的羅租村在哪?地址,簡單無比:
中國制造
再多的朝代又怎么樣?對農民工們,這世界不是太熟悉了嗎?所有這些苦楚,不是千百年來一直被傾訴嗎?我們似乎只呈現為那些嘴巴,一開一合,被同一首哀歌咀嚼著—嚼爛了:
一部《詩經》,憂慮一只碩鼠
是的,還得回到《詩經》這個原點。那每吮過一個人,就能把他(她)吸干成“妖”的歌聲。這部詩集里,有太多這樣的“妖”,他們“隨意”進出,不驚動別人,甚至不驚動自己,因為他們除了“無人稱”什么都不是:
投水時,隨意,哭了一下
祖國沒有在意、六個受傷的神沒有在意。 —《妖》
我說,《紙上還鄉》好在真經驗和真語言。其結果,就是拒絕簡單化—把一個“深現實”,簡化為低級的標語口號,最終既毀了對生存的理解,也毀了詩自身。郭金牛當然訴苦,且訴得痛徹心肺。但同時,他寫出的“底層”,卻絕不卑賤乞憐,相反,從這些詩中,我們讀出了高貴,精彩,講究—美!獨絕的詩思、輕靈的節奏,艷冶的字句,甚至匠心獨運的標點,在在把墜入深淵,點化成一條超越之途。這漆黑是發光的!這些詩,是重和輕的絕妙組合。“重”得恐怖:每個日子、整個現實、歷史之蒼茫、文化之殘破,到處走投無路;又“輕”得撩人:選字行文,珠圓玉潤,風格形式,神采飛揚。“重”、“輕”互補,就是一條自我拯救之途。對從二十世紀暴風雨群鉆過來的中國人,除此一途哪有他途?當我給《紙上還鄉》寫授獎辭,以“舉重若輕,似輕愈重”談郭氏輕功時,還以為這是他多年修煉而成。后來才知道,他小五十歲,打工二十余載,“詩齡”卻只有幾年。如此凌波直悟寫作秘訣,不能不稱為一個小奇跡!什么是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型?復雜嗎?難嗎?失望嗎?沒必要吧?請看郭金牛的啟示。中國農民工,藏龍臥虎呀!
《紙上還鄉》的核心,在“鄉”字上。“一塊水泥加一塊水泥”(《羅租村往事》)的大地上,我們還有“鄉”么?倘若連“鄉”本身也無家可歸,我們還得了“鄉”么?還不了,何處去?我得承認,《紙上還鄉》如此似曾相識,郭金牛的廣東之漂、農民工們的中國之漂,和我自己的環球漂泊,處境何其貫通!他《夜放圖》中的女鬼,說著我的《鬼話》(本人散文集的標題):“每天都是盡頭,而盡頭本身又是無盡的。”我們得記住,他寫的那些鬼魂,是在一個叫作“全球化”的迷宮中,摸索自己的還鄉之路。他用《紙上還鄉》一詩寫過的富士康工廠里,當代“小格格”們,站在流水線上,手中每天掠過千萬塊電子板。她們是否也用iPhone?是否知道她們給iPhone在全球創造了怎樣的利潤?那些天文數字,不會令她們迷路嗎?不會令我們迷路嗎?這些內蘊的提問,令這部詩集的思想意義,遠超出今日中國,而標志了當代世界的困境:當人類只剩下金錢這唯一的意識形態,自私這唯一的人生哲學,玩世這唯一的處世態度,我們都在徘徊,既流離失所,更走投無路!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崔顥這兩行鄉愁麗句,遙隔一千多年,托舉起郭金牛《紙上還鄉》的意境。但,時間兩邊,孰先孰后?我覺得,沒有先后。同一種詩意中,他們內含著彼此,從對方領悟了自己。回不去故鄉時,郭金牛,帶著他摔碎了的伙伴,那“飛呀飛。鳥的動作,不可模仿”,卻被地球迎面撞上的少年,和無數輪回的“在這棟樓的701 / 占過一個床位 / 吃過東莞米粉”的人生,回來了—
唯有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