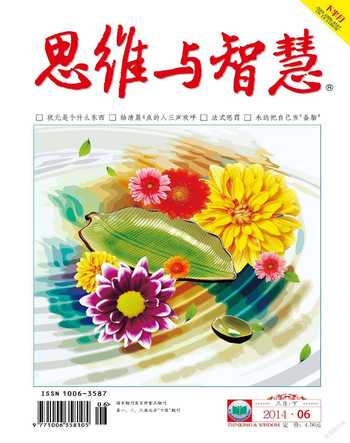有準備地生活
孫昕晨
在辦公室上網(wǎng),抬頭低頭之間,眼鏡的一個鏡片突然掉落在地磚上——“啪”,我腦袋也嗡地一聲:完了。
你懂的,這眼鏡價格一向不菲。更麻煩的是,我這樣既近視又散光的鏡片,從采購到打磨至少要五六天。如果加急,那又得多掏銀子。
而最要緊的是如何擺脫這有點狼狽的局面——手握殘廢的眼鏡,我眼前的世界已經(jīng)變得一片模糊。
清理了地上的碎片,坐定,喝口茶。我心里嘀咕著:趕緊趕緊回家取那副備用眼鏡。
這三十多年來,每一次換眼鏡,我總得多配一副備用。每次出遠門,也總得要把“替補隊員”帶著,以防萬一。雖然一次也沒用著,但,那是必須的。
想到這兒,我反倒笑了:嘿,這等了30年的“替補”,今天不就用上了嗎?
不過,現(xiàn)在我又該如何回家呢?我的大腦在這一瞬間“百度”了一下——幾年前,為了防止眼鏡在辦公室發(fā)生意外,我特地將一副舊眼鏡放在了某個柜子里。于是我馬上搜到了那副還在睡眠的眼鏡。嗨,伙計,起來吧,跟我走一趟。
一場眼鏡風波得以平息。一小時后,我安然回到座位上,辦公室同事渾然不覺。
這個并不精彩的小故事(或曰“小事故”)結束了,現(xiàn)在,我該像蹩腳的小學生作文一樣點題了:要有準備地生活啊。
這里,我不是重復那個長了皺紋的老道理——機遇總是垂青于有準備的人,我是說,這年頭活著,大家都不容易,有人為事業(yè)操心,有人為財富打拼,有人為生存苦熬,人各有其志,人各有其苦,而俗世的生活,我想還是要從容一點才好,做個對生活有準備的人。
生活,總在向我們提問;生活,也總在出其不意地給我們出些繞不過去的“必答題”。有準備,或可以從容面對;有準備,或可以多些應對的招數(shù)。即便不能“含著微笑,看著海洋”,也可以心定自然涼啊。
比如,一個年輕人成家了,你擁有了戀愛的秘訣,但是否學會了夫妻相處的藝術?你是否明白由轟轟烈烈的戀愛,進入相對平靜甚至平淡的家庭生活,意味著什么?是否知道在現(xiàn)實中,婚姻有時不僅是兩個人,而是兩個家庭、兩個家族之間的關系,需要你去經(jīng)營、打理?當愛人的嘴唇從你的臉上悄悄轉移到孩子的屁股上,你是否準備好一副肩膀扛起家的責任?
比如,一個人榮升了,你的仕途鋪上了朝霞,你可能諳熟于跟上級打交道的韜略,但你是否學會了跟下級相處的技巧?在運用權力的路上,你會遇到許多分叉的路口,你是否為自己的選擇做好了準備?且不說政務中那些有待探索的新路,你是否為自己的履職準備了足夠的常識?曾有人言:改革開放的每一步,都伴隨著對常識的重新發(fā)現(xiàn)和回歸。其實,有大識,也有我們經(jīng)營生活的小識。
比如,一個人上了年紀,可否做點關于面對晚境的功課。你跟著人家一會兒“退步”,一會兒“撞樹”,可以理解,但也要算算人生的加減乘除,學做老人,學會跟兒孫相處,學會跟新事物相處,學會面對越來越窄的生命之途,學會跟可能出現(xiàn)的多種疾病打交道,要學的、要準備的還真不少。
很多很多的“比如”啊!……
活著,就是一場不可能畢業(yè)的學習。這一生,我們可能會扮演各種角色,但我們更需要為這樣的角色做點準備。有準備地生活,我們才可能減少一些慌亂、驚悚、恐懼,從而獲得一份坦然、淡定與從容。
想起艾青先生的那首名為《礁石》的詩,我一直記得,有時候也會默念幾句——
一個浪,一個浪
無休止地撲過來
每一個浪都在它腳下
被打成碎沫,散開……
它的臉上和身上
像刀砍過的一樣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著微笑,看著海洋……
(鴨梨摘自《文匯報》2013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