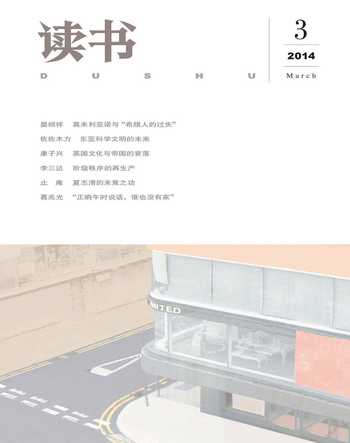七十年前的先知
李子秦
《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問世之際,正值一九四四年的“二戰”時期。自一九一四年德國向英國宣戰以來,德國納粹主義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給歐洲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而在戰爭尾聲,英國國內的建設社會主義,由國家干預,接管壟斷組織的呼聲越來越高。英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政黨亦越來越得勢。針對這種情形,哈耶克表現出了憂慮,于是寫下這本《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并非如斯密《國富論》那樣的鴻篇巨制,它只是一本不足九十頁的小冊子。哈耶克也說這并非學術專著,而只是一本通俗讀物。
先說思想,大家知道英國是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并率先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完成了工業革命,而從十七到十九世紀正是世界史上一段典型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人們剛從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中解放出來,對新生活和未來世界懷有極美好的憧憬,主動性和創造力被極大地激發出來,使這一時期的生產力得到飛速發展。而這樣的制度正是建立在“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而其實德國與社會主義的淵源在封建統治時期就開始了。如大名鼎鼎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為了緩和當時的社會矛盾于一八七一年強力推行了六千條保護勞工的法令,以增進工人福利,這可以說是“王朝社會主義”。由于法國先于德國發生了資產階級大革命,但德國人在目睹這場革命而為“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喜悅和激動的情緒隨著法國雅各賓派的流血專制統治而很快消失殆盡,轉而尋求其他道路。哈耶克認為一九一四年是一個對于英德兩國都很重要的年份,并不僅僅在這一年,作為“一戰”一部分的德國向英國開戰,而更多的是這次戰爭所包含的思想上的意義。關于這點,哈耶克引用了兩位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話來說明,其中一位比較極端:“這次戰爭是英國商業文明和德國英雄文化的一個不可避免的沖突,英國人享樂的商業文明是可鄙的,而德國人對于國家的看法是,國家不是為任何個人利益服務,它是一個人民的共同體,人在其中只有義務,沒有權利,權利的要求是商業精神的結果。”而另一個也沒好到哪里去,他說:“現在是承認社會主義必須是個強權政治的時候了,因為他必須是有組織的。在各民族戰爭時期,對社會主義最重要最緊迫的問題必然是:什么民族應得到高度的權力,因為它是在各民族的組織中模范的領袖?”“我們在國家和產業方面的整個政治生活已上升到一個較高的階段了。國家和經濟生活構成了一個新的統一體。經濟生活中德國的新的社團組織,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國家生活的最高形式。”從以上言論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德國人對集體主義與計劃經濟表現出來的優越感,和作為此種負面的結果—對于其他民族的掌控欲。雖然那時還正值“一戰”,但卻已經表現出希特勒時代納粹主義的性質。據此,哈耶克認為,正是由于前期社會主義,特別是國家社會主義為納粹的形成做了前期鋪墊,盡管人們認為那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但實質上兩者對于自由主義的共同敵視使二者具有了內在的聯系。
在經濟上,哈耶克認為價格不只是商品交換價值的貨幣表現,價格更是在市場經濟即自由經濟,無人管制下經濟體系的一種信號一種信息。注意,是價格在決定著人們的行為而不是政府。而價格是各種力量交織的結果,也不是人為確定的。看到這一段讀者可能會說,這不就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旨嗎?但哈耶克在這里的側重點不是這種體系多么精妙,他強調的更是自由。他認為每個人的認知都是有限度的,所以誰都沒有可能完全指導一切人的經濟行為,他只可以管理自己和與他相關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哪個人,而是政府想要拋棄自由競爭而建立計劃式的經濟這也是不合理的。因為這樣做計劃就意味著要在很多種事物中進行衡量取舍,也就是說政府得擬出一個復雜的價值體系,把所有事進行排序,這樣一來,任何經濟事物的決定權并不在單個人手中,這就不是自由的。同時也不是公平的。因為每個人每個集團的要求是不一樣的,當政府忽略了這種多樣性而推行單一計劃時,一定會損壞一部分人的利益。顯而易見地,隨著我們文明的發展,人的需求只會更趨于多樣,只有在原始社會才會有單一的價值取向。因此對于任何明智的人來說,想要將所有人的需求納入一個價值體系并逐一權衡大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綜上,哈耶克的意思就是說,自由競爭制度最重大的意義就是給所有的人提供了一個可以自由選擇的平臺,而無論日后出現何種局面,如賺錢或是虧本,這一行業利潤大或小等等,這都是所有人,各種力量共同決定的結果,而非是強制性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錢也就不再僅僅是方便人們交換商品的工具,而是一種自由的工具,也就是說市場、商業是這樣一種東西,在這種制度下,各行各業的人們被商業和市場組織起來,通過賺取利益,也就是貨幣參與到了競爭中,而這些環節中,人們是自由的、自發的,結果也是人們自己造成的,而非政府強制的結果。雖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失敗的痛苦,但哈耶克認為當痛苦和不平是非某人人為,而是大家的競爭活動共同作用的和是在當局有意識的決定下造成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說,關鍵不在于痛苦和如何解除痛苦,而在于一個強制性的環境下,人們幾乎怎樣努力都不能改變一個人的處境。俄國的無產階級領導者托洛茨基曾說:“在俄國,不勞動者不得食已變為不服從者不得食,反抗即意味著餓死。”這句話很好理解,如果沒有市場競爭的自由后備,要維持紀律就得向對待勞工那樣用刑。因此可以說是錢將人們從最殘酷最原始的奴役中解脫出來了。
在哈耶克看來,特權跟社會主義引以為自豪的“保障”密切相關。其實在此書中,哈耶克已經不止一次地慨嘆,社會主義者們對社會主義的期望是多么令人想往,而恰恰是這種人們利用它想把世界變成天堂的東西,卻把世界變成了地獄。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收入往往和風險掛鉤,要么有收益,也有風險,要么什么都沒有。而政府如果這時把保障給予某些集團,那么,顯然這就是特權。放到中國來說,也就是一部分領域已經改革,比如私企的出現與外企的進駐,它們可以說是有收益也要擔風險的地方,因為它們并不像國有企業,盈虧都有國家作為最重要的支撐,它們的利潤并不是每一個時期都固定平穩,也不是出了危機都有銀行、股民或者財政買單,它們有了問題面臨的是最直接的破產和倒閉。而另一部分領域,無論是說因為改革未到位或更深層次的原因,反正它有長久的保障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所謂的體制內: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對此哈耶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種局面的后果:“造成人們對保障的追求比對自由的熱愛更日趨強烈。”哈耶克雖然是二十世紀的人,但他分析人們熱愛保障即編制背后的原因,比任何二十一世紀中國媒體的分析都要到位“隨著每一次把完全的保障賜予某一個集團,其余的人的不安全感必然增加”,長此以往,“就逐漸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會價值標準。此時給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個年輕人領得年薪的權利比他懷有飛黃騰達的信心更是其結婚的資格”。這段話難道不正是對當代中國青年價值取向、生存狀態的最好描述嗎?
哈耶克本人也是不認可壟斷資本主義的。關于壟斷,他有一個和主流觀點完全不一樣的觀點,他認為壟斷并非是自由競爭不可避免的產物,它的形成常常是規模大、成本低以外種種因素的結果,它通過互相串通的協定形成并為公開的政策所促進,也就是說哈耶克認為是國家權力的介入使壟斷的控制生效。
他認為社會主義賴以建立的基礎是與個人主義相對的集體主義,這就意味著無論干什么,都需要一個為整個社會接受的目標體系,而要使每個人都歸攏于此體系下,就要讓每個人都相信那些目標,這就使社會主義的一切宣傳都只是為了一個目標,造成了特有的全民思想一體化。對于社會主義此種“思想國有化”,哈耶克的見解十分引人深思:“思想對社會對知識進步所起的作用不在于誰有能力說什么或寫什么,而是在于人和人對任何事都有言論與辯論自由。只有異議的存在,在人們不同見解的相互作用下,理性才得以成長,思想才會獲得生命。而對思想加以計劃,這本身就是詞語上的矛盾。”也就是說,競爭性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不在于創造財富,而在于它內在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實際上哈耶克在西方人眼中也曾被長時間地視為異端,同樣受到西方社會主義者、資本主義改良派及工人民眾的仇視。但歷史自有它自己的邏輯,當世界人民目睹蘇聯極權統治下的殘忍壓抑,以及種種計劃經濟帶來的弊端,人們不得不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哈耶克的學說。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