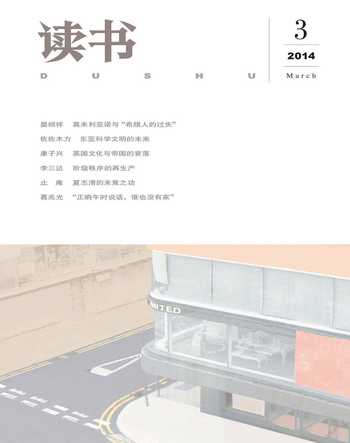拾穗風俗的延續與消亡
張旭
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紀曉嵐記載了這么一個場景:鄉村麥熟時節,婦女兒童數十人為一群,跟在開鐮收割人后面,收所殘剩,謂之拾麥。農家習以為俗,亦不復回顧,猶古風也。作者說其事遠見于周雅,確切的記載是在《詩經·小雅·大田》篇中,作者還說“遺秉”、“滯穗”,是寡婦之利。
對這一社會現象,唐代的白居易也曾寫了《觀刈麥》一詩予以記敘。
這種行為傳統由來已久,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與八十年代初,我上小學時也曾干過這種事。在當時,與農耕文明初始一樣,仍然是體力密集型的農耕勞作。
當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閉幕不久,但仍然是生產隊時期,有一點變化是,把生產隊的規模再劃小,分成幾個生產小組。作為農業機械化標配的大型拖拉機在大隊里有,幾乎沒用過幾次,露天擺放久了,成為一堆廢鐵,在八十年代中期人民公社與生產隊解體與實行承包制后,這堆廢鐵也不知所終。小型手扶拖拉機條件較好的生產隊有,但也是經常壞。耕牛犁鏵翻斗水車和各類傳統手工農具仍然是主流,在日常生產勞作時頻繁使用。在中學歷史課本上看到西漢時期普及的犁鏵、東漢時期出現的人力翻車又叫龍骨水車之類的插圖,我一點都不陌生。
順便一說,任何一種新技術的普及,只要有一條始料未及的條件不具備,都有可能成效為零甚至因造成損失浪費成效為負。在集體化時期的農民,對各種長官意志是既敬畏,又因對各項政治運動形式主義長官意志無法充分理解而在私底下予以藐視,他們中相當多是文盲或剛過掃盲線,但根據其目的(關鍵探究也在于其目的),行為卻是充分理性,反智論在農村基層有深厚的土壤,這也是重要根源之一。其實,將一項適用新技術完全普及的工作,也應該是屬于創新范疇,其推動者與推動者群體的歷史價值與歷史貢獻,應不亞于全新技術的發明者,這一觀點,至今仍然鮮有提及。
但糧食總有一點不夠吃,這是肯定的。在饑飽兩個絕對程度,也就是在0和1這一區間內,是間雜著嚴重程度不等的很多種類型的。白居易在他詩中所揭示的情形是一種,紀昀所說的“故四五月間,婦女露宿者遍野”,甚至“盜竊攘奪,又浸淫而失其初意矣”是另一種更為嚴重的饑饉類型。他在這一條記敘中接著說了一個假托鬼神的故事,這些婦女露宿者竟然“侑酒薦寢,每人贈百金;其余亦各有犒賞。媼為通詞(淫媒),犒賞加倍”,導致“貪利失身,乃只博一飽”。與其說反映了人心不古,注意下紀昀是生活在清代康雍乾時期,史稱“康乾盛世”,毋寧說反映了在生產力沒多大變化的前提下,攤丁入畝制度推行導致高水平均衡陷阱(Mark elvin)更為凸顯的社會現實。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這一時期,情形與歷史時期相比,饑饉程度無疑要減輕很多,沒有“大饑荒”年景那么夸張。雖說沒挨過餓,雖然糧價便宜,但票證流行并缺少現金,農戶的主糧還是主要靠初級分配(處于城市郊區以專事供應“菜籃子工程”的菜農有所例外),消費的主糧仍然要粗細兼雜。秋冬時節以紅薯煮粥為早飯,南瓜餅地瓜干紅薯或綠豆粉條是間雜主餐。春荒時節的野菜,如薺菜、馬蘭頭、馬齒莧、蕨菜與蒲公英的嫩芽之類,也經常由家中的婦孺自行采集,烹熟后擺上飯桌(現在這些可是農家樂餐館的招牌菜)。只要糧食沒有達到充裕程度,對糧食的禁忌行為也很明顯,當時一般的農戶都會養少量家禽家畜,它們的主食是麥麩谷糠與野菜,還有從城鎮飯館里挑來的泔水,如米湯之類。在那時的觀念中,自己如有剩菜剩飯讓家禽家畜和家里的貓狗“開葷”,那也是屬于浪費糧食之舉。以飼料喂養家禽家畜作為商品牟利,是后來專業養殖戶出現的事兒。
因此,婦孺歷來因無法替代只能是體力密集型農業生產勞作的輔助。一切勞作都是以溫飽為目標,婦孺雖然是輔助,但這個輔助是相對無法替代沉重的重體力勞動而言的,在每天勞作時間上并不短甚至還要更長更為辛苦。我還記得在這一時期有幾個中老年貧苦的農婦在賣糧時節,從黎明到黑夜都在國營糧食收購站幫忙。糧站收糧對谷麥的品質有硬性要求,在稱重入庫前,賣糧農戶必須用人力風谷車將干谷麥再扇一遍,這就必須要有人幫忙。她們幫忙的收益是混雜在秕谷廢棄物中的谷物歸她,其實這也是另一種“拾穗”行為。
家庭土地承包制和雜交水稻的完全普及,是距今三十來年才出現的事情,制度與技術的配合無縫對接,使糧食單產與總產量的提高,使中國人普遍告別了饑餓。只要制度不再出現問題,因為饑饉荒年為口吃的導致“人情漸薄,趨利若鶩,所殘剩者不足給,遂頗有盜竊攘奪”和因糧食供應不足導致饑餓發生的民變絕跡。
這是農耕文明史上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這一事件,使“八億農民搞飯吃”,也就是體力密集型傳統勞動生產方式下的饑餓型貧困成為歷史的終結。饑餓型貧困,是農耕文明下傳統中國最大的國情,現在則取而代之以如何解決可支配現金缺乏性貧困和城鎮化時代大潮的興起。原來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道統”認為,家庭經營這一生產方式是落后的,不是被資本主義大生產所取代,就是被社會主義大生產替代。回過頭來看,杜潤生團隊小心翼翼使“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終得以推行,制度建設的貢獻價值并不比劃時代的完全科技創新少。這一點即使馬克思與恩格斯本人也曾在《德意志國家形態》中說道:“歷史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
回過頭來看,技術視野條件下的中國農耕文明延續時期之長,鮮有變化,幾如靜止,對“天不變,道也不變”這一根深蒂固的強大觀念也似乎可以有基于歷史同情的理解,但從近代以來制度革命制度變遷的時代要求上著眼,由于近三十年來技術革命帶來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從七十年代末主糧短缺二三成的普遍情況向現今主糧消費由量到質進行轉變,包括拾穗行為在內的一系列“傳統古風”也告消亡,如果一味對此視而不見,那就意味著多少有點不合時宜了。
(《中國農民變遷論—試探我國歷史發展周期》,孫達人 著,中央編譯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10.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