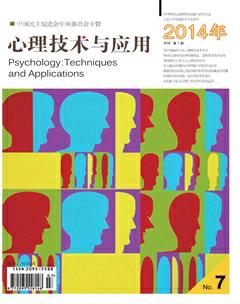得覺催眠及案例解析
格桑澤仁
一、得覺催眠理論簡介
得覺催眠是萃取遠古催眠術及近代東西方催眠術的核心思想,結合東方文化特色,凝練出來的一套適合東方人群的催眠術。它以得覺的“自我理論”為核心。得覺“自我理論”把人的“自我”分為“自”和“我”兩部分。
“自”——內(nèi)心的對話,是對內(nèi)的交流,以念的形式顯化給自己。“自”跟情有關系,跟“緒”有關系,它收到的是感受,要么是情,要么是緒。如果情的產(chǎn)生嫁接到一個習慣,就是情緒。“自”的存在特點是順應、變化、自由、自在,“自”的思維方式是頓悟、感悟、靈動,而非邏輯推理。
“我”——對外的交流,以交流的形式顯化給社會。顯示為人際關系中的我,是社會關系中的我。“我”是面具、是角色、是標簽、是習慣。“我”跟事有關,產(chǎn)生責任與壓力。“我”會產(chǎn)生從眾的需求,并受社會、時代和環(huán)境的影響。
“自”和“我”的互動,形成個體內(nèi)心的多種狀態(tài),表現(xiàn)為自尊、自信、自由、自卑、自閉、自殺等形式。這種自我結構分析模式,適合中國人的思維結構。在催眠過程中,掌握被催眠者是在“自”里,還是在“我”里,至關重要。被催眠者在“自”里,則用情交流,轉換被催眠者的“念”;被催眠者在“我”里,則說事溝通,熟知被催眠者的“習慣”。
二、得覺催眠的特點
1.得覺催眠不需要營造催眠環(huán)境,順時、順勢、順變,不需要考慮環(huán)境因素;
2.迅速捕捉可利用資源,抓住催眠引入時機;
3.立刻確定當下溝通點并自然介入;
4.催眠技巧豐富、帶入路徑立體、恰當有效。
三、得覺催眠治療術前恐懼癥的案例
患者產(chǎn)生術前恐懼司空見慣,大部分患者可以在醫(yī)生的鼓勵和家人的支持下成功完成手術,但是因為恐懼反復推遲手術而造成手術失敗的案例在臨床上也常有發(fā)生。得覺催眠是解決這類問題的一種非常實用高效的方法。
本文介紹的案例是一位女士兩次因害怕手術而產(chǎn)生暈厥導致手術失敗,醫(yī)生和家人對其使用了心理疏導、暗示、服藥等方式都沒有取得效果,最后通過得覺催眠順利完成眼科視網(wǎng)膜脫落治療手術。
1.患者的背景
黃女士,64歲,四川威遠人。性格開朗,患多種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壓等,曾有過疼痛性休克。2013年1月中旬的一天,老人突然感覺左眼金星閃爍,后來竟看不見東西了。到當?shù)蒯t(yī)院檢查,發(fā)現(xiàn)左眼裂孔性視網(wǎng)膜脫落。2月4日,救護車將老人送到成都某大醫(yī)院,該院立刻安排手術,這種視網(wǎng)膜復位手術通常采用局部麻醉,考慮到老人有 “疼痛性休克”史,決定實施全身麻醉。2月6日,老人在被護送進手術室前,血壓、心率正常,可等待麻醉時,血壓、心率驟降,并出現(xiàn)昏厥狀,手術被迫終止。2月7日,老人無法手術,只能出院回家。2月18日,老人再次入院,可躺上病床不久,血壓狂升到180毫米汞柱,遠超手術指征,不得不再次出院。回家后,她歉疚地對女兒說:“我一看到白大褂,心就揪緊了。”2月21日,老人再次住進醫(yī)院等待手術,她的女兒托報社求助,期望格桑教授能將母親催眠,讓她可以順利做完手術,否則眼睛復明的機會愈見渺茫。
2.病房所見
2月22日上午9:30,我來到黃女士所在病房。這是一間8人間大病房,醫(yī)生護士來回查房,患者們都在講述自己的病情,個別家屬補充說明,此時此刻老人所處的環(huán)境嘈雜,而這時手術室已經(jīng)通知老人準備馬上進入手術室。老人收到通知后僵直地躺在床上,雙目緊閉,雙手握拳拽著被單,整個身體處在緊張、焦慮和恐懼中。此刻的環(huán)境,并不利于進行催眠。
3.巧取催眠路徑
環(huán)境不適合,怎么辦?沒有猶豫時間。我略微環(huán)視病房后,端來一把椅子,背窗而坐。由于背對光線,老人必須扭過頭非常吃力非常用心才能看清我,而這種專注正是催眠需要的效果。我以老人女兒朋友的身份進入,打破阻抗,手拉著老人的左手。此刻老人滿手都是汗,全身僵直,沒有表情,眼神呆滯,對答模糊,鑒于這種情況,我意識到,處理老人當下的情緒應當放在首位。
4.催眠過程——22分鐘完成4次催眠
(1)第1次“催眠-喚醒-催眠”:尋找體感中心
得覺催眠強調(diào)要知曉被催眠者的體感。我進入病房后俯身在老人耳邊輕聲低語,一手輕輕抓住老人左手小指。老人直視我的眼睛后,順利導入催眠,不到1分鐘,老人眼神開始迷離。我通過“催眠-喚醒”確定老人的體感中心位置,也就是緊張時會出現(xiàn)的生理癥狀——頭暈、胸悶。再次導入催眠時,我讓老人用手掌壓在胸口,而我的一只手掌壓在其額頭。此時,老人臉頰緊繃的肌肉再度松弛下來。
(2)第2次“喚醒”:確認催眠后才能手術
鑒于不確定老人進入手術室后是否會再次緊張,我在5分鐘后再次把她喚醒。同時暗示老人到醫(yī)院是為了進行手術,觀察到老人眉頭緊蹙。此刻,我確認老人必須在催眠狀態(tài)下才能完成手術。
(3)第3次“催眠”:尋找最勇敢的時光
第3次催眠后,我有意識地引導黃女士回憶過去,尋找她一生中最勇敢最自信的時光。13歲時,她是籃球隊的后衛(wèi);那一年她參加乒乓球比賽,得了亞軍;也是那一年,她和幾個同學翻山越嶺去縣城考上了中學。我不斷強化老人13歲時勇敢自信的畫面,覆蓋當下病房中正準備前往手術室的畫面。定格畫面后,我發(fā)現(xiàn)老人的潛意識中還需要支持。通過催眠狀態(tài)下的對話發(fā)現(xiàn),“爸爸”這個角色,能夠給予老人堅實的力量。
(4)第4次“喚醒-催眠”:完備手續(xù)準備手術
催眠的最高境界不是睡著,而是讓被催眠者睜著眼睛,意識“糊涂”,在清醒的狀態(tài)下不受干擾專注地完成事情。上午10:00,我再次將老人喚醒,準備術前手續(xù);手術出發(fā)前,再次將老人導入催眠狀態(tài)。此時老人并未合上眼睛,而是一路輕松和我輕聲私語。進入電梯前,我躬身在老人面前問:“我是誰?”“爸爸!”老人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這時,我最后一次確認:老人還處在催眠狀態(tài)中。
三、本次得覺催眠過程的特點解析
在本案例中第一次催眠通過抓住老人左手小指帶入,凝視老人眼睛作為輔助;第二次催眠依托老人體感帶入,觀察老人呼吸作為輔助;第三次催眠憑借畫面帶入,暗示性語言作為輔助;第四次催眠則通過拉手、體感、語言、呼吸共同帶入,并連接關鍵詞“爸爸”作為面對手術恐懼的喚醒詞,一旦確定連接成功便立刻喚醒。那么如何判斷連接成功呢?時時注意老人眼神,只要重復同一個詞時,老人眼睛一亮,就成功了!
四、本催眠案例中的理論分析
得覺“自我理論”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闡述了被催眠者的“自”和“我”的對話,通過深度分析被催眠者的“自”和“我”,能夠準確抓住催眠的切入點。在本案例中,緊張狀態(tài)下的黃女士是處在自我糾結中的。她的“自”不斷生“念”,而且是與手術有關的恐怖的“念”,并讓“我”感知到。“自”還不斷將“念”轉化成畫面,播放給“我”看,“我”看到這些恐怖畫面時,全身肌肉開始僵硬、出汗、心跳加快、大腦血管痙攣、供血不暢。身體的生理反應越強烈,越容易產(chǎn)生更為恐怖的“念”,成為一個惡性循環(huán)。
在催眠黃女士之前,我做的第一步是讓她把“我”的感覺轉移,讓情緒釋放出來,但又不能釋放完,剛好讓體感消失就可以了。所以在我和她一見面時就先拉手,讓她莫名其妙,大腦中的“自”“我”對話就停止,“念”就終止,還沒等她緩過神,就除去她潛意識的阻抗,低聲告訴她,我是她女兒的朋友。(“老人家,我是你女兒的朋友,我們聊聊。”)接著盯著她的眼睛,給予一個指令讓她閉上眼睛,帶入催眠。(老人直視我的眼睛后,催眠開始無痕跡導入。不到1分鐘,老人的眼神開始迷離。)
此時的我與她的“自”連接共情,一旦與“自”連接上,馬上喚醒到“我”談事,(5分鐘后,老人被喚醒,這次,我暗示她:“你來醫(yī)院是干嗎的?”想起是做手術,老人眉頭緊蹙。)然后再次除去體感緊張部位,“我”就舒服了,當看到“我”一放松,馬上帶入催眠進入“自”繼續(xù)談情,(“13歲的你渾身充滿活力,13歲的你很勇敢,13歲的你很自信,13歲的你天不怕地不怕。”我不斷強化著。)反復三次進入中度催眠狀態(tài),“我”簡化成單一角色,“自”喚醒給予單一指令,只有單一“念”。
這時嫁接適合患者的關鍵詞,作為面對手術恐懼的喚醒詞,讓“自”記住成為“念”的一部分,并及時喚醒讓“我”也記住,成為喚醒“自”的指令詞,整個催眠過程完成,患者將在手術完成后自動從催眠狀態(tài)中出來。(于是,我又問:“13歲時是誰帶你們翻山越嶺去考試?”“同學的爸爸。”我應和:“有個爸爸支持你一定很好!”閉著眼的老人開心笑起來,我又問:“現(xiàn)在的你是13歲時的你,我是誰?”老人毫不遲疑回答:“爸爸!”此刻,老人進入手術室的最佳時機到了。)
在今后的生活中,關鍵詞還可以成為患者面對其他挑戰(zhàn)時的喚醒詞,每次遇到讓自己緊張的事件,都能自動運用,成為習得的程序,成為抗挫的能力。這就是得覺“自我理論”為催眠帶來的神奇效果。
欄目編輯 / 黃才玲.終校 / 楊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