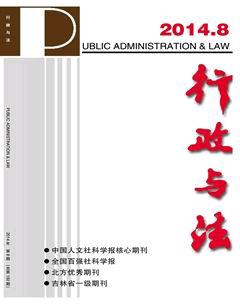基于村莊調(diào)查的農(nóng)村留守人員問題研究
摘 要:隨著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的快速發(fā)展,越來越多的農(nóng)村青壯年勞動(dòng)力離開農(nóng)村進(jìn)城務(wù)工,大部分婦女、兒童和老人成為農(nóng)村留守人員。本文在對湖南省雙峰縣梅龍村進(jìn)行調(diào)研的基礎(chǔ)上,分析了目前農(nóng)村留守人員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做好農(nóng)村留守人員工作的對策。
關(guān) 鍵 詞:農(nóng)村留守人員;農(nóng)業(yè);村莊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207(2014)08-0051-04
收稿日期:2014-05-27
作者簡介:周批改(1973—),男,湖南祁東人,中共湘潭市委黨校副校長,教授,湘潭大學(xué)公共管理學(xué)院碩士生導(dǎo)師,應(yīng)用社會(huì)學(xué)博士,農(nóng)林經(jīng)濟(jì)管理博士后,研究方向?yàn)楣舱吆腿r(nóng)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快速發(fā)展,使大量的農(nóng)民離土、離鄉(xiāng)進(jìn)城務(wù)工,而留在家里的老人、婦女和少年兒童(俗稱“三留守人員”)成為農(nóng)村留守人員。本文研究調(diào)查的梅龍村是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一個(gè)縮影。在梅龍村,黨的惠農(nóng)政策惠及每個(gè)家庭,鄉(xiāng)村風(fēng)貌呈現(xiàn)一派安詳平和景象。然而,同全國農(nóng)村社會(huì)一樣存在著農(nóng)村留守人員問題。
一、關(guān)于調(diào)查村莊與調(diào)查對象的說明
本次調(diào)研地點(diǎn)為湖南省中部的一個(gè)普通村莊——雙峰縣梅龍村。梅龍村位于偏僻山區(qū),有一條鄉(xiāng)村硬化公路通往相距15公里的梓門鎮(zhèn),梓門鎮(zhèn)鎮(zhèn)政府所在地距雙峰縣城6公里。目前,全村共有耕地面積450畝,其中水田面積350畝,旱地面積100畝;另有山地面積2800畝。全村分為5個(gè)村民小組,合計(jì)132戶432人。大部分家庭的主要?jiǎng)趧?dòng)力都外出務(wù)工,打工收入占到農(nóng)民總收入的80%以上,是典型的勞動(dòng)力外出務(wù)工村,其留守人員問題在湖南省具有典型性。
本次調(diào)查采取隨機(jī)和定額相結(jié)合的抽樣方法。共做問卷調(diào)查36戶,其中,隨機(jī)抽樣18戶,定額抽樣12戶,補(bǔ)充調(diào)查6戶。隨機(jī)抽樣樣本能較好地代表總體情況,但由于隨機(jī)樣本太少,故輔之以定額抽樣,即按老人、婦女分為兩類,按家庭收入分上中下三個(gè)層次,每類層分配樣本2戶,以保障調(diào)研對象符合總體結(jié)構(gòu)。補(bǔ)充調(diào)查是在調(diào)查報(bào)告寫作階段,根據(jù)分析問題需要而進(jìn)行的重點(diǎn)調(diào)查。實(shí)地調(diào)查結(jié)束后,將調(diào)查數(shù)據(jù)輸入SPSS統(tǒng)計(jì)軟件,制作成圖表,并進(jìn)行了單變量和雙變量分析。
本文調(diào)查中的農(nóng)村留守人員是指家里青壯年男勞動(dòng)力外出3個(gè)月以上,留守在家的老人(60歲以上)、婦女(指戶口在本村已結(jié)婚的女性)及兒童(15歲以下)。梅龍村總計(jì)432人,其中外出務(wù)工、經(jīng)商人員約180人,常住農(nóng)村人口約220人,其他外出就學(xué)等30余人。有老人近100人,其中留守老人約占80%。有婦女150人,其中留守婦女約占30%。有15歲以下兒童80人左右,其中留守兒童約占70%。本次調(diào)查36戶,這些家庭中外出務(wù)工者68人;有留守老人40人,其中男性老人19人,女性老人21人;有留守婦女11人,留守兒童19人。以下對留守人員的描述主要來自對這36戶家庭的調(diào)查。
二、農(nóng)村留守人員面臨的困難與問題
⒈務(wù)農(nóng)比較效益低,糧食生產(chǎn)能力下降。梅龍村處于群山之中,氣溫偏低,水利設(shè)施陳舊,通常只能種植一季稻。水稻種植基本上是靠手工勞動(dòng),鋤頭、鐮刀和扁擔(dān)為常用的工具,大部分是原始的牛耕。種植一畝水田的勞動(dòng)強(qiáng)度大,成本高,比較效益低。根據(jù)多次實(shí)地核算,該地種植一畝水田(中稻)平均勞動(dòng)用工32天,物質(zhì)支出約400元。一畝中稻平均可產(chǎn)稻谷1000斤,按2011年收購價(jià)(120元/100斤)計(jì)1200元;除去支出400元,一畝田可賺800元。一畝水田的物質(zhì)投入和收益比接近1:2,可見一畝水田的物質(zhì)投入效益較高。但按當(dāng)?shù)胤N植一畝水田平均32天計(jì),每個(gè)農(nóng)民勞動(dòng)一天收入不到30元。當(dāng)?shù)仄胀ㄗ龉すr(jià)平均為90元/天(在自家吃住),農(nóng)民種田的一天收益不到做工收益的1/3。
村里以務(wù)農(nóng)收入為主的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者家庭(農(nóng)林牧漁的收入占一年收入50%以上的家庭)大約25戶,占總戶數(shù)的1/5左右。比如一戶4口的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者家庭,收入大致如下:(1)種植水田2.5畝,每年糧食收入2500斤,除去開支按每畝收入800元計(jì),合現(xiàn)金2000元;()2種植玉米、黃豆等經(jīng)濟(jì)作物,約1000元;(3)養(yǎng)殖牛、豬等,約2000元;(4)林業(yè)收入約2000元;(5)打零工收入約6000元。調(diào)查顯示,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者家庭年收入不到15000元,由此可見,以務(wù)農(nóng)收入為主的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者家庭一年辛苦僅能維持溫飽,是農(nóng)村生活最艱辛而收入最低的群體。這也是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離開農(nóng)村外出務(wù)工的原因。
20年前,村里幾乎每家每戶都種田,整個(gè)村莊每年能產(chǎn)糧30多萬斤,基本可滿足全村400多人的溫飽。隨著越來越多的勞動(dòng)力外出務(wù)工,留守老人和婦女成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主力。種田種地是高強(qiáng)度勞動(dòng),留守人員體力弱,往往力不從心,由此村里荒廢的田地達(dá)20%,糧食種植面積和總產(chǎn)量逐年減少。2011年,村里糧食總產(chǎn)量約20萬斤左右,按人均年消費(fèi)800斤計(jì)算,可滿足常住村里200多人的口糧,略有節(jié)余。但如果外出務(wù)工者大規(guī)模返回村莊,就會(huì)出現(xiàn)糧食短缺問題。
⒉農(nóng)村外出務(wù)工人員收入較低,面臨何去何從的困惑。由于務(wù)農(nóng)辛苦而且收入低,早在20世紀(jì)80年代初,村里就有人外出務(wù)工,既能夠增加收入和解決個(gè)人溫飽問題,又可以將口糧留給家人。越來越多的村民進(jìn)入城市務(wù)工,用務(wù)工收入修建家里的房子,改善留守人員的生活。然而,在調(diào)查中,村里留守人員對外出務(wù)工人員工作的描述并不樂觀。
梅龍村青壯年男勞動(dòng)力基本外出務(wù)工,部分女勞動(dòng)力也外出務(wù)工,總?cè)藬?shù)達(dá)180人。根據(jù)調(diào)查估計(jì),約有15%的外出務(wù)工人員年收入超過50000元,45%的人年收入20000元以上,30%的人年收入低于15000元,還有10%左右的外出務(wù)工人員入不敷出。平均而言,外出務(wù)工人員年均勞務(wù)收入約為20000元,不到所在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的60%。他們在外節(jié)衣縮食,除去必要開支,一年寄回家里7000元左右。但如果將老人和孩子遷帶至城市,這些錢則遠(yuǎn)遠(yuǎn)不夠。可見外出務(wù)工人員的收入不足以維持一家人在城市生活。
外出務(wù)工人員是在農(nóng)村與城市之間搖擺的過渡群體。梅龍村外出務(wù)工人員大部分在廣州、深圳等地的生產(chǎn)加工、服務(wù)和建筑行業(yè)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dòng),還有些外出人員長期找不到相對穩(wěn)定的工作。雖然政府承諾保障進(jìn)城農(nóng)民的平等權(quán)益,但在實(shí)際上城市對農(nóng)村外出務(wù)工人員還存在著很多限制和歧視。外出務(wù)工人員雖然向往城市生活,但他們沒有足夠能力將父母和小孩遷帶至所工作的城市,城市也沒有做好迎接他們的準(zhǔn)備。如果他們真的回到農(nóng)村,也難以習(xí)慣農(nóng)村的生活。外出務(wù)工人員中的很多人不會(huì)也不愿再干農(nóng)活,同時(shí),農(nóng)村也難以接納如此眾多的外出務(wù)工人員返鄉(xiāng)。
⒊留守兒童就學(xué)困難,缺少親情關(guān)愛。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留守的這部分孩子總體上是在健康成長的。但是,他們在成長過程中也面臨著許多難題。梅龍村有15歲以下兒童80人左右,男女比例大致為5:4,性別比不均衡。一些留守兒童沒有戶口,原因之一是一些村民為逃避計(jì)劃生育,沒有登記結(jié)婚就生育。另外,有些男性從貴州、云南等偏遠(yuǎn)山區(qū)娶的婦女往往不到法定的登記結(jié)婚年齡,生育的孩子不能登記戶口。由于農(nóng)村適婚年齡段男多女少問題的存在,所以通過買賣婚娶的問題還會(huì)持續(xù)出現(xiàn)。而且通過買賣婚娶組成的家庭穩(wěn)定性差,在這樣家庭里成長的兒童往往會(huì)遇到更多問題。
留守兒童就學(xué)困難,學(xué)習(xí)成績不佳。調(diào)查的36戶人家中,有19戶家里有15歲以下兒童;其中上學(xué)的有16個(gè),本地上學(xué)9個(gè),在外地住宿上學(xué)3個(gè),跟隨父母在城里讀書4個(gè)。總體上看,4個(gè)跟隨父母在城里讀書的兒童要比在農(nóng)村上學(xué)的小孩成績好,母親在家的5個(gè)兒童又比由爺爺奶奶帶養(yǎng)的7個(gè)兒童成績優(yōu)秀。梅龍村村級小學(xué)幾年前被撤銷,村里的孩子需要去10里路外的學(xué)校上學(xué)。孩子們每天早上要步行一個(gè)多小時(shí)去學(xué)校。2年前村里有人購買了一輛小型面的車來做運(yùn)營車專門送學(xué)生上學(xué)。雖然近年小學(xué)生、初中生免交學(xué)雜費(fèi),但每年其他收費(fèi)仍需600多元。一些家長反映,不算吃飯,每個(gè)兒童的年均支出達(dá)4000元。如果家里沒人外出做工,則無法負(fù)擔(dān)一個(gè)學(xué)齡兒童的開支。
留守兒童在缺失父愛的情況下成長。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留守兒童逃學(xué)、輟學(xué)現(xiàn)象嚴(yán)重。一些留守兒童迷失在網(wǎng)吧里,有些已經(jīng)養(yǎng)成打架、偷盜等不良習(xí)氣。大部分留守兒童的學(xué)習(xí)成績不佳。外出打工的父母與留守在家的孩子溝通交流較少。調(diào)查顯示,70%的外出務(wù)工人員每年回家2-3次,少數(shù)每年僅回家一次。外出的父母往往以金錢代替關(guān)愛,容易養(yǎng)成孩子“拜金”的壞習(xí)慣。而爺爺奶奶對孩子的溺愛也容易使他們形成自以為是、固執(zhí)倔強(qiáng)、冷漠自卑等不良性格。調(diào)查的16個(gè)兒童當(dāng)中,留在父母身邊的兒童精神及身體狀況普遍要比由爺爺奶奶帶養(yǎng)的兒童好,安全感更強(qiáng),人際交往能力更佳。
⒋留守人員生活水平低,身體和精神狀況欠佳。留守人員勞動(dòng)強(qiáng)度大,生活水平低。留守老人和婦女既要承擔(dān)繁重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勞動(dòng),又要料理家庭事務(wù)和帶養(yǎng)孩子,勞動(dòng)強(qiáng)度很大。在被調(diào)查者中,70%的留守人員表示“勞動(dòng)強(qiáng)度大”,30%的人表示對生產(chǎn)勞動(dòng)和家務(wù)勞動(dòng)感到力不從心。村里留守人員的經(jīng)濟(jì)來源主要是勞動(dòng)收入和家中外出務(wù)工人員的收入。此外,從2011年開始,政府給60歲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發(fā)放55元的生活補(bǔ)貼。調(diào)查顯示,留守老人勞動(dòng)所得人均一年800左右,外出務(wù)工人員給予的生活開支平均為2000左右,加上國家補(bǔ)助,一位老人平均一年所得不到4000元。70%的老人覺得生活費(fèi)勉強(qiáng)維持生計(jì),20%的老人覺得生活費(fèi)用緊張,10%的老人認(rèn)為在生活上過得比較寬裕。相比之下,留守婦女的生活水平略高于老人。
留守人員大部分身體狀況欠佳。調(diào)查的24位留守老人中,有10位老人身體很不好,11位老人身體狀況一般,只有3個(gè)老人身體較健康; 5位老人生病無人照顧。近幾年,村里疑難雜癥增加,特別是前兩年,有10多個(gè)人因患癌癥去世。新型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部分家庭醫(yī)療費(fèi)用難以負(fù)擔(dān)的狀況。但村里沒有衛(wèi)生所,也沒有醫(yī)生,看小病也要走好幾里路到村外的小診所,因此小病不治、大病拖的現(xiàn)象較普遍。
留守人員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滿足。調(diào)查顯示,有近1/3的留守老人覺得很孤獨(dú)。在眾多留守老人中,不乏老伴先逝的,這更增加了另一半的孤苦伶仃之感。由于丈夫長年在外,留守婦女的精神壓力明顯增加。她們在辛勤勞作之余,要克制難言的心理、生理需求,容易產(chǎn)生失眠和焦慮情緒。在這樣的情況下,留守婦女更需要用精神文化生活來緩解壓力、排解不良情緒。而在村里,這些留守婦女除了干農(nóng)活、帶孩子,就只能看電視、閑聊或者打牌。調(diào)查的16個(gè)婦女當(dāng)中,空閑時(shí)有5個(gè)人選擇聊天,2個(gè)人打牌,2個(gè)人看電視。
留守人員安全問題突出,生活環(huán)境有待改善。男性勞動(dòng)力外出后,農(nóng)村治安防范力量減弱,財(cái)物被侵占的現(xiàn)象時(shí)有發(fā)生,性侵害案件也呈上升趨勢。近幾年農(nóng)村電器大幅增加,但留守人員缺乏相關(guān)知識,有時(shí)會(huì)因電器使用不當(dāng)而引發(fā)火災(zāi)。梅龍村雖地處山區(qū),但環(huán)境污染問題卻比較嚴(yán)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大量使用化肥農(nóng)藥,特別是村民無法處理的塑料瓶、包裝袋、薄膜等現(xiàn)代垃圾,隨意扔到河里造成環(huán)境污染。近幾年村里癌癥多發(fā),村民懷疑是水污染造成的。此外村里一些農(nóng)民開山劈石和亂砍亂伐樹木破壞了自然環(huán)境。
三、做好農(nóng)村留守人員工作的對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ì)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健全農(nóng)村留守兒童、婦女、老人關(guān)愛服務(wù)體系。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必須以改革創(chuàng)新的精神做好農(nóng)村留守人員工作,夯實(shí)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基礎(chǔ)。
⒈正確看待農(nóng)村留守人員問題,增強(qiáng)做好工作的緊迫感和責(zé)任心。要做好農(nóng)村留守人員工作,首先,必須正確認(rèn)識和看待農(nóng)村留守人員問題。農(nóng)村留守人員問題是城鎮(zhèn)化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中國的城鎮(zhèn)化進(jìn)程被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得主斯蒂格利茨稱之為21世紀(jì)影響世界的兩件大事之一。大規(guī)模的城鎮(zhèn)化建設(shè)支撐了中國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也為農(nóng)民進(jìn)城提供了機(jī)會(huì)。調(diào)查表明,進(jìn)入新世紀(jì),取消農(nóng)業(yè)稅以來,我國農(nóng)村發(fā)展進(jìn)入到最好的時(shí)期,也是農(nóng)村留守人員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時(shí)期。其次,必須從根本上解決農(nóng)村留守人員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一部分農(nóng)民就離土、離鄉(xiāng)外出打工,農(nóng)村留守人員隨之出現(xiàn)。到20世紀(jì)末,農(nóng)村留守人員已經(jīng)成為農(nóng)村中的大多數(shù)。在這些年里,農(nóng)村留守人員問題一直存在,隨著問題的積累和由小變大,已經(jīng)不可掩抑地凸顯出來。農(nóng)村留守人員問題已危及糧食生產(chǎn),危及農(nóng)村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危及農(nóng)村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因此必須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再次,采取有針對性的政策著力解決農(nóng)村留守人員最關(guān)心、最直接、最現(xiàn)實(shí)的利益問題。必須增強(qiáng)做好農(nóng)村留守人員工作的緊迫感和責(zé)任心,將農(nóng)村留守人員需不需要、滿不滿意、答不答應(yīng)作為評判標(biāo)準(zhǔn),采取更人性化的關(guān)愛方法做好農(nóng)村留守人員工作。
⒉落實(shí)惠農(nóng)政策,不斷改善農(nóng)村留守人員的生產(chǎn)、生活條件。在調(diào)查中我們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留守人員的生產(chǎn)條件近十年基本沒有改善,反而有惡化的趨勢。他們的生活水平雖有提高,但依然面臨著醫(y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wù)相對落后等問題。作為弱勢群體的農(nóng)村留守人員,自身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靠政府的政策扶持。2006年國家取消農(nóng)業(yè)稅之后進(jìn)一步出臺(tái)了一系列惠農(nóng)政策,這些政策獲得了農(nóng)村留守人員的高度擁護(hù)。
然而,惠農(nóng)政策并沒有明顯改善農(nóng)村生產(chǎn)生活條件。究其原因,一是惠農(nóng)政策不集中,涉及農(nóng)民的補(bǔ)貼已達(dá)十多種,但都是由各部門分散發(fā)放。如糧食直補(bǔ)、退耕還林補(bǔ)貼等由不同部門分發(fā)到各農(nóng)戶,資金分散且數(shù)額很小,難以發(fā)揮作用。二是近幾年社會(huì)保障類補(bǔ)貼增多,如新型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養(yǎng)老保險(xiǎn)、低保、殘疾人補(bǔ)助、優(yōu)撫、農(nóng)村獨(dú)生子女或兩女家庭補(bǔ)助等補(bǔ)貼可以直接到農(nóng)戶,但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方面的資金如道路修建補(bǔ)貼、水利建設(shè)補(bǔ)貼等很少進(jìn)入村莊,往往在縣鄉(xiāng)就被截留了。三是惠農(nóng)政策針對性不強(qiáng),外出打工經(jīng)商的群體已不再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但他們依然享有惠農(nóng)政策。這不僅導(dǎo)致了有限的資金偏離政策目標(biāo),而且降低了農(nóng)村留守人員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積極性。
目前,農(nóng)村留守人員已成為事實(shí)上的農(nóng)村生產(chǎn)和建設(shè)主體,落實(shí)惠農(nóng)政策必須根據(jù)農(nóng)村留守人員特點(diǎn)和愿望,調(diào)整工作的重點(diǎn)和方法。在調(diào)查中,為了解留守人員的愿望,我們設(shè)計(jì)了9個(gè)開放式問題,將搜集到的農(nóng)村留守人員的愿望和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一是農(nóng)村留守人員渴望獲得尊重和關(guān)心;二是“誰來種田”是農(nóng)村留守人員擔(dān)心的緊迫問題;三是加強(qiáng)水利建設(shè)和農(nóng)村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是農(nóng)村留守人員關(guān)于農(nóng)村發(fā)展提出的建議;四是改善醫(yī)療教育文化和養(yǎng)老保障等公共服務(wù)是農(nóng)村留守人員對黨和政府的熱切期盼。為此落實(shí)惠農(nóng)政策要順應(yīng)農(nóng)村留守人員這些期待和愿望,針對農(nóng)村留守人員面臨的突出問題,建立健全農(nóng)村留守人員的政策支撐體系。
⒊關(guān)愛農(nóng)村留守人員。“關(guān)愛”是現(xiàn)代社會(huì)工作的重要方法,是提高幸福指數(shù)重要途徑。首先,必須加快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步伐。農(nóng)村留守人員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xiāng)分治的二元體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ì)提出“健全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的體制機(jī)制”是解決這個(gè)問題的根本方法。一是大力推進(jìn)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推進(jìn)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是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的重點(diǎn)。要把農(nóng)村公共服務(wù)作為政府的重要責(zé)任,與城市公共服務(wù)統(tǒng)一規(guī)劃,統(tǒng)一建設(shè)標(biāo)準(zhǔn),統(tǒng)一財(cái)政保障。當(dāng)前要著重加強(qiáng)農(nóng)村社區(qū)服務(wù)中心建設(shè),使社區(qū)成為政府和社會(huì)各界服務(wù)農(nóng)村留守人員的基地。二是大力發(fā)展縣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縣域經(jīng)濟(jì)是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的基礎(chǔ),也是從源頭上減少留守人員的方法。要重視縣級工業(yè)園區(qū)建設(shè),在通過嚴(yán)格環(huán)保評價(jià)的前提下,積極引進(jìn)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積極探索土地有序流轉(zhuǎn),大力推進(jìn)一鄉(xiāng)一品、一村一品集團(tuán)式發(fā)展。一些地方還可發(fā)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制品,既增加農(nóng)村留守人員的收入又傳承了鄉(xiāng)土文明。
其次,必須努力為農(nóng)村留守人員辦實(shí)事。一是要強(qiáng)化關(guān)愛農(nóng)村留守人員的組織領(lǐng)導(dǎo)工作。各級政府要將關(guān)愛農(nóng)村留守人員工作提到重要議程上來,明確部門責(zé)任,發(fā)揮婦聯(lián)、共青團(tuán)等群團(tuán)組織的作用。支持并組建農(nóng)村留守人員互助協(xié)會(huì),提高農(nóng)村留守人員自我管理互相服務(wù)的能力。二是創(chuàng)造條件滿足農(nóng)村留守人員“和家人團(tuán)聚”的愿望。城市廉租房要面向進(jìn)城農(nóng)民,出租給他們做“暖心房”。根據(jù)《國務(wù)院關(guān)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guī)定》,職工在規(guī)定的探親假期和路程內(nèi),由所在單位發(fā)放本人的標(biāo)準(zhǔn)工資和往返路費(fèi)。要參照這些政策,制定具體措施保障農(nóng)民工享有這些權(quán)利。三是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dòng),促進(jìn)農(nóng)村留守人員身心的健康發(fā)展。婦聯(lián)等部門開展的“農(nóng)村留守婦女兒童關(guān)愛行動(dòng)”,宣傳部門牽頭的“三下鄉(xiāng)”活動(dòng),既可以對農(nóng)村留守人員進(jìn)行政策宣傳,又可以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要針對農(nóng)村留守老人、婦女、兒童的特點(diǎn),設(shè)計(jì)形式多樣的文化、教育、體育和衛(wèi)生活動(dòng),以促進(jìn)他們的身心健康發(fā)展。
關(guān)愛農(nóng)村留守人員任務(wù)艱巨,責(zé)任重大,各級領(lǐng)導(dǎo)干部都要自覺把農(nóng)村留守人員的事情放在心上,努力為他們排憂解難。要真心關(guān)愛農(nóng)村留守人員,同時(shí)要讓關(guān)愛成為各級領(lǐng)導(dǎo)干部的一種工作方法。
(責(zé)任編輯:牟春野)
注:湘潭大學(xué)公共管理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何柳參與調(diào)查研究,提供了很多基礎(chǔ)數(shù)據(jù),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