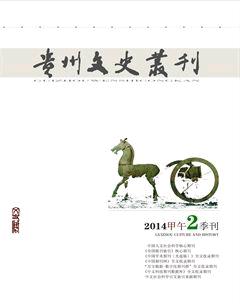“給僧道度牒”與“命道篆司造周知冊”
曹群勇
摘要:明王朝道教管理制度由三大部分構成:其一,道教管理機構——管理道教的組織措施;其二,道士管理制度——“度牒”制;其三,宮觀管理制度。明王朝道教管理從制度設計層面來看是合理的,然而明王朝道教管理制度的施行實踐卻不盡然。除了太祖和成祖嚴格執行外,其后諸帝皆有制不依,管理制度遭受破壞。
關鍵詞:度牒制 明王朝 道教管理 制度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4)02-23-29
政府設置道教管理機構,發端于南北朝。至元代,中央設集賢院總領道教,所轄各派再分級進行管理。正一道在天師之下,“路設道篆司,州設道正司,縣設威儀司,皆屬焉”,分領其事。明代道教管理機構,在借鑒、吸取前代經驗基礎上,特別是元代經驗上建立起來。
一、道教管理機構:管理道教的組織措施
1、明代道教管理制度體系
洪武十三年廢中書省,令六部各自獨立而直接聽命于皇帝。廢除相權,加強皇權,由此確定明朝政府官制。洪武十四年前后明朝政府的官制變化是研究明代社會政治生活的坐標性事件。洪武朝道教管理政策作為加強中央集權諸多政策的一項,毫無疑問亦與此坐標性事件息息相關。朱元璋的道教管理政策,以洪武十四、五年為界,分前后兩個時期。洪武十四、五年以前大體上是元代道教政策的繼承,特別是洪武五年以前繼承的色彩濃厚;洪武十四、五年后,則以一貫的政策臨事,奠定有明一代道教管理政策的基礎。
洪武元年(1368)正月,“立玄教院,以道士經善悅為真人,領道教事”。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革僧道善世玄教二院。洪武十五年(1382)始置僧箓司、道箓司。“僧道箓司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縣有僧綱、道紀等司,分掌其事,俱選精通經、戒行端潔者為之”。這制度分為“在京”和“在外”兩類。“在京”的道箓司,以掌天下道教。道箓司設正一、演法、至靈、玄義等官,分左、右設置,一職一人。即左、右正一各一人,正六品;左、右演法各一人,從六品;左、右至靈各一人,正八品;左、右玄義各一人,從八品。“在外”的府設道紀司,掌本府道教。都紀一人,從九品;副都紀一人,未人流。州設道正司,道正一人。縣設道會司,道會一人。俱未人流。又先后于龍虎山設正一真人一人,正二品;法官、贊教、掌書各二人,以佐其事。閣皂山、三茅山各設靈官一人,正八品。太和山設提點一人。
朱元璋“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曾特設神樂觀,并命道士主領神樂觀事”。洪武十二年(1379)所建神樂觀,設提點一人,正六品,知觀一人,從八品(嘉靖中革)。神樂觀職掌樂舞,以備大祀天地神祗、及宗廟社稷之祭,隸屬太常寺,與道箓司無相統屬。設立神樂觀之意義,他在《諭神樂觀敕》文中闡述說:“傳不云乎,國之大業,在祀與戎。曩古哲王,謹斯二事,而上皇祗,悅賜天下安和,生民康泰。朕起寒微,而君宇內,法古之道,依時以奉上下神祗,其于祀神之道,若或不潔,則非為生民以祈福而保已命也”。在朱元璋看來,祀神為“生民祈福”,為自己“保命”,是關乎整個王朝安危福禍之大事,因此祀神必須敬慎。另外他在《神樂觀提點敕》曰:“朕設神樂觀,備五音奉上下神,祗其敕居觀者,皆慕仙之士。其仙之教也,或云始廣成子,流傳至漢日道士,凡此者,多孤處云居,樓巖屋樹,是則宜其修也,晨昏目心以去玄覽,宵晝仰觀俯察以滌宿世之冤愆,措今生之善行。……如此者,安得不與神通!……今見修道士某,雖未若此,其志已處清虛,特命職格神朗、五音都提點、正一仙官,領神樂觀事,爾中書吏部,如敕施行,諭往欽哉”。此敕既闡述了由道士主持的原因,又“表明他對道士的十分崇敬,相信他們能與神通,可以利用他們來祀神,以達到設立神樂觀的政治目的”。
2、明代道教管理機構職制
道箓司是明朝廷總管天下道教的機構,隸屬于禮部。其職責是:凡天下府州縣宮觀、道士名數,從道箓司核實,而書于冊,申報禮部;各宮觀住持有缺,從道官舉有戒行、通經典者,送道篆司考中,具申禮部奏聞方許;道士申請度牒,亦從本司官申送如前考試,禮部類奏出給;負責簡束天下道士,使之恪守戒律清規,違者從本司理之;若犯與軍民相干者,方許有司懲治。
第一,設官不置署
明代“各級道教管理機構設官不置署,諸司全設在道觀內。道箓司在明初設在南京朝天宮,‘靖難之變后,京師遷北京,建靈濟宮于小時雍坊,置道箓司于內。宣德八年(1433),詔如南京式樣建朝天宮于阜城門內(今白塔寺西),以置道箓司。至天啟六年(1626),朝天宮遭火災,道箓司始遷入東岳廟,終迄清,未有改變。其下各司官署亦設在道觀內”。
第二,道官的品階秩祿
最初道箓司衙門各官,“一依宋制,不支俸”。糾但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一月,重定文武百官品階秩祿時,又命道箓司各官依品支俸。左、右正一,正六品,秩同翰林侍讀、京縣知縣,月給米十石;左、右演法,從六品,月給米八石;左、右至靈,正八品,月給米六石五斗;左、右玄義,從八品,月給米六石。府道紀司都紀,從九品,月給米五石。州道正,縣道會,皆未人流,俱不給祿。
第三,道官的選拔
按規定,各級道官,“俱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者為之”。“在太祖、成祖、宣宗等朝,大體按制施行,所選道官皆一時高道”。如劉淵然、李時中、邵以正、湯希文、曹大鏞等都為一代高道。“道箓司之下的府、州、縣各司的設置情況,史書缺乏完整記載,是全國各府、州、縣均設置?還是有條件者方設置?疑莫能定。推測當屬后者,即具有相當數量的宮觀和道士的府、州、縣設置,不具備條件者不設置,待條件具備后再設置。一般來說,內地漢族聚居的府、州、縣,宮觀和道士數量大都較多,在洪武十五年中央設立道箓司后,應相繼建立起府道紀司、州道正司、縣道會司,但史無記載,已不知其祥”。從中央到地方府、州、縣,建立了與行政體制相適應的四級道官體系。即備總樞道箓司,又有轄屬機構,上下互為一體的有機管理體系,建立如此嚴密的、綱目齊備的道官制度,是以往各朝不多見的。各級道官有明確的品階俸祿。明朝道官品秩皆備,則表明道官機構更衙門化,道職更官吏化。另外,道官的銓選任免成制,考課有常,迂轉有序,衣飾傘蓋有別,表明把道官完全納入政府官員的管理渠道。道官機構的設立及嚴密化,是明初集權政治發展的必然產物,是明王朝加強中央集權諸多政策的一項措施,是空前強化的專制統治在掌控統制道教事務層面上的一種折射。
二、道士管理制度——“度牒”制
鄭曉撰《今言》卷3記載:“王虎谷為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度牒。王晉溪問之日:‘兄謂此可塞異端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必有精通玄典者出于其問。今二氏之徒茍且為衣食計,尚不可遏塞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虎谷嘆服”。這段話透露三方面的含義:其一,佛道須度牒;其二,佛道之徒茍且為衣食計;其三,佛道與儒爭勝負。
明代僧道被列為專門一類戶口,是特殊人群之一。“凡民三等:曰民、曰軍、曰匠……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著籍。”管理僧道戶籍的主要是度牒制度。明代所定的道士管理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度牒”制。度牒制度出于三個目的:一是肅正僧界;二是與王朝財政收入問題有關;三是控制僧道人口。該制度開始于洪武五年,到洪武十五年建立僧、道箓司后,略近完備。洪武五年三月,“給僧道度牒”,當時禮部稱:“前代度牒之給,皆記名鬻錢,以資國用,號‘免丁錢。”太祖下詔廢除前代出賣度牒以增加財政收入的做法,發給僧道度牒,并著為令。“二十四年清理釋、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給牒。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試給牒,不通經典者黜之”。太祖以后,“每代統治者吸取前代的經驗,意欲通過嚴格獲證條件和完善發放手續等辦法,以繼續發揮其控制佛道發展的作用”。其獲證條件和步驟如下:
1、系籍:“入道之第一步”
“凡出家而尚未獲得度牒的初學者稱道童,俗稱徒弟。徒弟從師出家,寄名于宮觀,造籍上禮部聽候試經,唐宋時謂系帳,明代謂之系籍,是為入道之第一步”。明初,朱元璋父子對道童的條件作了些規定:其一,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其二,本人愿意,父母允許。其三,本人出家后,祖父母和父母有人供養。其四,鄰里保勘無違礙之事,并陳告有司得到許可。《明太宗實錄》卷205謂:“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鄰里保勘無礙,然后得投寺觀”。“符合上述條件,履行上述手續之后,始能入宮觀從師系籍,成為道童。道童從師期間的主要任務是學習經業,準備考試,時間為五年”。
2、考試:“成為道士最關鍵的一步”
系籍“作道童滿五年后,取得參加考試的資格。考試是道童能否獲得度牒成為正式道士最關鍵的一步,為明代諸帝所特別重視”。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明太祖在歸并寺觀的詔令中,即強調指出:“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洪武二十七年(1394)正月的詔令中,再次強調,僧道行童、道童隨師習經三年(后改為五年)后,“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為民”。
永樂十六年(1418)十月,成祖命禮部榜諭天下之文中,規定行童、道童“從師授業五年后,諸經習熟,然后附僧箓、道箓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為民”。
宣宗宣德年間、英宗正統年間也強調考試,亦有與之相關的規定。“正統十四年(1449)四月,再次規定考試之前,由僧道衙門進一步審查參加考試者的資格,并規定了應考的經典。”“除規定考試經典外,又規定實行兩堂考試,一為僧道箓司的初試,二為禮部的復試。明王朝之所以如此重視僧道的考試,其主要著眼點并不是提高僧道的素質,而是以之為控制僧、道數量和防止刑徒和反政府力量混入僧道的一種手段。”
3、給牒:“入道的最后手續”
“道童經過考試中式后,發給度牒。發放度牒的部門是禮部。道童獲得度牒,即完成了人道的最后手續,其道士身份才最后獲得國家的承認”。但是,道童能否取得度牒,又要受下列兩個制度的制約。
第一,定期給牒制。洪武初年規定三年一給牒,永樂中改為五年一給,后冒濫益甚,天順二年(1458)改為十年一給,弘治初,因左都御史馬文升奏,孝宗停止十年給度事例。至七年,又因禮部禁約各處僧道不許來京請給度牒。“仍將十年一度事例停止,待后僧道原額不足另行具奏定奪”。《明孝宗實錄》卷114謂:“太祖皇帝有三年一給度之制,以后日漸增多,故太宗皇帝改為五年一度,天順二年,因冒濫益甚,英宗皇帝復改為十年一度,皆斟酌多寡,因時制宜,初無一定之制,況三年所度止三五百人則三十年不過三五千人,五年所度止一萬人,則五十年不過十萬而止,使此制常行則額數必不過濫”,“我朝給度舊制甚嚴,額數不足,則照缺度補,無則止”。按當時的體例,額數不足之日,方許所在官司照依額內名缺,起送赴部,考中,給與度牒。“因此,即使道童從師五年期滿,亦必待國家給牒之期,才有參加考試取得度牒的機會。”第二,僧道總額。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釋、道二教……凡僧道,府不得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試給牒,不通經典者黜之。”永樂中亦有類似規定。“即全國僧道總額數分別不得超過36000余名。只有當此額數不足時,才能按缺額之數發放度牒,如果總額數已滿,即使考試合格,也不能獲得度牒。上述這兩條制度,顯然是防止度牒發放過濫的有力措施,是控制僧道發展過快的有力保證。”
“天下僧道,額設不過三萬有余,自成化二年以來,三次開度已逾三十五萬,正數之外增至十倍,妨政害治莫甚于此。……陛下以廢直等請給度而令禮部議處不許過濫,是已洞見其弊矣”。
明朝嚴禁私度,并不斷重申之。太祖對私度者的懲罰是“杖八十”。洪武三十年頒行的《大明律》對違反國家規定的度牒的行為規定了懲處辦法,其中包括:“凡寺院庵院,除現在處所外,不許私自創建增置。違者,杖一百,還俗。僧道發邊遠充軍;尼僧女冠入官為奴。若僧道不給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長,家長當罪。寺觀住持及授業私度者,與同罪,并還俗。”
宣德十年(1435)十一月,英宗下詔:“禁僧道私自簪剃,及妄言惑眾者。從給事中李性言也。”天順八年(1464),“令各處僧人年二十以上無度牒者,即便還俗,有隱瞞年歲者,并其師治罪”。另外成祖、宣宗都發過嚴厲懲處私度的詔令。“盡管明前期諸帝屢下禁令,但卻禁而不止,特別是在英、代以后,私度更加泛濫,原因是統治者官賣度牒愈演愈烈,私度也就暢通無阻,無暇顧及了”。
三、宮觀管理制度
“明初既面臨元代寺觀大發展的現實,又有元末以來民間秘密宗教存在的威脅,所以更加重視控制寺觀數量的增長和加強對他們的管理。”明初采取歸并寺觀的措施。元代的僧道綱紀紊亂,僧道又由元末的兵亂失去寺院而雜居民問。僧道遠離出家生活,而世俗又染于游食的不良風氣。朱元璋對此種社會現實的后果洞若觀火。鑒于此,太祖決意整理寺觀,“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因此令衙門調查全國寺觀。以此調查為根據,于洪武二十四年整理全國寺觀,設《歸并條例》,將小寺觀歸并于大寺觀而使其凈化。僧道居市者聚三十人以為一寺,二十人以下者悉令歸并。《釋鑒稽古略續集》記載:“凡僧之處于市者,務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此項措施的目的有二:其一,可以減少寺觀的數量;其二,便于對僧道進行集中管理,以防逃軍、逃犯和“邪教”分子混跡釋道。“在加強僧道管理和防止逃軍、逃犯“邪教”分子混跡方面,最重要的制度是令僧道箓司造‘周知冊”。“這是輔行度牒制的一項重要制度”。據《大明會典》稱,此制始于洪武五年(1372)。而據《明實錄》記載,則始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
“周知板冊”,又稱“周知冊”,朱元璋令僧、道箓司將在京和各府州縣寺院之僧道造成名冊,備載其籍貫、姓名、字行、父兄名號,以及入僧道年月與度牒字號等,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比對名冊,如有不符,即為偽冒,準有司送京治罪。頒行“周知冊”的時間有兩種說法:一為《大明會典》稱,此制始于洪武五年(1372);一為《明實錄》記載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祖實錄》卷223記載:“凡游方行腳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隱者,罪如之”。
另外《釋鑒稽古略續集》卷二亦有相關記載:
“命僧、道箓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到處,即與對冊,其父母籍、告度月日如冊不同,即為偽僧”。“試經給僧度牒,敕僧箓司,行移天下僧司,造僧籍冊,刊布寺院,互相周知,名為《周知板冊》”。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禮部再次榜示天下:“若游方問道,……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同者,獲送有司”。
對于朱元璋的“‘歸并條例和‘周知冊的用意,嘉靖中之詹事霍韜的一次上疏中,曾有過解釋,可謂一語破的”。《明實錄》記載:“洪武中給僧道度牒,令僧道箓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如有不同,即為偽冒。有令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者)一所,并居其眾,毋容散處,蓋作奸倡亂自易覺察也。宜遵行之”。
宮觀之組織,“明代正一派宮觀院庵,可考者約有六十四,其中以大上清官與大真人府最為重要。大上清官乃正一派規模最巨之宮觀,大真人府為天師所居,正一派教務發展的重心”。
第一,明代大上清宮之組織
大上清宮法員其定額職掌舊無考證。根據宋代道士傳記所載,宋代大上清宮的道士職稱有:道正、知宮、副知宮、管轄、都監等職。宋時則有留用光、薛應常為管轄,洪微叟為都監,王襲明為道正,郭保寧為監宮,鄭保和、徐處尚為知宮,李元溢為副知宮,呂惟一為知觀等職。
元代史料所載僅有提點一職。元代有道士張聞詩、李宗老、李嗣仙、詹益老、黃自明、方南翔等曾擔任本宮提點。
明代此宮的職事及員額分布:提點一員,提舉一員,副宮二員,上座二員,監齋一員,直歲一員,掌籍一員,書記一員,知事六員,知書一員,知庫一元。提點是大上清宮住持,為正六品,明代任大上清宮提點可考者有:洪武年問張友霖、張迪哲;永樂年問有吳伯理,嘉靖初年張定漢、陶隱賢、王時佐;嘉靖三十七年(1558)張拱極;崇禎年問何濤曙。隆慶二年(1568)革天師封號后,以張國祥嗣教,兼任大上清宮提點。
第二,明代大真人府職事員額
明代大真人府之職事員額有:知印、都目、司務各一員,掌事四員,贊教、掌書各二員,知事四員。另有法篆都提點,法箓局提舉、監紀二員。崇禎年間(1628—1643)增設監紀,相傳52代張應京募兵捍衛鄉里,什伯之長稱為監紀,而后沿誤成大真人府中法官之首職。贊教、掌書二職,設于明太祖洪武元年,太祖即位,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入賀,太祖特設此二職,“以佐理玄教之事”,王圻撰《續文獻通考》亦記載:“洪武元年以張正常為真人,……改天師印為真人印,秩正二品。其僚佐日贊教,日掌書”。任此二職者,必以大上清宮明習教典的道士擔任,由皇帝任命。作為開國的朱元璋“深知宗教的影響力。因此,對于流傳千余年的正一派不無防范之心,其設贊教、掌書二職,名為輔佐天師掌理教事,然實有監督的作用”。《龍虎山志》卷8記載:“正統中敕以上清宮道士高縉云、周應翰為贊教,官彥矩、席克中為掌書。成化二年敕以道士鄧玉元、王紹通為贊教,林智茂、朱文吉為掌書;嘉靖五年,敕以道士傅德巖、邵啟南為贊教,余永壽、詹望奎為掌書。是二員者必以上清官明習教典之法員為之,而受命于天子者也”。知印職責為掌管大真人印信的封開;都目掌大真人府地畝租稅錢糧的出入;掌事掌賚捧表簽及一切差委之事。《龍虎山志》卷8記載:“三項皆以在家之人克補,而舊志乃以冠于贊教掌書之上,失其倫矣。蓋府僚原分出家在家二項。知印、都目、掌書、監紀等俱屬在家;贊教、掌書、知事、法箓局、提舉俱為出家”。
四、明王朝道教管理制度的貫徹實施
明代的道教管理制度應該說是控制道教發展的較好的辦法,如果嚴格執行實施,應當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實際情形卻不然,那些制度大都未發揮應有的作用,原因無他,是明代統治者自己并未認真予以貫徹,有時還親手破壞了他們。”按照明代度牒制設置,禮部發放度牒即受額定總數,又受定期給度的限制。只有這樣,度牒制度才能起到控制佛道的作用。但事實上,除了太祖和成祖嚴格執行外,其后諸帝皆有制不依,甚至濫發度牒,使其遭到巨大破壞。“這又表現在:非給度之年零星賜牒、提前給度或給牒超過定額及政府出售度牒。”
1、度牒制的實施
政府出售度牒與度牒制與生俱來,在唐代即已出現。至宋室南遷,疆域漸小,經費支絀,便以出售度牒作為解決財政困難的重要手段之一。明代開國之初,太祖深知其弊,于洪武五年(1372)下令廢“免丁錢”,不準以度牒鬻錢。但幾朝過后因財政問題,同樣落入鬻牒的境遇。
明·鄭曉所撰《今言》卷2日:“馬鈞陽嘗上疏言,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該僧三萬七千九十余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人,共該五十余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余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況不耕不織,賦役不加。軍民匠灶,私自披剃而隱于寺觀者,又不知其幾。創修寺觀,遍于天下,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于僧、道過半,乞嚴加禁約”。明代鬻牒,始于代宗景泰年問,至憲宗成化年間大盛。孝宗年問,鬻牒之風稍落,至武宗朝又起。“政府出售度牒之風興起之后,不僅度牒制之各種規定被破壞無遺,而且在他的影響下,社會上出現轉手倒賣度牒的現象……偽造度牒賣錢的現象。這樣一來,不僅天下度牒滿天飛,完全喪失其控制僧道發展的作用,而且度牒本身也不再是僧道的身份證明書,僅是具若干交換價值的紙片而已。原來的度牒制度,實際已蕩然無存”。
2、宮觀管理制度的實施
太祖和成祖之時,曾用歸并寺觀和禁止私建等措施,目的是把寺觀數量控制在額定的范圍之內,但時隔幾代之后,此制度的實施即出現了偏離。后繼者們大量敕建寺觀及給寺觀賜額。在他們的影響下,宦官們也大建寺觀。民間的私建也連年不斷。如此以來,其結果無疑與太祖和成祖意欲限制寺觀額數之初衷南轅北轍。“明初所定的道教管理制度,自英、代以后漸遭破壞而被擱置,原擬限制道教道士和宮觀發展的各種規章,大都變成一紙空文。在此情況下,道教在明代的發展也就愈來愈濫,道士的素質逐步下降,使道教逐漸失去其活力”。
五、結語
總的來說,明統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唐宋時期的崇道政策,利用道教以及儒釋二教作為統治工具。這既與宗教的社會功能和政治作用有關,亦與明統治者自身的宗教信仰有關。在明中葉以前,統治者對道教的態度是以崇奉為主。同時,明統治者也清醒地認識到,對于一個政權來說,宗教固然有用,但利用不恰當也會有害;宗教固然可以成事,同樣亦可以敗事。尤其是,明初宗教界的狀況不盡人意,內部秩序相當混亂,某些僧道對明政權懷有敵意,甚至利用民間秘密宗教組織起義。基于此,明統治者對宗教可能包含的某些負面作用有所警覺,故對其采取了利用與管制并行的策略:一方面利用宗教為自己的統治服務;另一方面,對其進行管制,使其作用的發揮不至于逾越一定的界限。“這種崇奉、利用與管制相結合的宗教政策決定了道教在明朝的基本命運:能夠在較優裕的環境中生存,但在思想不可能有重大突破”。
參考文獻:
[1]《漢天師世家》卷3,《張宗演傳》,《道藏》第34冊,第829頁
[2][3][5][11][13][14][15][24][28][29][48][51][57][64]《明太祖實錄》,史語所校印本,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