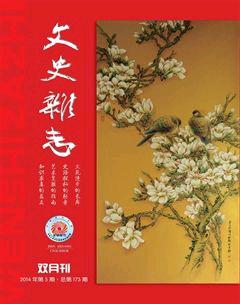為藏經洞“罪人”王道士辯誣
朱小農
敦煌莫高窟,因為有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代壁畫、塑像的“千佛洞”和埋藏宋之前5萬多件古代文獻資料的“藏經洞”,被譽為20世紀最有價值的文化發現,由此衍生專門研究藏經洞典籍和敦煌藝術的學科——敦煌學。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87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與一位姓王的道士有重要的關系。王道士是發現莫高窟藏經洞的功臣,但同時又因為那些珍貴資料在發現后的散失而讓他在某些人的眼里成為莫高窟藏經洞的罪人。《辭海》“莫高窟”說:“窟內歷史文物和藝術品遭到帝國主義分子的嚴重破壞,斯坦因、伯希和、華爾納、鄂登堡等人曾盜竊大量的珍貴文物。”[1]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影響很大,其中有一篇《道士塔》就明確將“盜竊大量的珍貴文物”的罪責直指王道士,說:“王道士是有名有姓的莫高窟的罪人。”[2]
可是,如果我們將王道士發現莫高窟藏經洞后的所有活動進行認真的、客觀的分析,就很難認同諸如余秋雨先生這樣的認識。
一、偶然間的重大發現
王道士名叫王圓箓,湖北麻城人,曾經在肅州(治今甘肅酒泉)當過兵,退伍后無事可做,就當了道士。他游歷到敦煌,在莫高窟里住宿下來。王道士是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人。按照沙武田著《藏經洞史話》的考證,藏經洞的發現經過大致有四種說法:一是人力清沙說;二是流水疏沙說;三是抄經人敲壁說;四是地震破壁說。[3]但不管是以何種形式發現的,王道士都是發現者之一,這是基本無爭的事實。
當時的莫高窟十分荒涼,崖間上的通道多數已經毀于戰火,一些洞口已經崩塌,底層的洞窟已為黃沙掩蓋,這里只有一些粗通漢語的藏傳佛教寧瑪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由于他既懂漢語,又能誦道經,漸漸地,便以忠厚、質樸、誠信、謙和、刻苦、奉公贏得了當地道、佛不分的信眾的敬重。在并沒有任何人對其封號的情況下,他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負責任的住持,于是就有很多人請他去做禮懺,香火漸盛。
王道士以中國農民對宗教極其單純的虔誠和勤勞負責的精神承擔對莫高窟的日常管理后,自覺踐行了三大任務:清理長期被落沙封堵的洞窟;率領僧眾四處奔走,苦口勸募,尋求布施;將募化得來的錢財盡其所能,搶救修復坍塌的洞窟和其中的塑像。敦煌地區人煙稀少,甚至數百里中無村戶,能夠獲得多少布施和化來多少善緣是可想而知的。而偌大的洞窟區需要投入巨額資材實施修繕,還要滿足和尚們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開支,也夠難為這個農民出生的道士了。
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5月26日,王道士偶然發現了掩藏在莫高窟第16窟壁畫背后的另一窟,即藏經洞。塵封千年的文化藝術寶庫隨之重現世間。王道士看到,在一扇緊閉的小門后有一間不大的復室,高約240厘米,寬約270厘米。地方雖然不大,然而里面的東西卻令人驚異不已:這個小洞里整齊地堆放著無數的白布包,每一白布包內裹著十幾卷古文書,還有平鋪在布包下的絹幡佛畫,以及古木刻印刷品,銅和木制的佛家法器等物件。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遺書以佛教典籍最多,還有天文、歷法、歷史、地理、方志、圖經、醫書、民俗、名籍、賬冊、詩文、辭曲、方言、游記、雜寫、習書,共達5萬多件,成為多種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據和補充參證,其主要部分又是傳統文獻中不可得見的資料,價值尤為珍貴。敦煌遺書以漢文最多,還有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闐文、梵文、吐火羅文、希伯來文等多種古代民族文字,成為研究這些古代民族語言文字和民族歷史、宗教、文化的珍貴資料。它又具有民族學價值和國際意義。敦煌遺書以卷軸裝為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還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繡本,在書籍發展史及書籍裝幀史、印刷史上都是難得的實物資料。
這就是舉世聞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原來在公元1006年(宋景德三年),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滅掉于闐佛教王國后,在佛教像法滅盡思想的影響和穆斯林東進的威脅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將公元4~11世紀的一些重要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5萬余件集中起來,收藏在原來存放各寺的剔除的經卷、外典、過時文書、舊幡畫、佛像的洞窟中(今編號為第17窟),并將該窟洞口封閉起來,并做了必要的掩飾。
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提供了數量極其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
二、讓政府保存“文寶”的努力
不可否認,藏經洞的許多文物最早是通過王道士的手流散出去的,但如果因此就把所有罪責歸在他一人身上,實在不公平。有大量資料顯示,在發現藏經洞后的7年間,王道士為保護藏經洞文物做出了局外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王道士被自己的發現驚呆了。雖然他的文化水平使他壓根就不知道這些藏品的文化價值,但還是隱約感覺到這些東西應該是有用的。他首先請來了敦煌本地的紳耆征詢意見,通過大家商議認為,這是先人們的功德物品,應該妥善保存在原地;如果讓它流失在外,那就是罪過,所以一致意見還是留在窟內為好。這是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后迅速采取的第一個保護措施。
王道士采取的第二個保護措施是盡快向官府反映,并數次逐級寫報告、送樣品,要求將這些文寶交上級官府保存。
王道士滿懷信心地步行50里,專程拜訪縣令嚴澤,還專門挑了兩卷經文帶去。然而這個縣令卻把兩卷經文當作發黃了的廢紙,一笑了之。王道士失望而歸。
1902年,到了發現藏經洞的第三年,敦煌來了一位進士出身、諳熟金石的新縣令汪宗翰。王道士重拾信心,向其苦心陳情,希望得到一筆保護費用。誰知汪縣令視察后,挑選了一批經文帶走,然后對王道士說:“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可是怎么保存?如何看管?王道士伸長脖子等待,卻沒有下文。
王道士仍不甘心,單槍匹馬,趕赴酒泉叩見他當兵時的老上級——肅州道臺廷棟。這位道臺是有學問的。他仔細觀看了經卷,最后卻只從書法欣賞的角度認為,這種經卷寫得還不如他自己的字,頗為輕視。盡管如此,他還是念及老部下從數百里之遙送來經卷的辛苦,將藏經洞的消息上報了甘肅藩臺,也建議藩臺將這些文寶運省妥藏。
王道士一次次求助朝廷和官府,想讓政府管理藏經洞,結果卻同樣令人傷心。如此對牛彈琴,究竟是大清朝根本不需要這批文物,還是王道士根本不該發現藏經洞?王道士百思不得其解。
發現藏經洞的消息傳到甘肅學政、金石家葉昌熾那里。他通過縣衙要了一些經卷。他看到部分敦煌遺書后,深知這些文物的重要價值,立即向甘肅省府當局建議,把藏經洞的全部文物運送到蘭州保管。
甘肅藩臺先后收到葉昌熾和廷棟文武二官的報告,再無理由推脫;但是,敦煌到蘭州路途遙遠,需耗運費,估計要五六千兩銀子。于是,甘肅藩臺在1904年以銀兩難籌為由,僅向敦煌縣令汪宗翰發出一張“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而沒有任何保護的實質舉措。
可憐的王道士只能滿臉困惑,每日提心吊膽,面對洞中的5萬件佛經字畫國寶,不知所措。然而,他仍以對佛的一片虔誠之意,苦苦支撐著這塊圣潔之地,數十年一以貫之,直至老去。
三、藏經洞文物的流失
肅州道臺廷棟雖然認為藏經洞經卷的書法還沒有他寫的字好,但他是有學問的官吏,知道這些經卷是有價值的。這時正好有個比利時籍的稅務官要回國,來向廷棟辭行,于是廷棟把一部分經卷送給了他。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于是被外界所知。
從此以后,一批又一批外國人來到敦煌攫取寶藏,其中“著名”的有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美國人華爾納。其中,斯坦因五次到敦煌,獲得的藏經洞文物最多,也是“來到敦煌攫取寶藏”的代表人物。。
斯坦因是從他的朋友洛克齊那里聽到莫高窟的情況的。1907年3月16日,斯坦因來到莫高窟,此時,王道士已在藏經洞門上裝上門鎖,并親自掌管著門鎖的鑰匙。斯坦因騙取得王道士的信任讓后者拆除了封堵藏經洞的磚墻,向他打開了藏經洞之門。
斯坦因進洞之后,在昏暗的油燈下,看到“經卷一層一層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亂無章。經卷堆積的高度約有10英尺,后來測算的結果,總計約近500立方英尺。藏經洞的面積大約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間僅能勉強容得下兩個人”。[4]由于洞窟太小,光線又暗,不便閱讀,王道士就允許斯坦因把幾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間小屋。之后,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寫本,拿到小屋里讓斯坦因研究。由于寫卷太多,斯坦因放棄了原來準備給每個寫本都編出目錄的打算,只是從他的考古學標準出發,盡可能多、盡可能好地選擇寫本和絹、紙繪畫。最后斯坦因捐出一筆錢作為酬勞,送給王道士,并約定在離開中國之前,除他們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這些寫本、繪畫的來源。對這筆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報告里寫道:“當我今天回過頭來檢視我用4錠馬蹄銀換來的無價之寶時,這筆交易簡直有點不可思議。”[5]
6月中旬,斯坦因帶著從王道士手中獲得的藏經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險”。4個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時,又從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書。16個月后,裝滿24箱經卷和5箱經過仔細包扎好的絹畫、刺繡等藝術品,便平安地存放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里了。
第二次中亞探險結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寫出了此次考察的個人筆記——《沙埋契丹廢墟記》(兩卷本),1912年在倫敦出版。
此后,斯坦因又三次來到敦煌。斯坦因先后到過莫高窟五次,所得共計9000多卷寫本和500多幅佛畫,全部運到了倫敦大英博物館。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報告《西域考古圖記》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1908年2月,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率探險隊到達敦煌。伯希和經過3周調查選出最有價值的文件約二千余卷,此外還有二百多幅唐代繪畫與幡幢、織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伯希和與計劃重建莫高窟的王道士談判,最后以500兩銀子的價錢“買”了這些文物。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帶走的文件中有很多屬于價值相對不太高的東西,而通曉包括中文在內的13國語言的伯希和選出的文件則全是珍品,其中也包括新發現的唐代新羅僧人慧超所著《往五天竺國傳》。他將這些文物全部運往巴黎,藏入巴黎國民圖書館。同時,他詳細查看了所有洞窟,對每個洞窟作了描述,特別是詳細記錄了洞窟中的壁畫題記。同年伯希和在《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發表《敦煌藏經洞訪問記》。[6]
1909年,伯希和把他所得的敦煌文物安全運回國之后,帶了極少的一部分漢文古寫本來到北京,給羅振玉等文人學士觀看。到此時,清政府才為之震驚,正式撥款6000兩白銀,命令敦煌知縣盡數搜買,運回北京。但這樣一來,又出現了另一種讓人痛心的現象:所有寫本都用席子草草包捆,用大車裝運。大車停在敦煌衙門的時候,經卷被人偷去不少,再經過沿途大小官吏等層層盜竊,運到北京,只剩下8600多殘卷。就是這8600多卷也未能保全。那些學部官員,把較有價值的古寫本挑選出來據為己有,然后把比較長的卷子撕裂為二三卷,以湊足原來8600多卷之數。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從王道士處,又弄走約600件經卷。1914年俄國人奧爾登堡又從敦煌拿走一批經卷寫本,并進行洞窟測繪,還盜走了第263窟的壁畫。1923年,美國人華爾納到達莫高窟時,藏經洞已經空了,于是他把目標轉移到了那些不能移動的塑像和壁畫上,用特制的化學膠液,粘揭盜走莫高窟壁畫26塊,共計3萬多平方公分。
四、幾點認識
藏經洞許多文物的流失,的確與王道士有關,但因此就將他確定為“莫高窟的罪人”,卻是不符合事實的。
作為一個沒有多少學識的王道士,他在發現藏經洞后,沒有據為己有,而是表現出很強的“組織紀律性”,首先報告了官府,這一點對他來說已實屬難得。再說他這是在官府沒有重視的情況下,非常辛苦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報告。是腐敗的清政府未能對其進行應有的保護,才致使藏經洞中的大批敦煌遺書和文物先后被外國“探險隊”捆載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運至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莫高窟的壁畫和塑像也遭到劫奪與破壞。
如果王道士真是“出賣”寶藏,那么,知道這些文物價值的斯坦因等人,還能大搖大擺地經過海關將文物運出,運出前還在北京六國飯店舉辦公開展覽嗎?當時大清達官貴人參觀的摩肩接踵,卻沒有一個人提出指責,也沒有人說王道士做得不對。直到斯坦因將藏經洞的珍寶公之于世界,全世界都為之發瘋,造成美國人、俄國人、日本人等許多國家的探險家、學者蜂擁而至,來到莫高窟。這時也沒見政府采取什么保護措施啊!
即便說王道士是“出賣”寶藏,他也不是為中飽私囊,而是為了籌錢修繕莫高窟。從當時外國探險家照相留下的黑白照片上可以看到當時的破敗景象:淺道塌陷,門板破落。是王道士用賣文物的錢對洞窟進行了有益的保護。王道士把從外國人手上得來的很少的錢用來看護那些洞窟,還在藏經洞的對面修了一個道家的“三清觀”,他自己一直住在那里,守護著莫高窟,直至老死。要知道清政府沒給他一分錢經費做這些本不該他做的事。
關于王道士修繕莫高窟的史實,已被多數專家所確認。可悲的是由于見識所限,這種修繕大都是拙劣的和破壞性的。不過,和王道士的無知、可悲相比,那些貪官、昏官,還有腐敗的政府,不是更可惡嗎?
我們再假設,如果王道士是一個文物專家,那么這些文物可能會很快大批消失掉,甚或可能永無見天之日。如果王道士是個官員,那么我們現在則連莫高窟也可能看不到;因為封建時代官員的貪婪是誰都清楚的:他要么把畫據為己有,要么把文物賣掉,把錢貪污掉,再一走了之,肯定不會用那筆錢來修復莫高窟。后來官府命令運送去京城保管的那些文物,不是一路被官員層層巧取豪奪嗎?那些丟失在中國的文物,現在還沒聽說找回一件!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的散失,對中國文化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但客觀上卻推動了東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它們進行整理和研究,并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是敦煌學的興起引起學術界對敦煌莫高窟的重視。
藏經洞文物的發現與散失已經是一個世紀前的事情了,歷史的真相早就應該大白于天下,一個世紀前當事者的功罪也是到了明判是非的時候了。而今,莫高窟的不可移動文物大體還在,正在供我們參觀賞析。可是,從藏經洞中取出的數萬件可移動文物中的絕大多數卻散存于世界13個國家的幾十個機構和不少私人手中,至今無法回歸,有的甚至難覓蹤跡,令人扼腕嘆息。然而,歷史長河中的事實,不會因為我們的惋惜、抱怨、憤怒、甚至悲傷而改變,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尊重歷史,并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
注釋:
[1]《辭海》“莫高窟”條,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
[2]余秋雨:《文化苦旅》,東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
[3]參見沙武田:《藏經洞史話》,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4][5](英)斯坦因著,巫新華譯:《西域考古圖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6](法)伯希和著,耿昇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紹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