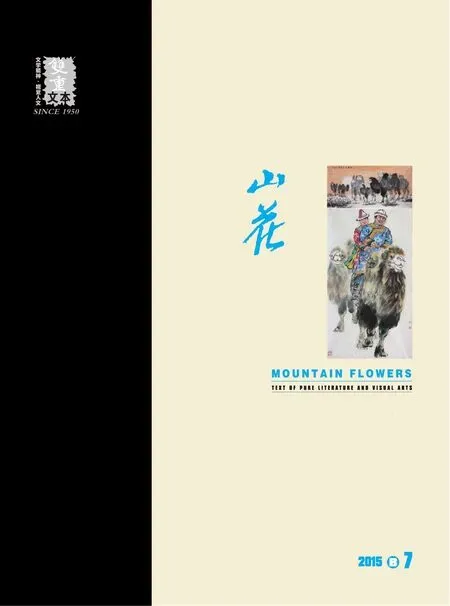在石頭下面
宇向
一
“在夜里也能聽到海浪拍岸的巨響”,對于現(xiàn)實,這樣說顯得夸張。夜里僅僅是能“感受”到驚濤拍岸,寂靜時能,起風(fēng)落雨時能,夢里能……在我幼年寄居的島嶼上,耳邊的巨響一定因無所不在的細(xì)節(jié)暗示而在某個敏感個體里滋長、漫延。
二
我曾聽在平原長大的朋友對我說起孩童時對山和海無限地向往、想象,也聽過雪山藏區(qū)的朋友說起自小就想翻過眼前這座山看看外面有什么,父親告訴他翻過這座山還是山,別的大人也告訴他那將是一座山又一座山,沒完沒了的山,直到那個唯一的出外者歸來,改變了敘述。唯一的出外者是描述外面世界的絕對者。
不同的是,我寄居在小島上,它是一種山脈,大海的潮起潮落和風(fēng)平浪靜給了我平原也給了我群山。我看得足夠遠(yuǎn),能看到變換的藍(lán)與藍(lán)匯于隱約的一線,幸運(yùn)時還眼見虛無:海市蜃樓。我所能夠向往的是去不同的地方看看,看不同的海,我現(xiàn)實的立足點基于一種海岸線。
其實我不曾離開。我生來就是那個“被驅(qū)逐的孩子”,被棄于孤島上。我想這就是我寫字的命運(yùn)的基因。在孤島,對于整個世界,我是唯一的出外者,我是我言說的絕對。這足夠的遠(yuǎn)、這豐富的空曠、這無情、這幸運(yùn)一見的虛無,恰恰是為了將我引入它的極端,它的另一頭,我寫作的立足點,基于怎樣的卑微、壓抑與黑暗之地?
三
2003年寫作初始,我寫過一篇短文《在石頭下面》。
我幼年很重要的一個記憶是外祖父蓋房子。院子里一下子堆滿石頭,樸素又好看的石頭是人們從海邊的山崖上采來的,帶著舊年海蠣子的殘骸。外祖父說這些石頭已被他計算過,不多不少,正好夠蓋一間廂房。
近一個月的時間,人們把形狀各異的石頭拼湊起來,不得已才去改變石頭原來的形狀。他們是能工巧匠,這點從那些長長的補(bǔ)抹石縫的水泥條紋就可以看出,那些過于曲折的條紋像極了蛇行的痕跡。
房子蓋好后,院子里多出一塊石頭,接近正方形。外祖父把它搬到墻根去,搖著頭說,它是怎么多出來的呢?
它是怎么多出來的?我想著這個問題,外祖父不再提這事。那塊石頭在那里,好像它很久以前就在那里一樣。也許在外祖父看來建成了房子的石頭才是真正的石頭,這一塊石頭不是真正的石頭。
我喜歡廢棄的東西,因為它們會被我記住。這塊石頭成了我的凳子和桌子,玩累了我就坐在上面歇息,它吸引我也一點一點吸走我的體溫,我在上面捏泥人、一個人過家家,當(dāng)我趴下用鼻子聞一聞它時,它就散發(fā)出舊海水的味道。有時,我坐到對面無花果樹粗矮的樹杈上,很長時間盯住它看,或者看看其他的東西偶爾也看看它,并想一想它是怎么多出來的。
終于有一天,我把石頭半掀了起來,光線一下子照進(jìn)去。我看到一群西瓜蟲、螞蟻,還有很多很多沒有名字的小蟲子,它們飛快地逃跑,向更黑的地方——我掀不動的地方。小蟲們跑進(jìn)黑暗,光線下暴露著腐爛的草根、蟲皮、死蟲子和玉米餅的渣子……后來我就經(jīng)常去掀動那塊石頭,看慌亂跑動的蟲子,我一邊吃力地干著這件事一邊想我長大以后一定能搬起這塊石頭,那時就會弄明白小蟲們跑到哪里去了。
大約在我6歲的時候,爸爸從城市來到鄉(xiāng)下老家,他突然出現(xiàn)在我的面前就像我掀開那塊石頭一樣掀開了我的生活,強(qiáng)烈的光線一下子進(jìn)來,我睜不開眼睛,我想和那些小蟲子一起逃跑,跑到黑的地方去。而我沒有力氣再將那塊石頭掀開得更多,那更黑的地方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最終我還是被我的爸爸從“石頭底下”拽出來,帶到城里去了。我被徹底地暴露在我不熟悉的光線下,開始了我并不健康的成長。
我后來的繪畫和寫作都和我的不健康有關(guān)。我寫作,它是我目前為止可以找到的通往我的石頭下面最隱秘的一條路。
四
我寫作,我仍在為自己構(gòu)建個人島嶼,在離我童年越來越遠(yuǎn)的地方,我重建它。回歸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