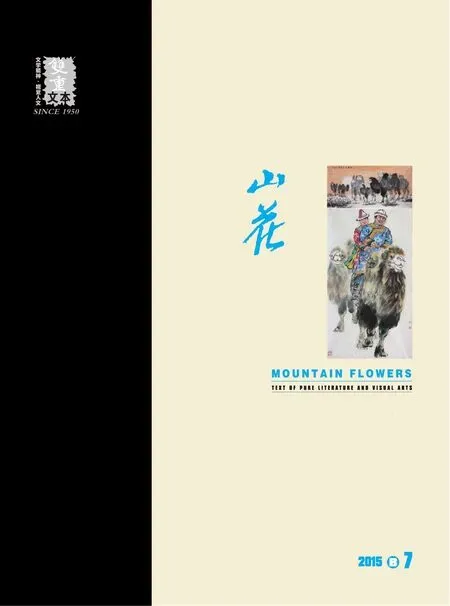論沈從文文學創作中的“反智主義”傾向和價值意義
黃高鋒
“反智主義”的概念厘定
“反智主義”一詞,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1962)一書而走紅。該書曾榮獲美國普利策大獎,隨之在美國傳媒界掀起了一股霍夫斯塔特熱。霍夫斯塔特提出“反智主義”這一概念是有其特定時代背景的。他曾經明確指出,創作此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回應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和知識分子狀況。作為一位極富洞見性眼光的歷史學家,霍夫斯塔特深刻捕捉和洞悉到了美國社會結構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和潛在隱患。作者以筆為劍,試圖厘清美國文化傳統中不尊重智力的反智主義源流。“反智主義”是與“理智主義”或“理性主義”相對而言的,是一種非常復雜的文化現象和思想傾向。在學者余英時看來,“反智主義”并非是一種學說,一套理論,而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在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有跡可尋,并不限于政治領域。“它可以分為兩個互相干涉的部分,一是認為‘智性及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皆有害而無益。……另一方面則是對代表‘智性的知識分子表現一種輕鄙以至敵視。”作為一種非常復雜的文化現象,“反智主義”在政治、哲學、歷史、美學等諸多領域都有反映,它具有多種視角和復雜文化內涵。作為一種文化立場和價值取向的“反智主義”,應該理解為依據一定的價值標準對人類智性以及由此而來的知識崇拜與技術迷信的心態所表露的一種質疑和批判的態度。這種態度并不以取消智性為最終目的。就文學創作而言,“反智主義”傾向也滲透到一些文本中,彰顯了作家復雜的價值取向。
沈從文文學創作中蘊含有“反智主義”傾向
縱觀中國現代作家,本文認為,沈從文的創作呈現出一種復雜的“反智”敘事特征,具體表現在四個層面:一是對“知識”、“智性”的質疑和反思;二是對“知識分子”的反思和批判;三是對近現代教育的反省和憂慮;四是對近現代文明(文化)的抨擊。
作為一名現代作家,沈從文深刻洞悉到了人類“知識”、“智性”背后所隱含的危機。他選擇了以文學這種特殊的藝術形式對人類理性和科學知識進行質疑和反思。與傳統的“知識觀”不同,沈從文對“知識”有著新的發現和獨到的見解。他認為:“……知識積累,產生各樣書本,包含各種觀念,求生存圖進步的貪心,因知識越多,問題也就越多。”
與“智性”相對照,沈從文更青睞于“感性”。他是一個具有濃烈感性色彩的作家,極富詩人氣質。他早年充滿感性的社會人生經驗,他對感性的大自然萬事萬物充滿了好奇心和神往,他筆下的湘西文學世界感性生命個體形象的生動塑造,他充滿感性色彩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無不昭示和體現著沈從文的個性特點。沈從文正是以感性生活經驗和生命個體來對抗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
知識分子是人類知識和“智性”的承載者,歷來被人們視為“道德的良心”,是人類基本價值的維護者。沈從文深刻洞悉到了代表社會良知和民族希望的知識分子的理性精神的退化與獨立人格的萎縮,他以筆為劍,對知識分子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狀態展開了深刻反思和無情批判。在《八駿圖》、《道德與智慧》、《有學問的人》、《記一個大學生》《自殺》等作品中,通過細讀我們就會發現,作家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往往被作者有意無意地戲謔化、漫畫化和粗鄙化了。
沈從文名震文壇之時正是中國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受到西方工業文明沖擊開始發生巨變之時,社會和時代的巨變毫無疑問會給個人帶來精神上的反響和心理上的回應。沈從文敏銳地感受到了現代文明發展的脈搏,尤其是銳利地看到了現代城市文明病態發展的因子蔓延對人性的侵蝕,便用筆記錄下了他的前瞻性的思考。沈從文批判近現代文明(文化),主要批判的是其病態(病相),即“現代文明病”。現代都市是現代文明的化身,現代都市文明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沈從文首先將矛頭對準了現代都市文明,他對近現代文明的批判主要是通過對“城市人”來完成的。對都市文明最有力的批判是他發現了都市文明(文化)的“閹寺性”特征。作者在1935年發表的《八駿圖》中提出的都市“閹寺性”問題,是他對中國近現代文明(文化)批判的最有力的一點。沈從文在批判現代都市文明的同時,也深刻洞悉到了現代文明已經開始侵入鄉村,從物質生活習俗到精神生活狀態以至于愛情、婚姻、家庭都深受其影響。“‘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上等紙煙和各樣罐頭在各階層間作廣泛的消費。”
“反智主義”傾向在沈從文文學創作中的價值意義
1.文化預警意義
當今社會,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財富”的觀念深入人心。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國家發展改革和建設中擔負著重要責任和偉大使命。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崇尚科學、信仰知識的時代。但同時,就如同魯樞元在《生態批評的空間》一書中描述的那樣,當今社會“實用主義”、“工具理性”意義上的“科學”似乎成為了人們思考問題和行動的唯一“理性”,“隨著科學技術的節節勝利,隨著神學系統的土崩瓦解,對于某種超驗的東西——信仰,已在現代人的精神生活中退化乃至完全消失了。人們收獲的是知識以及由知識帶來的力量,失去的是精神上的虔誠、敬畏和信仰”。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核戰爭的威脅及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當這一切出現在人類面前時,人類才真正清醒地意識到,這個“無往而不勝的知識系統”似乎“存在著太多的漏洞”和隱患。人類在不斷追求文化前進的同時,也時刻以一種可貴的反省精神在反思著自身的文化。這種文化反省精神在現代作家沈從文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2.審美救贖意義
沈從文在文化反省的同時,也孜孜求索,致力于審美救贖。“救贖”的方式和途徑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此在式救贖、宗教式救贖和審美主義救贖。沈從文選擇了第三種:審美主義救贖。沈從文“反智主義”傾向的目的是為了審美救贖,也就是以審美的藝術形式(文學)來進行救贖,即他所謂的“重造”理想。“重造”包含了人性、生命、民族品德,進而實現對國家和社會的重造。沈從文決心要“用一支筆好好地保留最后一個浪漫派在二十世紀生命給予的形式,也結束了這個時代這種情感發炎的癥候”,“在充滿古典莊嚴與雅致的詩歌失去光輝和意義時,來謹謹慎慎寫最后一首抒情詩”。他以文學的方式展現了一個充滿了人情美和人性美的湘西世界,由此喚起人的感覺、想象,重新體驗、思考、發現生活,達到生命的明悟,激發生命來開動人生觀,從而重造人性、生命和民族、國家,試圖點燃萎縮的情感和壓扁的理性;他站在審美現代性立場,通過構筑一個詩意的、感性的、自然的審美世界,對現代性進行修復與救贖,不遺余力。蘇雪林曾經指出,沈從文創作的理想,“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邁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興奮起來,年輕起來,好在二十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權利……他很想將這份野蠻氣質當作火炬,引燃整個民族青春之焰”。endprint
3.思想折射意義
沈從文的“反智”敘事傾向,折射了其思想深處的復雜性和矛盾性。應該說,從“反智主義”角度切入,讓我們洞悉到了沈從文復雜思想的另一面。明確沈從文創作中的“反智主義”傾向對解讀沈從文的創作思想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沈從文的“反智”敘事并非是自始至終、一成不變的。在沈從文創作后期,盡管其思想中仍有“反智主義”傾向的余緒,但同時他為了實現“重造”的理想,又不得不依靠“知識”和“理性”的抬頭,把民族重造和國家復興的希望寄托在知識分子身上。從中也折射出了作為自由主義作家的沈從文思想的復雜性和矛盾性。
20世紀40年代后期,沈從文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兩年間,相繼發表了《從現實學習》、《(文學周刊)編者言》、
《一種新希望》等文章,就當時國內政治問題闡述了自己的意見。他從對國內政治的失望與不信任出發,將國共兩黨的戰爭說成是“民族自殺的悲劇”,“數十萬同胞在國內各處的自相殘殺”。他希望“理性”與“知識”抬頭,“用愛與合作重新解釋‘政治二字的含義”,以黏和“民族新的生機”,重造“民族未來的希望”。他將這一責任寄托在學有所長、有“理性”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身上。這種知識分子,應當是“游離”于國內任何政治派別(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和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種”政治勢力)之外的“第四種”力量。
在沈從文創作的后期,他的知識分子觀開始發生變化。早期他筆下的知識分子主要包括大學教授、作家、編輯和大學生等。他認為:“如不能在普遍國民中(尤其是知識階級中)造成一種堅韌樸實的人生觀,恐怕是不會有將來的!”這時,在沈從文眼里,知識分子仍然要擔當重任,成為民族復興的中堅力量。“沈從文對知識分子態度的轉變,一方面或許與他自己在社會上的際遇改變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對現代社會的認同和接納。現代知識分子的確立與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中國現代化的開始與發展。沈從文的這一轉變,意義非同尋常。”
4.題材創作意義
沈從文創作中的“反智主義”傾向對現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在整個抗戰及其后續的年代,知識分子成了一個社會處境十分尷尬的群體。一方面,民族獨立與解放的偉業需要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擔當重任;另一方面,歷史的基因卻使知識分子人性本質中脆弱、虛偽的一面在血與火的洗禮中暴露無遺。他們要么自視清高、高蹈孤傲;要么投機鉆營、自私自利;要么消極處世、軟弱無為,躲進‘圍城,茍且偷生。時代與知識分子的要求和知識分子的實際人格狀態發生了‘錯位”。沈從文為什么會選擇把知識分子作為重點書寫對象呢?按道理說,生活在城市中的有官僚政客、富商巨賈、普通市民、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而沈從文卻把大量的筆墨和心血用在了知識分子身上。筆者以為有以下三個方面原因:首先,沈從文對知識分子群體最熟悉,接觸最多,感觸最深,受傷害也最痛。其次,知識分子是民族重造的希望,是國家的中堅力量,在知識分子身上寄托著沈從文的重造宏愿和夢想。最后,也是知識分子的自省精神使然。沈從文主要從文化——心理層面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病態人格。他對現代都市知識分子階層集體心理意識和病態人格的挖掘,犀利尖刻,入木三分。
當今天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沈從文文學創作中的“反智主義”傾向時,我們發現,沈從文半個世紀之前對知識、“智性”的質疑和反思,對知識分子的輕鄙和批判,對近現代教育的反思和對現代文明(文化)的抨擊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精神盲點,有助于人們在追求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去理性審視和警惕“現代文明病”,有益于人類生態文明的平衡與人的全面發展。這是一種前瞻性的思維,而絕非“開歷史倒車”。研究沈從文創作與“反智主義”的關系,有助于我們今天在大力推動現代化的同時,去思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負面因素,去關注現代文明發展進程中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態。用沈從文的“反智主義”思維來觀照當今社會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完全可以成為當今構建文明社會,實現科學發展可供借鑒的重要資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