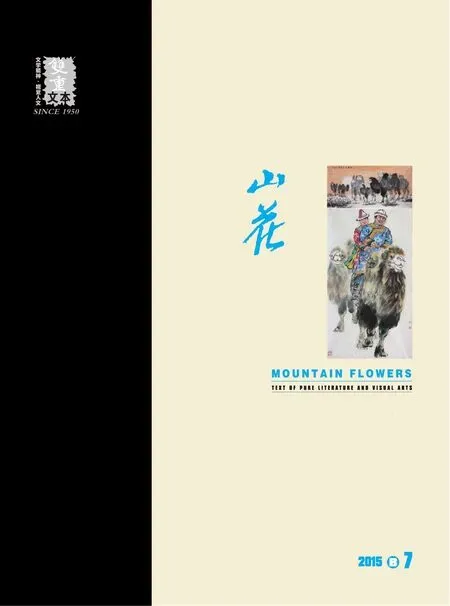君特·格拉斯《鐵皮鼓》的象征意象與女性書寫
侯景娟
《鐵皮鼓》(1959年)是德國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小說處女作。小說采用了獨特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和倒敘手法,以30歲的主人公奧斯卡在療養院的病床上伴隨著鼓聲追憶往事的形式展開,講述了外祖母和外祖父土豆地里相遇,母親與表兄亂倫,自己和繼母有染,一直到現在自己孤獨的養老院生活為止的家族故事。不難發現,奧斯卡對自己家族史的追溯并沒有像通常那樣從父系一族的歷史展開,而是開始于他摯愛的母親的家族,逐一向讀者展現了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生母阿格內斯-科爾雅切克和繼母瑪麗亞·特魯欽斯基這三位女性的生活狀態,通過她們集中再現了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中期旦澤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聯邦德國社會的生活。在藝術上,小說吸收了17世紀德國巴羅克文學的某些表現手法,意象豐富,充分展現了作家超凡的想象力。這些意象和作家象征手法的運用有很大關系,可以說,對象征手法的把握是解讀這部小說的一把重要鑰匙。
海茵茨·戈克爾指出:“這部小說(《鐵皮鼓》)就像一個由具有不同象征意義的個體組成的拼接照片。”的確,在這部小說中,象征手法被大量運用,奠定了小說深沉、含蓄的敘事格調,特別是在女性形象塑造上,象征伴隨著君特·格拉斯女性書寫的整個過程。在《箴言和沉思》一書中,歌德曾對“象征”一詞下過如下定義:“真正的象征就是用個別代表普遍。它不是作為夢境和幻影,而是作為對某種玄妙莫測的事物的生動、即時的領悟。”也就是說,象征用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具體可感的事物來替代抽象、模糊、無法言說的內容,從而使小說更加生動形象,富于表現力。在《鐵皮鼓》中,君特·格拉斯通過運用大量的顏色、數字、動物、植物等象征手段,展現了女性豐富的內心世界,成功塑造了在動蕩不安的歷史中不同時代、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
祖母的裙子:寬容與愛的代表
奧斯卡的回憶開始于外祖母安娜,然而小說僅僅用外祖母穿的裙子來勾勒她的形象,并沒有從年齡、外貌、喜好等細節方面對其進行詳細描述。裙子是德國女性典型的傳統服裝,外祖母的裙子之所以能給讀者留下強烈的印象,是因為她的裙子無論數量、顏色、尺碼,還是穿著方式、功能,都有其異乎尋常之處。可以說,“四條土豆色肥大的裙子”成了祖母代表性的符號,格拉斯通過這條裙子豐富的象征意義,塑造了一位與自然親近,像大地一樣寬容、善良的女性形象。
根據圣經的數字象征,第四個希伯來詞“Daleth”是“門”的意思。很久以來數字“四”就被看作是現世的、世界的、大地的,以及女性的數字。水火風土四要素、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就是這一觀點的生動體現。因此,這個數字往往被賦予收獲和生命之源的意象。外祖母的四條裙子讓讀者很容易聯想到為人類開啟生命和希望的自然界。外祖母的裙子是四條套穿的裙子,并且按照一定的順序,每天里外倒換一次循環著穿。裙子的更換順序正如春、夏、秋、冬四季的自然更替,是對自然的模仿。
此外,裙子的“土豆色”,與外祖母的生存環境完全吻合。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農夫和小市民,他們的食物大多依靠當地生產的食材,其中最重要、最廉價的食物就是土豆。外祖母從小就和哥哥文岑特一起在卡舒貝的土豆地里勞作,在土豆地里長大,在土豆地里遇到了外祖父。可以說,格拉斯描述的旦澤和卡舒貝人的日常生活和勞作都和土豆有關,土豆的顏色是他們所熟悉的顏色,也就是大地的顏色。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諾伊豪森認為:“穿著四條循環更替的土豆色裙子的外祖母就是地母蓋亞和收獲女神得墨忒耳的統一體。”
除了這種顏色以外,外祖母的裙子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尺寸寬大。裙子的特征賦予了外祖母這一女性一種強大的包容力。“它們(裙子)圓墩墩的,風來時,似波浪翻滾;風吹到時,倒向一邊;風過時,劈啪作響;風從背后吹來時,四條裙子一齊飄揚在我外祖母的前頭;她坐下來時,四條裙子便聚攏在她的周圍。”其中,“四條裙子聚攏在她的周圍”暗示了肥大的裙子的另一個作用,就是猶如母胎一樣的保護功能。
外祖父約瑟夫·科爾雅切克曾經躲在外祖母的裙下擺脫了追捕者這一情節使“裙子”具有了避難所的意義。奧斯卡在出生時就表達出“重返娘胎頭朝下的位置的愿望”,這種回歸渴望在現實中通過裙子得以具體實現。小說多次出現奧斯卡渴望待在外祖母裙子下面的描寫,可以說,裙子是拒絕成長的奧斯卡唯一的烏托邦。
外祖母的裙子底下是奧斯卡向往的天堂,“這里,慈愛的上帝坐在奧斯卡身邊,他總是喜歡溫暖;這里,魔鬼在擦他的望遠鏡,小天使在玩捉迷藏;在我外祖母的四條裙子底下,永遠是夏天,不論是圣誕樹點燃的時候,還是奧斯卡尋找復活節彩蛋或者禮拜萬圣的時候”。與丑陋的現實不同,裙子底下的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是上帝和凡人、魔鬼和天使都能和睦共處的世界。裙子代表了溫暖、包容、和平與友愛。在這個意義上,維拉赫認為,祖母的裙子與圣母的披風作用相同。可以說,身穿四條土豆色裙子坐在土豆地里的外祖母既是偉大母親,同時又是溫柔而強大的守衛者和保護者,體現了人類與自然、自我與他者的和睦共存。
從圣潔到墮落:三角關系中的生母
與生母阿格內斯·科爾雅切克密切相關的象征符號是“白色”、數字“三”和“鰻魚”。
白色是小說中出現較多的一種顏色,貫穿了整部小說。按照時間順序,小說中的白色第一次出現在母親在銀錘陸軍醫院擔任助理護士時穿的制服上,在軍醫院里,純潔少女阿格內斯結識后來成為丈夫的馬策拉特。阿格內斯以白色天使和作為身著白色婚服的新娘出現在那個時期的照片中。白色是圣母瑪利亞的顏色,那時的阿格內斯與白色本身所代表的圣潔一樣純潔無瑕。
后來的照片中,通過對母親、表舅和父親三人的幾張傳達出“劍拔弩張地和平”的合影的描述,在短短的幾段文字敘述中,反復詠嘆式的強調了“三”這個數字。與數字“四”相比,“三”在宗教意義上表示圣父、圣子、圣靈的三位一體,是與男性相關的數字。古代神話中,海神波塞冬手持標志性的三叉戟,“三”就成為波塞冬的象征。在這部小說中,格拉斯用“三”這個數字來暗指男女三角關系,即性的意義。奧斯卡的母親阿格內斯與表舅揚和名義上的父親布朗斯基之間存在著三角關系。不倫一直伴隨著阿格內斯和馬策拉特的婚姻,連幼小的奧斯卡也知道阿格內斯和揚差不多每星期四都在木匠胡同那家膳宿公寓里幽會。母親阿格內斯的生活處于與情人偷情、去教堂懺悔、再次偷情、再次懺悔的循環往復的矛盾之中。endprint
在小說中,三人游戲施卡特牌則是掩蓋這種三角矛盾的最好辦法。三人同時在場時最和諧的畫面就是玩施卡特牌。“施卡特牌戲——誰都知道,只能三個人玩——對于媽媽以及那兩個男人來說,不僅是最合適的游戲,而且也是他們的避難所,他們的避風港,每當生活想要引誘他們以這種或者那種搭配構成兩人生存,玩兩人玩的六十六點或下連珠棋這類愚蠢游戲時,他們就躲到那里去。”然而,這種牌桌掩蓋下的表面的和平終有一天會被摧毀。母親和表舅明知這種關系背離社會道德,但仍然沉溺于偷情的歡樂。而父親清楚知道這件事卻選擇了沉默,他所做的只是用湯和菜肴向母親表達他的愛。因此,三人對此都是有罪的,但受到懲罰的卻只有母親,這場婚姻危機最終以母親的死得到終結。
阿格內斯之死始于耶穌受難日的郊游,其中“鰻魚”是導致她死亡的直接原因。鰻魚的形狀可以使人聯想到陰莖。海茵茨·戈克爾指出,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中轉用了《圣經》中象征魔鬼的蛇所代表的邪惡意象,用鰻魚替換了蛇來指代罪惡和不道德行為,進而成為性的象征。…在小說中,鰻魚不僅象征性器官。《耶穌受難日的菜譜》這一章,碼頭工人抓鰻魚的情景以及母親對鰻魚的不斷需求就體現出鰻魚本身所代表的死亡意象。鉆在被砍下的黑色馬頭里的那兩條“胳膊一樣粗,胳膊一樣長的鰻魚”,暗示了在一旁觀看的阿格內斯的境況。也就是說,她的內心處于被丈夫和表兄的撕扯之中,這最終導致了她的死亡。鰻魚是母親欲望的象征,無度的吞食包括鰻魚在內的各種魚使母親中毒致死。
通過“白色”、“三”和“鰻魚”這三個象征,格拉斯形象地勾勒出從純潔少女淪為被欲望撕扯,最終成為不倫之愛犧牲品的母親阿格內斯的悲慘命運。
蘑菇:靈與肉的尋找和追問
在母親阿格內斯去世后,繼母瑪麗亞·特魯欽斯基成為對主人公奧斯卡最重要的女性。與繼母相關的情節里,多次出現了“蘑菇”這一象征符號。
從石器時代開始,蘑菇就是一種重要的食物。在卡舒貝和旦澤人的廚房中,蘑菇是除了土豆之外,另一個占據舉足輕重地位的食材,在小說中就出現了阿爾弗雷德·馬策拉特用卡舒貝的雞油菌和雞蛋、肉放在一起炒的情景。
蘑菇通常是好運的象征,賦予這種象征意義的首先是一種漂亮的帶白色圓點、紅色菇頂的毒蘑菇,有些地方用它制成迷幻藥。有些蘑菇外形近似男性生殖器,故人們把它們與性能力和繁殖聯系在一起。在此處,蘑菇沒有使用其傳統的代表男性的意義,而是象征了女性生殖器。安杰莉卡·希勒·山德沃斯指出,不只是男性生殖器用蘑菇形象表達,女性生殖器也在此找到了形象的對應:這出現在《鐵皮鼓》的氣味中,蘑菇與女性懷抱或陰道相聯系。
奧斯卡用汽水粉引誘瑪麗亞。在波羅的海海濱,兩個人同在一間“熱的、干的,顏色是自然的白里帶藍”的更衣室換衣服。當奧斯卡看到瑪麗亞毛茸茸的三角形時,他一躍而起,向瑪麗亞撲去,隨后他“聞到了蘑菇或其他辛辣的味道”。格拉斯將蘑菇與人類生殖器聯系起來,將同房比作尋找蘑菇。作家詳細描述了奧斯卡在瑪麗亞的“苔蘚地帶”尋找生長在那里的“蘑菇”的場景帶有強烈性的意象,而奧斯卡本人則自稱為“香菇、羊肚菌以及其他我叫不出名字但仍可享用的蘑菇的收集者”
用蘑菇指代繼母瑪麗亞,除了好運的象征,還表明了瑪麗亞本身的客體性。瑪麗亞最初是來奧斯卡家幫助經營商店的幫工,之后成為奧斯卡的情人,后來卻嫁給他的父親成為他的繼母。在所有這些變故中,瑪麗亞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她是“蘑菇采集者”奧斯卡和父親馬策拉特帶有侵略性意志的被征服者,是男權社會中男性權力支配的對象。
繼母這一形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瑪麗亞看望療養院的奧斯卡時穿著“一套時新的春裝,配上一項時新的鼠灰色帽子”,關心的是手提式收音機里報道的新聞。當奧斯卡試圖要喚起過去采蘑菇的美好回憶時,瑪麗亞表現出“惱火”和“驚愕”,這體現了戰后她擺脫了男性權力的枷鎖,試圖忘記過去,在新的時代重塑自我的強烈渴望。可以說,這一場景本身就暗示了戰后女性主體的重塑問題。
結語
在《鐵皮鼓》中,君特·格拉斯通過巧妙運用多個象征意象,生動描述了旦澤一個小市民家庭中的外祖母、生母、繼母三代女性的命運,揭示了女性在不同社會歷史時期的地位和生存狀況,進一步折射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段時期旦澤社會的歷史全貌。女性從戰前寬容與愛的代表,到戰爭中的犧牲品和男權社會的被動接受者,再到戰后的自我意識覺醒、試圖重新獲得身份認同的新生者,這一歷程也恰恰是旦澤這座城市在這一歷史時期的命運和發展軌跡的真實寫照。在這個意義上,女性生存狀態描繪具有了廣闊的社會文化內涵和深刻的政治寓意,也是這部作品具有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的重要原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