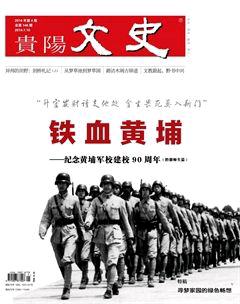我的苗鄉情結
在21年與苗族同胞的親密接觸中,我一次次經歷了苗族人民太多的感人事實,用“刻骨銘心,終身難忘”來形容一點都不夸大。
1958年我在干部下放勞動鍛煉中,因不識時務對“大躍進”說了真話,加之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微妙關系處理不好,我竟然“因言獲罪”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從此,在稱之為“苗疆腹地”的臺江縣待了21年,把整個青春年華都留在了那里。
臺江屬于黔東南州一個很小的縣,當時全縣人口大約10萬,苗族卻占了總人口的97%,是一個苗族歷史文化底蘊深厚,但卻因為交通極為不便制約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地方。當時凱里到臺江的公路尚未修通,從貴陽去臺江,必須從鎮遠繞行,經兩天路程方能到達。
當時縣城的主干道是一條寬約5米的街道,從東門到西門全長也不過1公里,街道兩側的民房幾乎是清一色的木結構板房,低矮陳舊,僅百貨公司是唯一的一棟磚木結構兩層樓房。在這條街上,集中了縣城所有的商鋪、餐飲等等服務行業,到了趕場天,更是人山人海,擁擠不堪。
縣委會、縣政府這兩個主要領導機關也在這條街上,坐落在東西兩端,相距300米左右,都座北朝南,背靠老百姓稱之為“大炮臺”的一座山。進入縣委會,大門左側是縣委大禮堂,臺江是盛產木材之鄉,這大禮堂也毫不例外是木結構的,可以容納400人左右,是全縣干部集中開會、學習的地方。縣委各辦公室則在一棟磚混結構的兩層小樓里。
縣政府和公安局、檢查院、民政局、教育局等則在舊政權留下來的衙門里辦公,辦公樓是一樓一底兩層木結構,走到樓上就會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
街道的西端新修了一幢面積約100平米的文化館,是一座兩層的磚木結構樓房,所謂文化館,只不過提供了樓下一間房子做個報刊閱覽室而已。在文化館后面,卻有一個面積相當于足球場大小的廣場,老百姓都叫它“大操場”,這里倒成了人們進行文體活動的中心,從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延續到改革開放前,一年四季這里都是人們早晚鍛煉身體、進行球類比賽和文娛活動的場所。
縣城北邊叫“大炮臺”的山上,依稀可見清代遺留的古城墻。每年端午節,臺江老百姓有“登高”的風俗,這時,大人小孩都會不約而同地奔向“大炮臺”奮力登頂。登山者眾,宛如一條游動的長龍,景象十分壯觀。縣城南邊,有一條源于雷公山麓的翁里河,它清沏秀麗,平緩地流過城南側,經梅影、桃賴、南省、南冬等十數個苗寨,灌溉數千畝良田后,默默地在南乜寨與巴拉河匯合進入清水江。
我留在臺江以后,1958年底參與了縣里的 “縣城發展規劃”,首先是要獲得一張平面圖,我記得參與測量的還有楊鳳池、段松柏。那段時間,我們每天早餐后就各自背上水壺,扛著標桿,帶著測量儀、三角架等測繪儀器,沿著今天從臺拱寨到梅影寨的這條大道(當時還是一片田壩)進行測繪。那時說搞規劃,真是有點前無古人,我們全憑“三個臭皮匠”的思路和“腹稿”進行,也就是小平同志說的“摸著石頭過河”吧。首先,我們按照自己的思路確定一條中心線,然后將標桿的坐標向南北兩邊的山頭延伸……楊鳳池和段松柏是建筑和科技部門的干部,對測量是內行,他倆選好中心線,把測量儀架好、觀測、記錄、作圖,我就根據他們的指揮,扛著標桿跑南北兩邊山頭。我當時24歲,年輕力壯,跑路登山自認為是我應該做的事,在扛著標桿跨越河道和溝溝坎坎時,摔跤再所難免,毫不覺得艱苦。10多天后終于繪制出一張一張平面圖,交由縣的主要領導會同有關部門充分發揮想象力“指點江山”,定下哪里是文化教育區,哪里是商業區,哪里是工業區,哪里要建什么學校,哪里要建敬老院,哪里要建醫院,道路要多少寬……等等。為了更形象地展現這個規劃,還責成文化館的賈人智充分發揮想象力,用對開紙將道路及各種設施制成比較直觀的效果圖,但是,這次規劃卻因為當年全省統一的并縣行動(臺江與劍河合并)而“泡湯”。但從今天臺江縣城的實際格局看來,頗與當年那個“理想”的規劃十分吻合。
我“因言獲罪”滯留臺江21年,也讓我一生的生活、工作、思想發生了深刻變化,這就是有了終生難以割舍的“苗鄉情結”。在那個做“馴服工具”、當“鑼絲釘”的年代,人的一切行動都是有限度的,只有思想——如果不用語言或文字表達出來,還可以“偷偷地自由”。在整整21年的現實生活中,我通過對社會和不同人的觀察發現,苗族是我國56個民族中的優秀民族之一,他們天性勤勞,純樸善良,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善于奮力拼搏,生存能力極強。比如,每年的春耕大忙季節,男男女女都會早出晚歸頂風冒雨犁田、翻山越嶺割秧草、爬坡上坎運肥料,到插秧結束時,男女都會消瘦,體重減輕很多;又比如我們電影隊下鄉放電影,三四百斤重的發電機,兩個小伙子可以抬著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健步如飛,實在令人佩服。
從歷史上看,苗族歷經數千年的發展、戰亂,保持了自己的語言、服飾、風俗習慣,遷徙到湘西和貴州各地定居、繁衍下來是相當不易的,不愧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優秀成員之一。在21年與苗族同胞的親密接觸中,我一次次經歷了苗族人民太多的感人事實,用“刻骨銘心,終生難忘”來形容一點都不夸大。
1958年,當我被劃為“右派”時,報效巖寨的老鄉為我鳴不平,下放領導小組把我調離巖寨,借此把我與當地老鄉隔開。“文革”時我又因“翻案”(因我從被劃為右派之日起一直堅持申訴)被揪斗、游街,巖寨的老鄉竟然集體給縣革委寫信,幾十個人蓋手印證明我無罪。在“一打三反”中,我更被開除公職,下放到南冬寨監督勞動,可是南冬的群眾、隊干、共產黨員不但不歧視我,反而在生活、勞動中給予我許多關照和安慰,而且下去的第三天就讓我當計分員。隊長李春林,會計李文澤還經常到我的住處聊天安慰我。考慮到我是從城里下去的,他們把最輕的活分配給我干,當我生病時,隊長、會計會按苗族治病的方法給我“刮痧”、“拔火灌”,老媽媽們則會給我熬稀飯……面對這些無微不至的關懷,深刻體驗著苗族同胞發自靈魂深處純樸善良的人性,讓我這個罹難的人刻骨鉻心,終生難忘。每當我重返臺江,一進縣境,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人們的一舉一動,我都會感到親切。當然,那里也留下了我人生的苦難,有人問我:你在臺江倒霉這么多年,怎么還會對那里這么情深、念念不忘?他們哪里知道,在那以階級斗爭為綱、災難深重的日子里,沒有苗族兄弟姊妹、父老鄉親對我施予援手,給予我無盡的恩惠,我簡直懷疑是否有勇氣活到今天。
這些點點滴滴是我幾十年的人生感悟。退休22年了,多次回去探望父老鄉親和共過事的老朋友,共度苗族“姊妹節”、“龍舟節”。每次回去都會聽說有好友告別了人世,有的還會在病中通過電話與我“訣別”。去年6月我回到巖寨看望了老友張富學(一位抗美援朝退伍軍人),今年4月他竟然在電話中對我說:“朱宇同志,再見了!”3天后他的孩子在電話中告訴我:老人走了。人生苦短啊!嗚呼!苗鄉又一位善良的人離我而去了。
我現在已經是82歲的老人了,照目前的身體情況,興許還能再活一些年頭,還有機會看到社會的許多進步和變化。臺江當然也在變,它與半個世紀前大不一樣。如今,一條寬10多米的水泥路已經從東端的臺拱寨一直延伸到了梅影寨,從舊大橋到鴨場壩也都鋪設了寬闊的大馬路。臺拱寨前的秀眉廣場矗立著苗族英雄張秀眉的塑像,成了群眾文化娛樂活動的中心;翁里河上跨越著兩座具有民族風格的風雨橋,沿河兩岸新建住宅小區、商店、酒樓、旅社林立;河的兩岸花壇錦簇,樹影婆娑;“姊妹街”集中展示著各種苗族手工藝品。
縣委、縣政府等幾大班子和辦事機構,也都從小街那陳舊、狹小的環境搬進秀眉廣場西北邊的辦公大樓。張家寨、梅影寨和原來的大操場都修建了一大批住宅小區,行政上也升格為臺拱鎮了。320國道和玉(屏)凱(里)高速公路的相繼修通,更讓臺江的發展如虎添翼。
(作者系團省委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