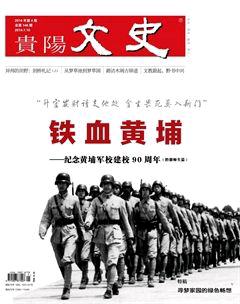多雪的冬天
王六二
戰(zhàn)爭的傷害,不只殺戮,還有那些無法彌補(bǔ)的、極度的、欲哭無淚的悲痛,漸漸化為沉默,蔓延到生活的每一個(gè)角落。
2013年底,嚴(yán)寒襲擊美加?xùn)|部。
芝加哥遭遇50年一遇的寒冬,凝凍導(dǎo)致多倫多大面積停電。我們住的美加邊境城市溫莎,幾場大雪,下得隆隆重重,鋪天蓋地,春節(jié)過了都還未停歇。
窗外,白茫茫一片真干凈。
出不了門,呆在家里,只有微信時(shí)不時(shí)地叫兩聲,提醒著我的注意。雖然那都是千里萬里以外的事,卻時(shí)常令人揪心、寒心。
調(diào)頻FM90.9正播放著約翰·斯特勞斯的圓舞曲。大雪天里,河對面的市政府都破產(chǎn)了,底特律音樂臺還在放送這種輕松歡快的音樂,一點(diǎn)同心同德的意識都沒有。
新年的報(bào)紙,一大堆,都懶得去翻了。網(wǎng)也不想上,一些吸引眼球的文章,看到關(guān)鍵處,總會跳出一小方塊提示,叫你訂閱后再往下看。這年頭,好東西本來就不多,好看又有意思的更少,花點(diǎn)錢看文章說來是應(yīng)該的。可是,閱讀不花錢,是我們這一代人從小養(yǎng)成的壞毛病。
無所事事,時(shí)間就溢得滿地都是。百無聊賴,找不到一件有意思的東西。還是撿起書來吧,蜷縮在沙發(fā)里,舒舒服服,順便把這滿地的時(shí)間掃進(jìn)一百年前。
朱麗葉·尼科爾森(Juliet Nicolson)的《大沉默——生活在大戰(zhàn)陰影中的1918年至1920年》(The Great Silence—1918-1920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War),是從溫莎公共圖書館借來的。我自以為對二戰(zhàn)比較熟悉,一戰(zhàn)比較陌生。覺得一戰(zhàn)是祖輩的事,很古老了。如果以戰(zhàn)爭來劃分人的記憶的話,我的父輩應(yīng)該算是二戰(zhàn),我們這一輩,應(yīng)該是越戰(zhàn)和海灣戰(zhàn)爭。
戰(zhàn)爭是殘酷的。可是,描寫戰(zhàn)爭殘酷的作品卻并不多見。我從小接觸到的,大多是以正義之名歌頌戰(zhàn)爭,把戰(zhàn)爭英雄化浪漫化史詩化,讓人產(chǎn)生一種崇高感,一種慷慨激昂,并愿意為之獻(xiàn)出生命。而對于殘酷的事實(shí)本身,卻鮮有貼近真實(shí)的描寫。
戰(zhàn)爭,除了殺戮,還有另一種殘酷,那便是漫長的悲痛,傷心,有的甚至是終生的。
這本書描寫的,正是一戰(zhàn)后英國人的這種悲痛。
戰(zhàn)后兩年間,無法彌補(bǔ)的、極度的、欲哭無淚的悲痛,漸漸化為沉默,“蔓延到生活的每一個(gè)角落”。
埃特爾太太在戰(zhàn)爭中失去了兩個(gè)兒子。大兒子朱利安負(fù)傷后被運(yùn)送回國,她在醫(yī)院里守護(hù)了兩周,眼睜睜地看著他在懷里死去。小兒子威利在一次戰(zhàn)役中,跟幾百人一起沖鋒,再也沒能回來。英國在1915年就有法令,陣亡將士的遺體一概不準(zhǔn)運(yùn)送回國。埃特爾太太很清楚,這么多的年輕人被機(jī)槍掃射,手榴彈炸開,倒在泥淖里,他們的遺體根本無法辨認(rèn),威利也許就跟那幾百同伴一起埋在了他們倒下的地方。夜深人靜,在埃特爾太太的心里,小兒子的突然失去,比大兒子的慢慢永別更加難以接受。
但是,特埃爾太太的悲痛只能是默默的。她不愿敘說,也無法敘說,她害怕把自己的悲痛傳染給本身也承受著同樣悲傷的人。戰(zhàn)后的英國,250萬的傷亡,使同情變成了一種很理性的感情,只為最親密的人保留著。個(gè)體的死亡在大量的死亡中被淹沒了。在許多場合,悲痛得不到傾泄。面對悲痛,英國人的習(xí)慣是抑制,而不是討論。好像保持沉默,痛苦就會消失。
這本書的扉頁,用了一幅著名的照片,標(biāo)題就叫《悲痛》,攝于1919年11月,簽署停戰(zhàn)協(xié)定整整一年后。身著一襲黑衣的英國女子,掩抑在深深的哀傷之中,看不見的她的表情,卻讓你感受到她的悲痛有多深。
在索姆河戰(zhàn)役的第一天,英國人的傷亡就達(dá)到57470人,其中有三分之一因傷而亡。然而,戰(zhàn)前年輕人對死亡是什么回事卻模糊不清,沒有人知道戰(zhàn)爭是什么樣。根據(jù)歷史學(xué)家A.J.P.泰勒的說法,年輕人把戰(zhàn)爭想像成一次偉大的進(jìn)軍,一場很快就會結(jié)束的偉大戰(zhàn)役。
戰(zhàn)爭開始之初,上流社會的許多子弟,像伊頓公學(xué)的格林菲爾一樣充滿幻想。這個(gè)熱情開朗的年輕人寫信給他的母親說,“這是所能夢想到的最好玩的事了,……戰(zhàn)爭的不確定太好了,就像你不知道什么時(shí)候,要到什么地方去享受一次野餐。”上流社會雜志《饒舌》描述戰(zhàn)爭時(shí),將它比喻為一次“偉大的歷險(xiǎn)”。但7個(gè)月后,當(dāng)愉快的野餐結(jié)束時(shí),伊頓公學(xué)報(bào)名參戰(zhàn)的5687名學(xué)生,有1160人永遠(yuǎn)回不來了,包括格林菲爾,還有1467人負(fù)了傷。
這本書不單純是紀(jì)實(shí)文學(xué),還有豐富的社會心理學(xué)。作者想發(fā)現(xiàn)戰(zhàn)前與戰(zhàn)后,經(jīng)過戰(zhàn)爭和250萬人的死傷之后,社會心理的裂痕體現(xiàn)在哪里,究竟有多大?戰(zhàn)后社會是如何改變的,人們?nèi)绾芜m應(yīng)?或者根本無法適應(yīng)。以及“深深的悲痛和社會壓抑如何轉(zhuǎn)換成渴望愉悅和享樂”。
當(dāng)悲痛的情緒還在蔓延時(shí),人們面對的是四百萬復(fù)員軍人,三百萬從事軍需生產(chǎn)的工人,他們都需要重新尋找工作。戰(zhàn)后的社會,就像急剎車以后,突然轉(zhuǎn)朝另一個(gè)方向疾馳。文化上,古典的含蘊(yùn)優(yōu)雅,被刺激性的娛樂消遣所取代。美國文化撞入了英國疲倦沉悶的心靈,為國家?guī)砹祟澏兜男奶k娪霸罕榧俺擎?zhèn),歌舞廳夜總會到處興起,爵士樂來了,卓別林也來了。
電影、音樂、夜總會就像催眠一樣,幫助人們克服沉默中的痛苦,克服孤獨(dú)與恐懼,用刺激和愉悅的方式讓人們沉睡,讓人們遺忘,因?yàn)椤靶褋恚褪且洃洝!?/p>
這本書充滿細(xì)節(jié),文筆生動(dòng)。作者還不忘提到,愛丁頓爵士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推廣者。1919 年,他通過觀測日全食時(shí)太陽附近星體的位置,證實(shí)了相對論。故事發(fā)生在德英兩國互為敵視的歷史背景中。
作者朱麗葉訪問了許多90歲、100歲的老人,包括一些公爵、爵士,他們向她講述了那個(gè)年代許多有趣的故事。一些人還讓她走進(jìn)家庭圖書館,讓她翻閱珍藏的家書。她在致謝中還特別提到,伊利莎白二世女王向她開放皇家檔案館,并允許她引述瑪麗王后的日記。
(作者單位:中國科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