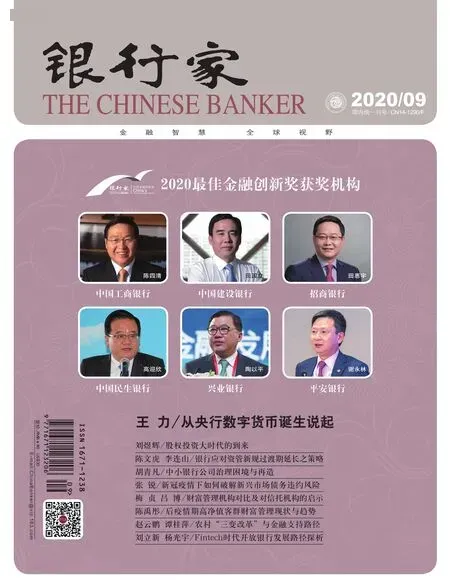中國傳統 老而不死
高續增
怎樣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一個全面的評價呢?我以為,中國傳統的價值評判不但要看它曾經起過的正面的和負面的作用,還要看它在當下和將來能為民族文化的進步產生什么樣的作用。是的,自秦漢以后形成的中國文化傳統阻尼了中華文化進一步的開放和升華,變成為專制統治者的鞏固既得利益的得力工具,其“害”的一面顯而易見。但是即使是有百害,也不能否定它有一些有益于中國人的另一面,它畢竟是在反復博弈中反復激烈碰撞中取得的結果。我們也應當看到,那一套治理社會的文化系統用了很不人道的非常規的手法把一個本來松散的部落文明集合(西周社會)改造成為一個碩大的有著廣泛民族認同的巨型國家,并讓這個國家在應對來自外部的危機時,可以依仗巨大的人口優勢在大部分情況下化解掉有時看來是岌岌可危的險境,其有效性應當被我們后世的中國人認可。
秦漢以后的中國文化延續到今天這個不好不壞的結局是可以從各個角度進行分析評判的,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讓中國人受到了屈辱;但是它畢竟還是活過來了,總比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為好。換一個角度試想一下,如果中國兩千多年來一直像春秋初期那樣幾百個諸侯國林立,中國的歷史航船就能駛向自由市場經濟的方向么?中國顯然不具備必要的條件來實現那樣復雜且痛苦的轉化,這是由于現代自由市場的理念和社會管理架構都無法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自覺產生,依據中國古人的智慧,只能產生諸侯會盟那樣高度的“天下理論”,而時間恰恰又證明了絕大多數中國古人(農人社會中的小生產者)是厭煩那種處于動態的不穩定的社會局面的,——好了,如此看來,中國歷史后來的真實發展就是一種必然了。
再往深入一層想一想,在“等”來了別人創造出了“柏拉圖主義”思潮、并面臨它的大規模進逼到國門以后,也就是在面臨接受或者抵制世界現代市場經濟理念的時候,中國是分散的好呢,還是保持成一個整體的好呢?我以為,顯然是后者要好些,我們中國保持著一個整體顯然能夠讓我們的社會的進化過程平穩一些。說到這個層面就會陷入一個為史家長久爭論不息的論題——歷史宿命論應當被肯定還是應當被徹底否定呢?我們為了避免繁瑣的論爭,此時不得不繞過這個可以被判定為無解的漩渦,就是直接認定:中國真實的歷史有其必然性,我們只能承認它,并從這個起點來出發繼續進行接下來的討論。
不管是埋怨中國傳統文化阻尼了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也好,還是慶幸它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不間斷地延續了大中華這個文明體也好,既然我們的注意點是“今后我們應當怎么辦”這一論題上,那么,還是留出更多的空間討論一下今后我們怎么對待它。
首先我要點明的一個觀點是:中國傳統文化確實為我們擁抱現代文明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條件。
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巨大的經濟成就,絕不是任何一個民族只要無條件地打開國門引進來自西方的現代文化思潮和科技成果就能取得的,這樣重大的一個事件絕不會來的那么簡單。雖然在我們民族的骨子里找不到現代市場經濟的精髓——平等、民主、人人意志的自由表達,以及由信仰精神培育出來的契約意識,但是現代社會文明這個系統并不只有這些精髓而沒有其他必要的輔助的文化儲備,例如團隊意識的培育,商品交換習俗的養成,以及對勞動價值的認可,
從西方傳來的現代社會文明理念的核心,它的物質基礎——市場經濟需要許多預先設置的文化成果的儲備,中國的文化傳統則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執法地養成了其中的必要部分。我這樣說絕不意味著我主張這樣一個觀點:中國文化傳統本身就孕育著現代世界文明的基本DNA,而是想說:中國文化傳統在長期頑強地生存期間,在中國人長期的社會生活中也養成了一些與現代社會文化并行不悖的理念,這些理念是組織一個現代社會所必備的素材。古代中國人崇尚讀書、樂于學習的精神,中國人認定“勞動”具有普遍社會價值并應當被社會認可的理念,認定社會產品的相互交換活動應當被承認為一種勞動形式的理念,盡管這最后一種的價值與“儒文化”有沖突(即:“抑商”和貶低商人商業的偏見)——這些理念長久期間存在于社會中,已經不自覺地為將來一旦有條件時融入西方商業社會提供了便利。
很值得強調的一個方面是中國古代教育體系的作用。盡管主持中國社會的統治者限定有志于成就大事業的學子們學習的內容是僵化的教條(目的當然是首先為了鞏固他們的獨裁統治),但是作為副作用而存在的結果卻是讓草民中的有條件的人們埋頭于書堆——此時的“副作用”是對前人的知識的繼承,這當然有利于社會向著理性的方向發展,——不斷強化國人的讀書意識,對后來的文化轉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試想,一個鄙夷書本知識的民族要比一個死肯書本迷信圣賢教條的民族更沒有前途。
特別應當提起的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東亞各國在20世紀創造出來的幾個經濟騰飛的奇跡,都與長期受到中國上述的文化傳統和精神理念的熏染有關。
比較一下世界上其他地域的民族在面對來自西方的現代文化沖擊時的表現,就能顯現出中國傳統文化比他們藏有更多的現代社會文化理念的元素。
首先與基督教文化長期打交道的穆斯林文明體,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長達兩千年,但是直到現在(從整體上看)也不愿意接受現代社會的基本理念,文化沖突一直持續不斷,還時不時地伴以武裝沖突。
第二,印度次大陸的文明體的歷史與中國可以比肩,也是一個很優秀的古老文明體,但是即使受到西方人(英國人)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但是在“理解”和運用現代社會文化成果的許多方面還是趕不上東亞圈的“儒文化”的各國。
第三,二百多年來拉丁美洲的發展一直讓制度經濟學家們困惑不已,原因是拉丁美洲各國有與基督教新教相似的文化氛圍(天主教文明圈),但是,北美經濟的順利發展與南美經濟的長期躊躇不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此外至于黑非洲、南洋群島這些“文化荒蕪之地”,更是像扶不起來的天子,更不爭氣了,經濟上始終落在世界的末端。因此說,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中孕育著與現代社會文化理念相互融通的某些共性,是使得東亞和中國能在較短的時期內成為與西方社會并駕齊驅的“強者”,而看到這一點后,我不能不在心里認可這一點:中國傳統文化雖然長期禁錮了中國人的發展,讓中國人從古到今吃盡了苦頭,但是我們只從我們已經實現的經濟騰飛這一點就應當悟出傳統文化給我們的不僅僅是糟粕,其中必有有益的元素。因此我們應當要對這份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進行兩分:批判——要徹底,要溯根,不然那些“惡俗”還會在我們的文明體內發酵;繼承——要珍惜,要身體力行,發掘其潛在的優勢。endprint
再比如崇尚節儉和勤勞務實的精神,這兩個習俗也是中國人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人的現代文化體系中的重要部分——經濟實體,其名稱的原義ECONOMY就是中文“節儉”的意思。中國人的朝廷和作坊(有的雖然很大也只能被稱為作坊)都有負責管理核算工作的“賬房”,這個部門只要把管理方式一變換,就能轉化為現代企業的經濟管理部門和財務核算部門。
這些是有利于現代市場經濟從外太空“濺落”中國這塊“熟土”并很快(以中國人所能接受的方式)扎下根來的好條件。當然,還有一些與現代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因素存在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這些內容都被黎鳴先生在書里狠狠地予以批判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平等觀念的嚴重匱乏,表現為君主專制制度對國人創造性思維和思辨能力的長期摧殘。
除了對黎鳴先生批評中國文化傳統的觀點有上述的不同意見以外,我從該書的其他部分已經找不到可以與黎鳴先生進行“商榷”的地方了,尤其是在中國有無真正的哲學這個問題上,黎鳴先生精辟的論述更讓我把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從根本上重新梳理了一遍。
說“中國無哲學”,首先是需要有膽量的,此外除了膽量還要有學識,黎鳴先生敢于把這個觀點說得那么徹底那么干脆,是由于他對(西方)哲學有著深刻的了解并將它與所謂的“中國”哲學進行過反復比較。我雖然有此心(主張中國哲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但是,沒有開口的膽子,原因是從來沒有能力從根本上對此二者進行過比較。這回我起碼知道了這類學術性很強的話語應當從何處開始說起。
黎鳴先生說哲學的語發點是“真”、“善”、“美”,這就把問題說到根子上了。
哲學的第一要素就是“真”。中國哲學說了“真”了么?——沒有。什么是真?黎鳴先生說“真”就是說清楚“大自然是怎么回事”,中國哲學說過沒有?——沒有。這一層叫黎鳴先生說得更“哲學”:它叫“必然王國”,客觀先驗的必然王國,它的存在與人的誕生無關,也就是說,它雖然是產生人類的基礎,卻根本不屑于有沒有人類意識到它。中國哲學只有老子在《道德經》里有過這樣精辟的議論,秦漢以后的中國人說話的發語詞就變成了虛偽的“奉天承運”如何如何,被這樣的緊箍咒控制住的人,他的兩眼還看得見“天”么?
哲學的第二要素是“理性王國”,用黎鳴先生的話說就是“相對經驗的實然王國”,又稱為“善王國”。
這是建立在第一要素基礎上的“王國”,沒有了前者,直接建立起來的一切“善王國”都是空中樓閣。中國哲學的缺陷處就在這里露餡了,中國哲學中的“善”是從家族倫理開始的,那就是“孝道”,人與人的關系,即使是天倫關系(還不要說假道天倫關系而僭位的君臣關系了),也是在大自然存在了若干億年以后才發生的事情,怎么能夠成為人類對客觀世界認知的基礎呢?如果一個哲學體系從這里做源頭開講,那不是一套淺薄的見識就肯定是一套別有用心的說詞了。
哲學的第三要素是“自由王國”,用黎鳴先生的話來說,就是“自由超驗的應然王國”,這是立基于“理性王國”的一個理想王國,那時一個“美”的王國,在現今人類的認知世界里,還難以描繪出那個“理想王國”的輪廓。
按照黎鳴先生的理解,因為西方哲學(1)對“真王國”做出了迄今為止人類最好的描述,全面揭示了“真王國”的規律,這就是自然科學的偉大成就;(2)對“善王國”同樣也做出了迄今為止最好的描述,比較全面地揭示了“善王國”的倫理;(3)它對“美王國”也有所涉及,雖然不及前兩個王國那么出色,所以西方哲學是個完整的哲學系統。
而中國人所謂的“國學”與上面所描述的哲學體系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所以被套上“中國哲學”標簽的那套理論,充其量不過是一堆中國古代文人思想資料的籮筐而已。
讀到黎鳴先生的上述議論,我真切地又一次感到一種被啟蒙的感覺,我先前自以為很成熟的想法原來還很凌亂,現在的想法則被梳理的頭頭是道了。
我的這篇文章和黎鳴先生的那本書說的主題是傳統,但是為什么要轉到哲學這個題目上來呢?在黎鳴先生的書中沒有解釋,我把我的理解闡述一下。
評判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否完美或者是不是在趨向完美,不能只看它的歷史是否悠久,也不能看它容納了多少零散的文化成果(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這個民族的人數多少、文化圈的空間有多大也不是那個文明體優劣的終極指標。要想用一個指標來判斷一個文明體的優劣,那就是看那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其哲學含金量的多少和深度。
黎鳴先生給予中國傳統那樣的評價,也可以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學含金量十分淡薄來解釋。
在現實生活中,中國人的智慧無可挑剔,經濟上算計得清清楚楚,可謂錙銖必較,但是中國人的理性思維就無法贊美了,表現為邏輯不通,推理不嚴,不識真理,只認權威。黎鳴先生在這本書中說的最憤激的話是:“中華民族的智慧被狗吃了。”它十分推崇老子的智慧,尤其是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表現出的哲學元素,墨子的學說也被黎鳴先生反復贊揚過,只是秦漢以后的歷朝歷代奉行的獨尊儒術的國策讓那些閃耀著燦爛光芒的智慧被無情地泯滅了。
民族文化中的哲學含量之所以能夠作為一個民族文化優劣的標志,是由哲學自身的文化性質決定的。從根本上看,是哲學理念統御著一個民族的世界觀,尤其是它統御著這個民族的精神領袖的思維方式,這樣,那個民族的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環節(家庭文化體系、社區文化體系、教育體系、經濟體系、法律體系、民族防衛體系、……直到喪葬文化體系)能否被同一個至高的哲學理念所統御,決定著它們能否配合到一起融洽地組成一支宏大的“交響樂隊”,每一個分群體能不能都在其中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聲部”,只有這樣,那個社會才是一個和諧的社會。以前中國人愛說“中體西用”,現在看來那顯然是一種空想,誰的器官都只能長在自己的身上。現在的中國,彌漫全社會的精神迷茫證明:李鴻章時代的中國夢是根本無法實現的,我們憂心于中國前途的人必須從根基上建立起一套與現代的“柏拉圖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中國新文化體系和新思想體系,舍此,中國只能靠著強力的行政管制方法以專政的手段來維持社會穩定,而這樣一直做下去終究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長遠治國方略。我想,這大概就是黎鳴先生在《老不死的傳統》一書中激憤地否定中國傳統的本意吧。(續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