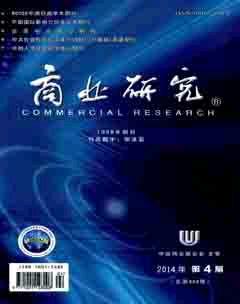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機理與實證檢驗
詹浩勇+馮金麗
文章編號:1001-148X(2014)04-0049-08
摘要:理論分析表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通過降低貿易成本和提升創新收益的中介效應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實證研究發現該外溢效應依賴于城市經濟基礎和區位環境的支撐,同時還要克服阻礙這種外溢跨區域傳遞的制約條件。區域性中心城市和先發工業化城市已表現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積極影響,但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尚缺乏對制造業的創新驅動作用。
關鍵詞: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制造業轉型升級;作用機理;中介效應
中圖分類號:F719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9-28
作者簡介:詹浩勇(1974-),男,廣西南寧人,廣西科技大學財經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工業化與產業集聚;馮金麗(1978-),女,湖北鄂州人,廣西科技大學財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數量經濟。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西部地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影響及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3CJY062。我國制造業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須盡快實現產業微觀要素配置結構和資源利用方式從低級到高級的演變,提升產業競爭力。問題的真正解決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因為生產性服務業對于增加制造業生產的迂回度和知識含量,提升制造業的要素和資源使用效率,進而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過,上述認識只涉及“應該發展”和“發展什么”,而未涉及“如何發展”特別是“何地發展”。隨著地理因素被納入主流經濟學考察的視野,產業發展的空間集聚狀態愈加得到重視。因為,產業集聚及由此形成的集聚經濟圈正成為國家和區域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工具。近年來,國內外生產性服務業出現了向集聚經濟圈中心城市、城市中央商務區和制造業園區集中的趨勢,成為區域和城市現代經濟空間演化的顯著規律。那么,這一集聚對生產性服務業的主要服務對象——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能否及如何產生積極的作用?研究這一問題,對真正把握以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路徑具有較強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現象的傳統研究主要包括:一是探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及其模式的形成機理,指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主要源于規模報酬遞增和外部性[1-3];二是探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區域空間或城市功能變遷的關系,提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將調整優化城市和區域經濟空間結構,高端服務業向中心城市或城市主城區集聚,傳統制造業向中心城市外圍或經濟圈中小城市遷移 [4-6];三是通過測算國家和地區生產性服務業及其細分行業集聚度,研究集聚的特征、趨勢和影響因素[7-8]。這些研究很少從產業間分工聯系視角,討論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其他產業的外部經濟影響。而近年來,部分國內外學者開始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作為一項重要因素,納入影響工業尤其是制造業演變升級的結構框架加以研究:一是研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作用。施衛東(2010)發現金融業集聚促使上海市二、三產業比重提高,第一產業比重下降。二是探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增長的影響。藤田昌久、蒂斯(2004)構建了一個兩區域、三部門的內生增長模型,指出創新部門在某區域集聚可通過增加現代制造業部門的產品種類推動區域全局經濟增長[9]。蘇紅鍵、趙堅(2011)分析了長三角制造業結構趨同合意的原因,指出生產性服務業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了區域產業資源的配置效率,從而有利于區域制造業增長[10]。三是分析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工業效率的溢出效應。顧乃華的研究發現服務業距工業的距離越長,外溢效應越小[11],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工業全要素生產率有促進作用,中心城市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工業的輻射帶動作用因受到地理限制而不能充分發揮[12]。總第444期詹浩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機理與實證檢驗????商 業 研 究2014/04上述研究已初步形成了一個新的詮釋二、三產業動態演變(空間集聚、轉型升級)之間關系的方向。其中,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積極作用已得到關注和重視。但這一作用機理還有待進一步梳理和總結,尤其需厘清這種外溢效應的傳導機制和其鏈條中關鍵的中介變量,同時還需要通過實證分析來檢驗。
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機理生產性服務業是從制造業內部分離出來成為獨立業態的,進而通過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重新嵌入制造業價值鏈。不同類型服務業所集聚的地域特征各不相同,這將導致對制造業外溢作用的機理不同。以下將生產性服務業劃分為功能型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分別討論其集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機理。(一)功能型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機理波特(2002)歸納了與企業相關的競爭活動,并稱這些活動為價值鏈。其中的一種價值鏈活動為基本活動(包括生產制造、營銷、運輸和售后服務等)[13]。隨著分工深化和競爭加劇,制造業企業將基本活動中具有服務性質的部分外包出去,產生了一批獨立的生產性服務業態,如運輸、倉儲物流、維修維護服務、商貿會展、批發零售業等。筆者將上述服務業稱為功能型服務業。這類服務企業不僅通過大批量生產和增加服務產品取得內部規模經濟,降低了作為制造業中間投入品的服務成本和價格;還體現出主要集聚在區域性制造業園區或產業集群周圍的空間特征,并從地域集中化經濟中追求集聚所產生的整體規模效應和整體產業鏈形成。相比于傳統的縱向一體化產業組織,產業發展的空間集聚新范式更有利于充分發揮功能型服務業企業間的競爭及協同合作所帶來的積極外溢效應,以降低貿易成本為紐帶,為制造業轉型升級打下良好基礎。1.競爭帶來的外溢效應功能型服務業企業在一個區域集聚,不論是同一個細分行業(如物流業、維修服務業)企業集聚,還是關聯細分行業(如專業市場和品牌銷售業)之間企業集聚,其引發的適度競爭有利于服務企業努力改善業務流程,增強服務創新能力,推出適應制造業發展需求的差異化服務,從而降低服務價格,對制造業投入成本的降低和競爭力提升產生積極影響。從產業屬性上講,功能型服務業為制造業提供的是一種增加商業便利、拓展交易通道的服務。隨著現代產業鏈的發展動力逐漸由生產端驅動轉向采購端驅動,這類服務集聚業態(比如商貿會展業中的專業市場、批發零售業中的大型連鎖零售超市等)在產業鏈整合優化中的決定性作用不斷強化,則其集聚組織內各服務企業間、乃至集聚組織間的相互競爭,還會形成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某種倒逼機制。也就是說,既連接最終消費者、又連接制造業企業的功能型服務業可充分利用其消費者顧客信息優勢,以產業鏈主導者的身份提升整個產業鏈條的績效水平。通過功能型服務業空間集聚,不同服務商之間的競爭壓力以及與之相伴隨的來自全國乃至全球的產、供、銷信息,便通過產業鏈的后向傳遞施加給了制造企業,促使后者降低成本,加強創新,不斷推出附加值更高、更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并突破全球價值鏈分工路徑依賴和自我鎖定,實現轉型升級。例如,浙江義烏集聚發展專業市場服務商及其衍生的物流、會展、電子商務、信息集成處理等配套服務業,帶動了小商品制造業的發展與升級(劉亦、夏杰長,2010)。2.合作帶來的外溢效應不同功能型服務業間存在著有機聯系、協同合作的基礎,它們都在提供商業便利基礎上,降低區域制造業的貿易成本和交易風險,減少交易費用。于是,制造業價值鏈的整體集成能力和競爭能力也就經由這些行業的緊密合作而得以提升。如通過區域物流業集聚整合,形成相互關聯作用的各物流功能要素所構成的、具有一系列采購、加工、倉儲、配送、信息管理等功能的有機整體,為制造企業提供在供應鏈上從始到終的一體化服務,從而提升集群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效率,顯著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特定制造業上下游企業之間的相互銜接和制造業效率的增進(王艷玲,2011)。同時,根據特定區域產業發展特征,不同功能型服務業態集聚的協同合作模式創新不僅可為制造業帶來貿易成本縮減的放大效應,往往還能進一步與制造業共同形成一條新的價值鏈條,從而推動制造業向新型發展模式演變。比如,廣西南寧商品交易所依托所在中心城市商貿、電子交易、物流倉儲等服務業集聚優勢,引入期貨交易方式,推出了甘蔗糖蜜(甘蔗制糖的副產品,可再次投入化工產品生產)中遠期電子交易,對促進廢棄物資源定價和循環利用,激勵區域制糖、化工等上下游企業實現綠色轉型起到了推動作用。綜上,功能型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外溢效應的實質是通過降低制造業價值鏈的貿易成本,使制造業取得了成本上的剩余。功能型服務業集聚不僅通過合并制造業的基本運營流程使之獲得規模經濟,還滲透出創新性元素,調整和優化制造業價值鏈,推動制造業向要素投入和資源消耗成本更低的發展模式轉變。制造業轉型升級后又對功能型服務業提出更高的多樣化需求,從而強化后者集聚的規模報酬遞增效應并加深集聚程度,再次對制造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支持,形成累積循環因果機制。(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機理另一種制造業價值鏈活動為支持活動,包括公司的基礎建設(如財務、企劃)、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發展、采購等[13]。這些專業服務獨立后,形成金融財富管理、人力資源、科技研發、商務咨詢等服務業。上述服務業的投入和產出主要是知識,稱為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表現出更多樣化的地理集中特征:既可在制造業園區及周邊集聚,也很顯著地在集聚經濟圈的大都市及其中央商務區集聚。因為知識型服務企業的發展十分需要與同行和相關行業之間的交流和知識共享,需要更為便捷有效和低成本的信息傳輸,這要求多樣化經濟作為支撐。大型城市以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性基礎設施、多樣化的產業配套、完善的公共服務、融洽的社會氛圍吸引了這類服務業集聚。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具有典型的技術外部性,即一種基于技術交流和知識擴散的產業關聯。它不僅發生在服務業內部,還發生在其與制造業之間,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產生了有力的助推作用。這種知識溢出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面對面交流。獨立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相比內化在制造業部門內類似的職能有更高的專業化水平,可通過集聚加快服務技術和產品創新,生產大量知識,包括可編碼知識、緘默知識或黏性知識。通過知識型服務業與制造業從業人員的面對面交流以及持續重復的接觸,使知識尤其后兩種極具地方化色彩的知識能及時輸入制造業中,轉化為產品、技術升級或綠色轉型的動力。二是熟練勞動力的行業間流動。熟練勞動力一定程度上可視為知識的載體。知識型服務業集聚地提供了一個區域熟練勞動力的共享池,使得不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之間、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和制造業之間的人員流動成為可能并頻繁進行,起到知識傳播和擴散加速器的作用,使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不斷根據制造業的發展現狀和趨勢提供更有效的創新服務支持。三是通過信息網絡傳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地的知識信息不斷匯聚、篩選、整合,借助優良的信息網絡渠道向不同半徑的制造業傳輸擴散,使其獲得持續不斷的市場、技術、行業新信息和增值服務,滿足轉型升級的需要。在一個集聚經濟圈內,不同類型城市的產業基礎、要素投入特征和區位環境存在顯著差異,這為城市群產業分工協作并獲取整體經濟性創造了條件。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和制造業若在集聚經濟圈中心城市和外圍不同類型城市錯位集聚,即金融、研發、商務及大型企業或機構的管理總部向中心城市集聚,制造業向中小城市轉移,便可利用不同城市的比較優勢生產相應的產品和參與相應的企業職能環節,在優勢互補的基礎上實現二、三產業資源的區域優化配置[10],提高區域制造業整體效率,促其轉型升級。所以,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有利于知識的加速生產和積累,并通過知識空間溢出,為制造業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并隨著經濟圈內城市間產業空間結構的優化,提升區域產業資源配置效率。總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使制造業取得了一種收益上的剩余,有利于加速創新,驅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反過來,這又強化了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規模報酬遞增效應,有利于制造業持續升級,形成累積循環因果機制。歸納上述,功能型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分別通過貿易成本縮減效應、創新收益提升效應等兩種中介效應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產生積極的外溢作用(見圖1)。圖1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機理圖示
endprint
三、實證檢驗本實證研究的地域單位為城市。相比省域,以城市為對象可更精確地描述產業集聚,進而可更明確揭示不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特征對制造業外溢作用的異質性。目前,我國缺乏系統的城市制造業統計資料,因此只能從各城市統計年鑒中收集。但不同年份不同城市統計年鑒的可得性有顯著差別。為盡量擴大樣本,本研究選擇2009年122個城市(直轄市、地級市)的制造業數據進行橫截面分析。生產性服務業數據則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0》整理。其中,功能型服務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零售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制造業范圍根據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確定。(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外溢作用的檢驗1.變量選取(1)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測度。基礎指標有:①制造業利潤率,以城市制造業利潤總額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表示。制造業要素投入和資源利用結構的轉變和升級,最終將體現在效益提升上。相比勞動生產率等非市場化效率指標,利潤率更能體現制造業企業在競爭中實現產出價值和創造最終收益的能力。②制造業規模比,以城市制造業總產值占當年全國制造業總產值的比例表示。引入該指標是為了改善由于部分城市特定制造業(如制酒業)利潤率偏高造成的扭曲。筆者認為,只有在積極發展那些體現新興市場需求、運用新興技術及成長迅速的制造業過程中實現效率和效益的提升,才是真正的產業轉型升級和又好又快發展。運用極值處理法將上述指標分別轉化為[0,1]內的相對指標lr和gm,并設置相同權重,得制造業轉型升級綜合指標sj=0.5lr+0.5gm。(2)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度的測度。由于對服務業的統計遺漏較多,服務業的真實規模和比重常被低估,采用產業規模類指標測度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不夠合適[2]。參考有關研究[12],本文使用行業就業人數計算區位熵衡量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度:jj=PSiPSPiP。其中,PSi為第i市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數,PS為全國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數;Pi為第i市從業人數,P為全國從業人數。(3)虛擬變量。直轄市、各省會與國內發達經濟圈主要工業城市的經濟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均處領先位置,通過服務業集聚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內在能力和外部環境不僅具備,可能還會更強。設虛擬變量D1檢驗該推斷:屬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經濟圈城市及其他省會城市或直轄市取1,否則取0。D1jj為發達城市外溢自身加強作用指標,若其顯著,則需關注不同城市通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基礎條件與集聚方式的異質性。同時,生產性服務業發達的城市,還可通過知識的區域性溢出,形成對鄰近城市制造業的輻射作用。設另一虛擬變量D2檢驗直轄市、省會城市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與之相鄰的外省城市或省內城市制造業升級有無作用為:與所在省會或直轄市S相鄰的城市取1,否則取0。D2sjjs為中心城市輻射作用指標。這些虛擬變量涉及樣本城市的經濟基礎和區位稟賦因素,有助于減少檢驗偏誤。2.模型估計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1),使用Eviews60回歸,結果見表1:sj=C+β1jj+β2(D1jj)+β3(D2sjjs)+μ(1)
表1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外溢作用檢驗結果變量系數t值C0.2729.927jj-0.122-1.098D1jj0.2873.831D2sjjs0.0420.966DW=1.814;F=8.675;R2=0.68dU=174
yy = β1 jj1 + ε2 (3)
sj = α′1 jj1 + γ1 yy + ε3 (4)sj = α2 jj2 + ε′1 (5)
xc = β2 jj2 + ε′2 (6)
sj = α′2 jj2 + γ2 xc + ε′3 (7)在對變量原始數據標準化處理后,利用Eviews60進行OLS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表2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中介效應檢驗結果模型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系數系數估計值P值結論(2)sjjj1α10.120***0.003系數α1顯著,可進行中介效應檢驗(3)[]yy[]jj1[]β1[]0.495***[]0.000[]系數β1、γ1均顯著,可進行完全中介效應檢驗(4)[]sj[]yy[]γ1[]0.242***[]0.002[][]jj1[]α′1[]0.00096[]0.985[]系數α′1不顯著,存在完全中介效應(5)sjjj2α20.2110.174系數α2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不顯著,不存在中介效應注:***表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4.結果分析對集聚經濟圈中心城市和先發工業化城市,功能型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具有完全的貿易成本縮減效應;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通過加速創新并提供收益剩余來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中介效應尚未形成。(1)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中除金融業外的行業發展還存在不足,創新效應及對制造業的服務功能不強。首先,在42個樣本城市中,租賃與商務服務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發展規模還較低。有28個城市上述三個行業的從業人數少于功能型服務業從業人數50%,這種狀況限制了對制造業創新提供強有力的技術和人才支持,導致中介作用不顯著。其次,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區運營管理不夠完善,阻斷了創新中介橋梁。當前我國知識型服務業集聚區的發展正從成本競爭的初級階段向創新型集群轉變,創新網絡和機制還需進一步構建。很多集聚區采取行政層級化管理,極大降低了服務企業應對迅速變化的市場技術條件的警覺和能力,減少了創新概率;同時,集聚區內非正式交流的場所和中間性服務組織還比較缺乏,使服務企業難以經常互相學習,技術外部性無法體現[15]。(2)金融業集聚對制造業創新與重構的作用受到制度性因素制約。42個樣本城市的金融業在生產性服務業中的從業人數占比平均達21%,最高達50%,集聚程度較高,但對制造業的溢出效應卻并不理想。首先,在以間接融資為主的中國,銀行貸款是制造業的基本“輸血管道”。許多小微企業雖擁有較強的創新意愿,但由于獲得貸款的條件嚴苛(如一般需提供抵押擔保),很難得到傳統信貸對創新的支持。而即便更易獲得貸款的大中型企業,貸款在創新活動支出的比例也很小。2000-2008年我國大中型企業科技創新活動經費來自貸款的比例僅在5%-10%。這從側面反映出,當前我國還非常缺乏針對制造企業特別是小微型企業創新融資困境、由正規金融或第三方機構提供的間接融資特色服務及配套制度安排。其次,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大型中心城市集聚了大批證券公司等直接融資類金融機構。然而,資本市場中事前準入的行政審批制,對違規造假上市公司懲罰力度明顯不足等因素,使得投資銀行集聚為制造業提供的資本增值服務效應嚴重扭曲。
四、政策啟示首先,各級政府應根據本區域或城市產業發展的基礎、趨勢和區位特征,把握集聚生產性服務業以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臨界點,并將此作為引導二、三產業協調演進與區域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戰略切入點。由于不同區域和城市制造業轉型升級中利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方式有所區別,各類城市應積極融入區域或經濟圈分工體系,深化產業分工協作,合理構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格局。對于大型中心城市和其他先發工業化城市,可以全面推進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并充分發揮對經濟圈內其他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而對于中小城市,應圍繞其主導或者支柱制造業轉型發展和優化升級的具體目標,有側重地形成與之配套的生產性服務業體系化或特色化集聚。其次,政府還應努力在產業發展環境、經營環境、創新環境及基礎制度的建設和優化上下功夫,通過實施保障政策,為以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實踐提供外部動力。一是圍繞提升知識生產和外溢的能力,努力構建促進服務業高端創新要素集聚的城市綜合環境,提高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的集聚度;妥善利用政策扶持引導功能,增強知識型服務業集聚區創新能力;協調優化經濟圈尤其是跨省區創新資源布局,提高區域創新整體效益,形成以區域性中心城市為龍頭、重要先發工業化城市為關鍵節點的創新型服務業空間結構,強化中心城市的輻射效應。二是圍繞提升服務要素集聚的設施保障力,積極改善交通、現代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制造業服務化進程,努力降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經營成本和商務成本[16]。三是圍繞提升服務經濟關鍵性基礎制度的支撐力,培育多元化服務競爭主體,加強信用管理、知識產權保護,創造服務業自由有序的競爭環境;破除區域和城際貿易壁壘,促進關鍵服務要素合理流動組合與合意配置;以支持制造業產品、技術、資源利用、資本運營創新升級為目標,尋求金融市場監管、財政稅收等制度或政策改革新突破,增強生產性服務業態集聚模式創新的良性外部效應。
參考文獻:
[1] 李文秀,譚力文.服務業集聚的二維評價模型及實證研究——以美國服務業為例[J].中國工業經濟,2008(4):55-63.
[2] 陳建軍,陳國亮,黃潔.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來自中國222個城市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09(4):83-95.
[3] 但斌,張樂樂,錢文華.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區域性集聚分布模式及其動力機制研究[J].軟科學,2008(3):5-8.
[4] Duranton,G.,Puga,D.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satio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5,57:343-370.
[5] 陳建軍,陳菁菁.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同定位研究——以浙江省69個城市和地區為例[J].中國工業經濟,2011(6):141-150.
[6] 劉曙華.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區域空間重構[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
[7] Dan O Donoghue,Bill Gleave.A Note on Methods for Measuring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J].Regional Studies,2004,38(4):419-427.
[8] Meyer,S.P.Finance,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 firms and the nature of agglomeration advantage across Canada and within metropolitan Toronto[J].Canadian Journal of Urban Research,2007,16(2):149-181.
endprint
[9] 藤田昌久,蒂斯.集聚經濟學——城市、產業區位與區域增長[M].劉峰,譯.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10]蘇紅鍵,趙堅.經濟圈制造業增長的空間結構效應——基于長三角經濟圈的數據[J].中國工業經濟,2011(8):36-46.
[11]顧乃華.生產性服務業對工業獲利能力的影響和渠道——基于城市面板數據和SFA模型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0(5):48-58.
[12]顧乃華.我國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工業的外溢效應及其區域邊界——基于HLM模型的實證研究[J].財貿經濟,2011(5):115-122,44.
[13]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M].李明軒,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14]侯杰泰,溫忠麟,成子娟.結構方程模型及其應用[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
[15]高運勝.上海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發展模式研究[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9.
[16]李翠霞,葛婭男. 我國原料乳生產模式演化路徑研究——基于利益主體關系視角[J].農業經濟問題,2012(7):33-38.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Test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ZHAN Hao-yong,FENG Jin-li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iuzhou 545006,China)
Abstract:Through mediating effects brought by reduction of trade cost and increase of innovation benefit proposed by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 empirical study shows such spillover effects not only depend on supports of economic basis and location environment of city, but also break constraints that prevent transition of the spillover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has shown in those regionally central and early industrialized citi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no innovation-driven effect over manufacturing resulted from knowledge intensive services agglomeration.
Key words: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mechanism of action;mediating effect
(責任編輯:陳樹明)
endprint
[9] 藤田昌久,蒂斯.集聚經濟學——城市、產業區位與區域增長[M].劉峰,譯.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10]蘇紅鍵,趙堅.經濟圈制造業增長的空間結構效應——基于長三角經濟圈的數據[J].中國工業經濟,2011(8):36-46.
[11]顧乃華.生產性服務業對工業獲利能力的影響和渠道——基于城市面板數據和SFA模型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0(5):48-58.
[12]顧乃華.我國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工業的外溢效應及其區域邊界——基于HLM模型的實證研究[J].財貿經濟,2011(5):115-122,44.
[13]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M].李明軒,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14]侯杰泰,溫忠麟,成子娟.結構方程模型及其應用[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
[15]高運勝.上海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發展模式研究[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9.
[16]李翠霞,葛婭男. 我國原料乳生產模式演化路徑研究——基于利益主體關系視角[J].農業經濟問題,2012(7):33-38.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Test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ZHAN Hao-yong,FENG Jin-li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iuzhou 545006,China)
Abstract:Through mediating effects brought by reduction of trade cost and increase of innovation benefit proposed by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 empirical study shows such spillover effects not only depend on supports of economic basis and location environment of city, but also break constraints that prevent transition of the spillover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has shown in those regionally central and early industrialized citi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no innovation-driven effect over manufacturing resulted from knowledge intensive services agglomeration.
Key words: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mechanism of action;mediating effect
(責任編輯:陳樹明)
endprint
[9] 藤田昌久,蒂斯.集聚經濟學——城市、產業區位與區域增長[M].劉峰,譯.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10]蘇紅鍵,趙堅.經濟圈制造業增長的空間結構效應——基于長三角經濟圈的數據[J].中國工業經濟,2011(8):36-46.
[11]顧乃華.生產性服務業對工業獲利能力的影響和渠道——基于城市面板數據和SFA模型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0(5):48-58.
[12]顧乃華.我國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工業的外溢效應及其區域邊界——基于HLM模型的實證研究[J].財貿經濟,2011(5):115-122,44.
[13]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M].李明軒,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14]侯杰泰,溫忠麟,成子娟.結構方程模型及其應用[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
[15]高運勝.上海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發展模式研究[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9.
[16]李翠霞,葛婭男. 我國原料乳生產模式演化路徑研究——基于利益主體關系視角[J].農業經濟問題,2012(7):33-38.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Test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ZHAN Hao-yong,FENG Jin-li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iuzhou 545006,China)
Abstract:Through mediating effects brought by reduction of trade cost and increase of innovation benefit proposed by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 empirical study shows such spillover effects not only depend on supports of economic basis and location environment of city, but also break constraints that prevent transition of the spillover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has shown in those regionally central and early industrialized citi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no innovation-driven effect over manufacturing resulted from knowledge intensive services agglomeration.
Key words: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mechanism of action;mediating effect
(責任編輯:陳樹明)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