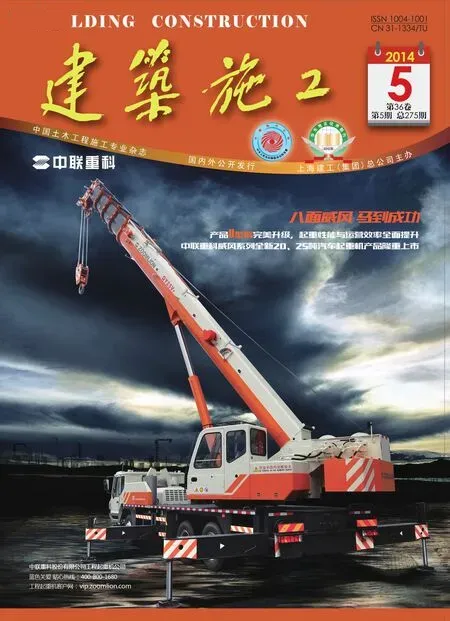特殊環境下基坑工程的監測與分析
上海機場建設指揮部 上海 201202
1 工程概況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T1航站樓流程改造工程——旅客捷運系統土建預留工程包括車站、連廊段區間、渡線段區間、設備段區間及工作井5 個部分,工程范圍均位于T1航站樓主樓(南北向)與候機長廊(南北向)之間的中庭區域,并穿越二者之間的南連廊(東西向)樁基承臺。
車站區簡稱為CD區,為整個工程的中心部分,基坑平面形狀為狹長形,面積約為5 560 m2,周邊約616 m,基坑常規開挖深度達到了8.7 m,承臺落深區域最大開挖深度達到了10.9 m。基坑圍護采用Φ800 mm鉆孔灌注樁,灌注樁外側設置止水帷幕,受航站樓外傾玻璃幕墻影響,止水帷幕均采用雙排Φ800 mm旋噴樁,距主樓和候機長廊承臺最近距離為0.8 m 。基坑設2 道支撐順作開挖,首道為800 mm×800 mm混凝土支撐,下落1.7 m,支撐水平間距約6 m,第2道支撐在直撐段為Φ609 mm×16 mm鋼支撐,在斜撐段仍為混凝土支撐,以控制變形。
2 工程地質條件
根椐本工程巖土工程勘察報告,建設場地缺失上海市統編第⑥層暗綠色硬土層和第⑧層灰色黏性土層,場地各巖土分層為:①層雜填土,成分復雜,厚度變化較大,②1層褐黃-灰黃色粉質黏土,第②2層灰色黏質粉土夾淤泥質粉質黏土和第②3層灰色砂質粉土;第③1層灰色淤泥質粉質黏土、第③2層灰色砂質粉土;第④層灰色淤泥質黏土;第⑤1層灰色黏土、第⑤3層灰色粉質黏土和第⑤4層灰綠-草黃色粉質黏土;第⑦2-1層草黃色粉砂和第⑦2-2層草黃-灰色粉砂。
3 工程難點分析
3.1 四邊既有建筑結構
基坑東西兩側分別為T1航站樓主樓與候機長廊,全部為樁基基礎,兩側建筑的基礎承臺與基坑圍護邊線距離最近處僅為2 m。基坑南北兩側均為航站樓連廊,結構基本相同,首層架空,承臺埋深3.02 m,承臺高2 m,承臺與基坑圍護邊線距離約6 m。既有建筑物承臺距離基坑極近,基坑施工對既有建筑物基礎的影響不可避免,對施工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3.2 基坑東西側淺層積水
東西兩側建筑物基礎底板埋深約0.4 m,底板下部有雨污水管道通過,且回填土沉積時間較長,底板已變為架空結構,空腔部分被水填充,基坑東西兩側淺部已被水包圍,增加了施工難度,對基坑的止水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3.3 施工條件
基坑東西兩側建筑物底板下部的積水,以及基坑周邊松散的淺部土,為止水帷幕的施工效果提出了挑戰。基坑與建筑物間距較小,加上東西兩側玻璃幕墻的外傾,導致基坑上部施工空間較小,為圍護、止水帷幕等的施工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4 基坑監測方案
通過現場監測,及時掌握基坑的變形情況和對周邊環境的影響,及時調整施工方案和施工步驟,以達到有效地指導施工現場、優化施工、安全施工和避免事故發生的目的[3]。
根據本工程監測技術要求和現場施工具體情況,本監測方案需要做到:以基坑施工區域周圍2 倍基坑開挖深度范圍的建筑物、周邊土體和基坑圍護結構本身作為本工程監測及保護的對象,監測點平面布置見圖1。具體監測內容見表1,監測報警值見表2。

圖1 基坑監測點平面布置

表1 基坑監測內容

表2 基坑監測報警值
5 監測結果分析
5.1 圍護體傾斜(深層水平位移)分析
根據基坑受力分析和實際經驗,一般情況下基坑長邊中部變形最大,角部變形較小,故選擇東側中間部位的P04孔進行數據分析,歷時曲線如圖2。本基坑東南角處出現了漏水并注漿堵漏,變形較大,故選擇漏水處的P07測斜孔進行數據分析,歷時曲線如圖3。

圖2 P04測斜孔隨開挖時間的變形曲線

圖3 P07測斜孔隨開挖時間的 變形曲線
由圖2和圖3可知,基坑開挖過程中,圍護墻體的最大水平位移與開挖深度和時間的關系密切。圍護墻體水平位移量隨著開挖的進行不斷地變大,隨著開挖深度的加深,各個測點的側向位移逐步加大,尤其是挖土工況導致地下連續墻側向位移增長最快,基坑開挖面附近深度水平變形增大迅速,基坑圍護墻底部也有一定的變化[4]。圍護墻的水平位移大小及分布與基坑開挖深度、圍護結構體剛度、支撐系統的剛度、地質狀況、地面超載等因素有關。
在基坑開挖階段,開挖第1層土到第2道支撐位置處,深約5.7 m,P02孔和P07孔變形都不大,P02孔最大值不超過3 mm,P07孔不超過5 mm,變形控制比較可觀。從第2道支撐底繼續下挖到基坑底部時,墻體的的水平位移迅速增大,最大水平位移都出現在當前開挖階段的開挖面附近,由此可見,墻體水平位移的最大值處于在當前開挖面附近,墻體的變形不僅發生在開挖面以上,開挖面以下也會產生一定的變形。澆筑墊層后,圍護墻體的水平位移變形速率迅速下降,但墻體水平位移依然有增大趨勢。直至底板澆筑完成,墻體水平位移變化才明顯減緩,不過,地下結構施工階段, 圍護墻體變形依然有變形,依然占有一定的比例,說明上海軟土的流變性質對基坑變形的發展影響也很大[5-7]。
從P02孔和P07孔變形歷時曲線圖可以看出,雖然P02處于基坑長邊中部,但P07孔的累計變形卻較大,這主要是由于在第1層土開挖階段,P07孔附近墻體出現漏水,坑外進行了注漿堵漏,注漿壓力對墻體產生了一定的擠壓,導致了P07孔在第2層土方開挖階段,產生了大量的變形,其累計量超過了P02孔。
5.2 支撐軸力分析
由數據分析可知,本基坑的第1道支撐軸力最大值出現在基坑角撐與直撐過度部位,主要是由于此處支撐間距較大,支撐需要平衡的土壓力就較多,故表現為較大值。
本基坑第1道支撐和第2道支撐的角撐為混凝土支撐,混凝土支撐澆筑完畢后,由于混凝土硬化過程中體積有一定的收縮,混凝土就會對握裹的鋼筋產生壓力,在基坑未開挖前支撐內部已經產生了一定數量級的壓應力,而軸力的初始值是在支撐養護完畢后測得,所以此時計算出來的支撐軸力表現為拉應力,這是由于混凝土支撐的本身材料特點決定的。從由圖4和圖5可以很明顯看出混凝土支撐的這個特點。

圖4 第1道支撐軸力隨開挖時間變化曲線

圖5 第2道支撐軸力隨開挖時間變化曲線
本工程第2道鋼支撐采用的軸力自動補償系統,軸力自動補償支撐系統實現了傳統施工技術與液壓控制技術以及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結合,對支撐軸力變化實施全天候監測和自動補償,使支撐軸力始終處于恒定狀態,克服了傳統預應力隨時間不斷損失的缺陷,減小了基坑變形,使基坑變形始終處于可控狀態。從圖5可以看出,軸力自動補償系統鋼支撐的支撐軸力一直處于恒定狀態,而混凝土支撐的支撐伴隨著基坑的開挖變形,軸力不斷增大。
5.3 立柱隆沉分析
由圖6可知,在基坑開挖初期,立柱隆沉變化不大,部分測點由于位于棧橋下,受重車來往影響,還有所下沉。隨著基坑開挖深度的增加,坑內土體卸載造成坑底土體回彈,帶動立柱上升。開挖第1層土時,立柱明顯抬升,挖到第2道支撐處,隨著挖土的暫停,立柱抬升也慢慢趨緩,隨著第2層土的繼續開挖,立柱又慢慢抬升,不過速率大大減小,底板澆筑后,立柱隆沉基本穩定。立柱抬升最大值沒有超過25 mm,說明基坑開挖雖然對坑內立柱上升有影響,但未對工程施工造成不良影響,依舊在控制范圍內。

圖6 立柱隆沉時間變化曲線
5.4 周邊承臺隆沉分析
通過觀察監測數據曲線后發現,90~180 d期間,基坑東側航站樓承臺沉降曲線出現了1 個拋物線形的變化過程,先猛烈抬升,后慢慢回落。結合工況分析可知,前期抬升主要是由于基坑外圍的止水旋噴樁施工所致,旋噴樁施工一方面對原狀土體產生了擾動,另一方面注漿有壓力產生,在二者的綜合作用下,承臺出現了明顯抬升。130~180 d期間,隨著注漿施工的完成和基坑挖土的開始,曲線變化呈持續下降趨勢,說明此階段土方開挖導致了圍護結構和外側土體向坑內變形,引起周邊建筑物沉降。
180 d以后,承臺沉降曲線又出現了先抬升后下沉的過程,不過變形幅度有所緩和,據分析,是由于東側圍護出現了數處漏水,注漿加固導致了承臺的抬升,隨著基坑挖土、地下結構施工等工序的進行,承臺慢慢下沉并穩定,變化曲線趨近水平。270 d之后,沉降曲線有所下降,此時基坑正在進行支撐拆除施工,說明支撐的拆除間接影響到建筑物的沉降。
6 結語
深基坑開挖引起周邊土體變形,對基坑圍護結構和周邊環境都會產生不良影響。因此,深基坑工程開挖不僅要保證基坑本身的安全與穩定,而且還要嚴格控制基坑周圍地層移動以保護周圍建筑物。特別是在特殊環境下,周邊環境的特殊性為基坑的設計、施工和監測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所以在基坑施工過程中,對基坑和周邊環境進行實時監測,對數據進行跟蹤分析,判斷基坑工程的現時安全性,優化下一步施工參數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