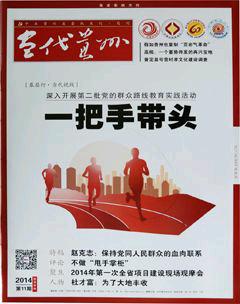紀檢人員的政績觀價值觀
梁衡,本刊顧問,當代作家,著名的新聞理論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論家,人教版中小學教材總顧問,歷任《內蒙古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2014年新年剛過中央就召開了紀檢工作會。十八大之后報上公布的副部級以上被查貪官已達18名,今年注定將是一個反貪年、廉政風暴年。不由聯想到歷史上的反貪。
唐以后專設監察機關諫院和御史臺,設有專職諫官和御史,“糾察官邪,肅正綱紀”。他們常常大膽到冒犯皇帝,搬倒了一個個貪官、奸臣,名垂青史。這除了制度保證,他們有話語權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上下都認同的政績觀和價值觀。就是皇帝對他們也是不敢太過。
身在監察之職的官員是干什么的?是與邪惡斗爭,查處違規違紀,這就是他們的GDP,不管蒼蠅、老虎,查處愈多成績愈大。如果在任期間沒有彈劾、搬倒幾個壞官,反倒會被人譏笑無能,瞧不起。如果因敢于堅持原則而被打擊,反受人尊敬,名聲大漲。如唐朝的諫臣魏征,多次當面批評唐太宗。
北宋范仲淹任諫官時因為在廢皇后問題上頂撞皇帝被貶出京,發配睦州,這是他第二次被眨(后又被請回)。他27歲中進士,64歲去世,為官37年,因為直諫四起四落,在京城工作總共不到四年。歐陽修評價他“直辭正色,面爭庭對”,“敢與天子爭是非”,是為一代名臣。
比范仲淹稍晚一點,也是宋仁宗朝的御史唐介,反對皇帝給他的貴妃伯父加官,揭發宰相給貴妃送禮,走“婦人路線”,被眨出京,發配廣東,卻贏得一片贊揚聲。士大夫們紛紛賦詩送行,說他:“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后又被請回。史稱“真御史”。歷史上還有許多身在官場體制內,又敢于反貪、除奸的如包公這樣的人物。在傳統政治中已經形成了一個政績觀和價值觀:說真話,干好分工內的實事。
我們早就有一支專業的紀檢隊伍,而且給了紀檢部門很大的權力,很高的待遇(與班子成員同級別)。許多單位還給予與工作無關的特別關照,比如每年出國訪問、其他福利等。但是相比之下在十八大前動靜并不大,特別是本單位的、同級的紀檢很少查出問題。而民間反貪,特別是網絡監督倒很活躍,上級派巡視組也很見效。現在中央已從制度上作了改進,但還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要從理論上、輿論上說清并大力宣傳紀檢人員的政績觀和價值觀,要以反貪為任,以反貪為榮,專業隊伍應有專門業績,這個行當中應多出幾個像歷史上的名諫官、御史一樣的名人。要樹起一批“當代包公”、“紅色包公”的形象。只有一個王岐山不夠,各級都要有。(責任編輯/吳文仙)
鏈接
古代“紀檢干部”的品質要求
中國古代,“紀檢干部”擔負著風憲重任,“糾劾官邪”、“匡輔人君”,選擇什么樣的人來行使這一權力,是決定監察目的能否實現的一個關鍵因素。為此,歷代統治者就“紀檢干部”的選拔任用環節建立起了相對完備的制度,強化“紀檢干部”素質和能力的要求。《冊府元龜·憲宮部》里說:“夫憲官之職,大則佐三公統理之業以宣導風化,小則正百官紀綱之事以糾察是非,故漢魏以還,事任尤重,至于選用,必舉賢才。”
宋代司馬光曾說:“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清官包拯亦言,“紀檢干部”“自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
實踐中,歷代在“紀檢干部”選任上,都首重德行。
漢代作為選官主要方式的察舉制度正是以薦舉諫官而開其端。
唐時“凡所取御史,必先質重勇退者”。
明代朱元璋要求擔負“六部”對口監察職責的六科給事中“不愛富貴”而“惜名節”,要求他們“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要“國而忘家,忠而忘身”,為朝廷、為皇帝不惜身家性命。
清順治年間上諭:內官考選科道必須才德兼優之員,外官必須錢糧全完,且任內“無參罰者”方準行取。
梁衡,本刊顧問,當代作家,著名的新聞理論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論家,人教版中小學教材總顧問,歷任《內蒙古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2014年新年剛過中央就召開了紀檢工作會。十八大之后報上公布的副部級以上被查貪官已達18名,今年注定將是一個反貪年、廉政風暴年。不由聯想到歷史上的反貪。
唐以后專設監察機關諫院和御史臺,設有專職諫官和御史,“糾察官邪,肅正綱紀”。他們常常大膽到冒犯皇帝,搬倒了一個個貪官、奸臣,名垂青史。這除了制度保證,他們有話語權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上下都認同的政績觀和價值觀。就是皇帝對他們也是不敢太過。
身在監察之職的官員是干什么的?是與邪惡斗爭,查處違規違紀,這就是他們的GDP,不管蒼蠅、老虎,查處愈多成績愈大。如果在任期間沒有彈劾、搬倒幾個壞官,反倒會被人譏笑無能,瞧不起。如果因敢于堅持原則而被打擊,反受人尊敬,名聲大漲。如唐朝的諫臣魏征,多次當面批評唐太宗。
北宋范仲淹任諫官時因為在廢皇后問題上頂撞皇帝被貶出京,發配睦州,這是他第二次被眨(后又被請回)。他27歲中進士,64歲去世,為官37年,因為直諫四起四落,在京城工作總共不到四年。歐陽修評價他“直辭正色,面爭庭對”,“敢與天子爭是非”,是為一代名臣。
比范仲淹稍晚一點,也是宋仁宗朝的御史唐介,反對皇帝給他的貴妃伯父加官,揭發宰相給貴妃送禮,走“婦人路線”,被眨出京,發配廣東,卻贏得一片贊揚聲。士大夫們紛紛賦詩送行,說他:“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后又被請回。史稱“真御史”。歷史上還有許多身在官場體制內,又敢于反貪、除奸的如包公這樣的人物。在傳統政治中已經形成了一個政績觀和價值觀:說真話,干好分工內的實事。
我們早就有一支專業的紀檢隊伍,而且給了紀檢部門很大的權力,很高的待遇(與班子成員同級別)。許多單位還給予與工作無關的特別關照,比如每年出國訪問、其他福利等。但是相比之下在十八大前動靜并不大,特別是本單位的、同級的紀檢很少查出問題。而民間反貪,特別是網絡監督倒很活躍,上級派巡視組也很見效。現在中央已從制度上作了改進,但還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要從理論上、輿論上說清并大力宣傳紀檢人員的政績觀和價值觀,要以反貪為任,以反貪為榮,專業隊伍應有專門業績,這個行當中應多出幾個像歷史上的名諫官、御史一樣的名人。要樹起一批“當代包公”、“紅色包公”的形象。只有一個王岐山不夠,各級都要有。(責任編輯/吳文仙)
鏈接
古代“紀檢干部”的品質要求
中國古代,“紀檢干部”擔負著風憲重任,“糾劾官邪”、“匡輔人君”,選擇什么樣的人來行使這一權力,是決定監察目的能否實現的一個關鍵因素。為此,歷代統治者就“紀檢干部”的選拔任用環節建立起了相對完備的制度,強化“紀檢干部”素質和能力的要求。《冊府元龜·憲宮部》里說:“夫憲官之職,大則佐三公統理之業以宣導風化,小則正百官紀綱之事以糾察是非,故漢魏以還,事任尤重,至于選用,必舉賢才。”
宋代司馬光曾說:“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清官包拯亦言,“紀檢干部”“自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
實踐中,歷代在“紀檢干部”選任上,都首重德行。
漢代作為選官主要方式的察舉制度正是以薦舉諫官而開其端。
唐時“凡所取御史,必先質重勇退者”。
明代朱元璋要求擔負“六部”對口監察職責的六科給事中“不愛富貴”而“惜名節”,要求他們“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要“國而忘家,忠而忘身”,為朝廷、為皇帝不惜身家性命。
清順治年間上諭:內官考選科道必須才德兼優之員,外官必須錢糧全完,且任內“無參罰者”方準行取。
梁衡,本刊顧問,當代作家,著名的新聞理論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論家,人教版中小學教材總顧問,歷任《內蒙古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2014年新年剛過中央就召開了紀檢工作會。十八大之后報上公布的副部級以上被查貪官已達18名,今年注定將是一個反貪年、廉政風暴年。不由聯想到歷史上的反貪。
唐以后專設監察機關諫院和御史臺,設有專職諫官和御史,“糾察官邪,肅正綱紀”。他們常常大膽到冒犯皇帝,搬倒了一個個貪官、奸臣,名垂青史。這除了制度保證,他們有話語權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上下都認同的政績觀和價值觀。就是皇帝對他們也是不敢太過。
身在監察之職的官員是干什么的?是與邪惡斗爭,查處違規違紀,這就是他們的GDP,不管蒼蠅、老虎,查處愈多成績愈大。如果在任期間沒有彈劾、搬倒幾個壞官,反倒會被人譏笑無能,瞧不起。如果因敢于堅持原則而被打擊,反受人尊敬,名聲大漲。如唐朝的諫臣魏征,多次當面批評唐太宗。
北宋范仲淹任諫官時因為在廢皇后問題上頂撞皇帝被貶出京,發配睦州,這是他第二次被眨(后又被請回)。他27歲中進士,64歲去世,為官37年,因為直諫四起四落,在京城工作總共不到四年。歐陽修評價他“直辭正色,面爭庭對”,“敢與天子爭是非”,是為一代名臣。
比范仲淹稍晚一點,也是宋仁宗朝的御史唐介,反對皇帝給他的貴妃伯父加官,揭發宰相給貴妃送禮,走“婦人路線”,被眨出京,發配廣東,卻贏得一片贊揚聲。士大夫們紛紛賦詩送行,說他:“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后又被請回。史稱“真御史”。歷史上還有許多身在官場體制內,又敢于反貪、除奸的如包公這樣的人物。在傳統政治中已經形成了一個政績觀和價值觀:說真話,干好分工內的實事。
我們早就有一支專業的紀檢隊伍,而且給了紀檢部門很大的權力,很高的待遇(與班子成員同級別)。許多單位還給予與工作無關的特別關照,比如每年出國訪問、其他福利等。但是相比之下在十八大前動靜并不大,特別是本單位的、同級的紀檢很少查出問題。而民間反貪,特別是網絡監督倒很活躍,上級派巡視組也很見效。現在中央已從制度上作了改進,但還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要從理論上、輿論上說清并大力宣傳紀檢人員的政績觀和價值觀,要以反貪為任,以反貪為榮,專業隊伍應有專門業績,這個行當中應多出幾個像歷史上的名諫官、御史一樣的名人。要樹起一批“當代包公”、“紅色包公”的形象。只有一個王岐山不夠,各級都要有。(責任編輯/吳文仙)
鏈接
古代“紀檢干部”的品質要求
中國古代,“紀檢干部”擔負著風憲重任,“糾劾官邪”、“匡輔人君”,選擇什么樣的人來行使這一權力,是決定監察目的能否實現的一個關鍵因素。為此,歷代統治者就“紀檢干部”的選拔任用環節建立起了相對完備的制度,強化“紀檢干部”素質和能力的要求。《冊府元龜·憲宮部》里說:“夫憲官之職,大則佐三公統理之業以宣導風化,小則正百官紀綱之事以糾察是非,故漢魏以還,事任尤重,至于選用,必舉賢才。”
宋代司馬光曾說:“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清官包拯亦言,“紀檢干部”“自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
實踐中,歷代在“紀檢干部”選任上,都首重德行。
漢代作為選官主要方式的察舉制度正是以薦舉諫官而開其端。
唐時“凡所取御史,必先質重勇退者”。
明代朱元璋要求擔負“六部”對口監察職責的六科給事中“不愛富貴”而“惜名節”,要求他們“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要“國而忘家,忠而忘身”,為朝廷、為皇帝不惜身家性命。
清順治年間上諭:內官考選科道必須才德兼優之員,外官必須錢糧全完,且任內“無參罰者”方準行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