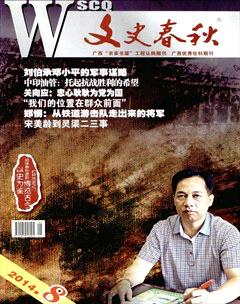程應(yīng)镠的文筆
董寅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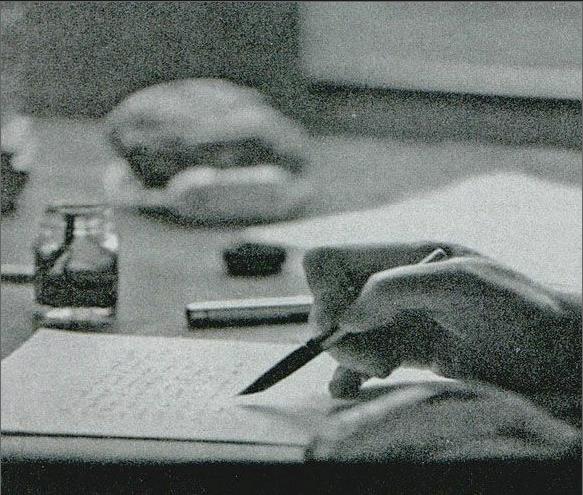
古人以為,所謂史家當(dāng)具三長——史才、史學(xué)、史識,這其中的史才,主要是指史家對歷史事件的敘述能力及對史料的組織功夫,《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所以被后人稱道,很大程度上即由于作者出神入化的文字功夫。假使讓今天的史家,用今天的學(xué)術(shù)語言來寫項羽、李廣、李固、范滂等人的紀(jì)傳,恐怕很難達(dá)到類似的效果。
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yuǎn)”,好的史才,其文字能令人常讀常新、百讀不厭。比如民國時期成長起來的那一代史家,也許在學(xué)術(shù)規(guī)范上不及今天的博導(dǎo)們嚴(yán)整,但純就文字功夫而言,每每讓后人有望塵莫及之恨。大體而言,他們的文字,往往既信、亦達(dá),既美、亦雅,讀者看后,不僅能夠明了其中的大意,還頗有一種閱讀的快感。相比而言,我們今天博士買驢式的學(xué)術(shù)文章,就很少再能給讀者這樣的享受。
久聞程應(yīng)镠《南北朝史話》(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1版)的大名,據(jù)說程先生1963年送部分稿子給吳晗審查,吳晗回信說:“就按這個樣子寫下去,我們打算把它印出來,作為擔(dān)任其他各朝史話作者的參考。”
吳晗之所以如此贊許,恐怕主要是由于程先生的稿子深入淺出,富于文采。我近日重讀此書,也深為程先生的文字打動,其中一些簡潔明快的佳句,今天的文史學(xué)者似已很難寫出來了。
程先生講劉宋時期,“士族的勢力,日漸衰落,象過午的陽光,逐漸西斜”;他寫劉家子孫骨肉相殘,“宮廷里密布著疑云暗劍,公開叛亂和平叛的戰(zhàn)爭幾乎沒有間歇地進(jìn)行著”;他講齊明帝做賊心虛,“在他看來,人世間無處不是陷阱,無地不是網(wǎng)羅,因為他自己便是個慣于設(shè)陷阱張網(wǎng)羅的人”;他講南朝人民墾荒播種,使“綠油油的田疇,代替了過去的叢林茅草……山坡上也出現(xiàn)了一片一片在微風(fēng)中皺起的青蔥”;他寫南北開戰(zhàn),“土地被踐踏,生命被殘害,房屋被焚燒。春天來了,呢喃的燕子找不到舊窠,只好在樹上做巢”等等,都幾乎令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有親身穿越回那個時代的現(xiàn)場感。
我們不少人感嘆史景遷的文筆活靈活現(xiàn),其實(shí),程先生與其相比,何嘗遜色?只是有時,有人不免數(shù)典忘宗,一味沉醉于對西式學(xué)術(shù)語言的效顰,甘心去當(dāng)邯鄲學(xué)步的壽陵余子罷了。
好的史筆,往往簡明扼要又耐人回味。程先生的史話里,這樣的例句比比皆是,比如他說北魏初期,“戰(zhàn)時的擄掠,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平時的貪污,加深了統(tǒng)治者和人民之間的矛盾”,短短幾十字,即概括出北魏當(dāng)時的情勢;他講宇文泰建立府兵制度,“從此,分散的鄉(xiāng)兵逐步納入了朝廷的軍事系統(tǒng)……地方豪強(qiáng)武裝力量的首領(lǐng),成了朝廷的軍官”,不過幾十字就點(diǎn)明了府兵的由來。這樣高屋建瓴、正中肯綮的總結(jié),今天又有幾人能夠做到?
如何將古代史料翻成白話又不失原有的風(fēng)味,歷來是一大難事。程先生在這方面的努力令人敬佩,比如他翻《神滅論》,將“良由厚我之情深,濟(jì)物之意淺”,譯成“自私的打算過多,救人的意思太少”;將“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譯成“用渺茫的謊言迷惑人,用地獄的痛苦嚇唬人,用夸大的言辭引誘人,用天堂的快樂招引人”,不僅準(zhǔn)確生動,而且能將范縝原文那勢不可當(dāng)?shù)臍鈩菀徊鬟f出來,這樣的功夫,今天的學(xué)者大概不易達(dá)到。
程應(yīng)镠先生是1916年生人,那一代人,對古籍不僅通曉,自己也多能寫一手合乎規(guī)矩準(zhǔn)繩的舊詩、古文,所以他們闡釋古代典籍時總是能做到“不隔”。比如他解讀謝朓的“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說這兩句詩,分別“用彩色的綺來比喻落日余暉渲染著的繽紛云影;用潔白的練來形容江水的平靜無波,把人們帶入一幅春江日暮的美妙圖畫中去,心情和景物好像融成了一體”,如此充滿詩意的解讀,真令讀者有如臨其境、美不勝收之感。今日有的文史研究者,往往缺乏這樣的基礎(chǔ),能寫一手合乎規(guī)矩的古詩詞者更是鳳毛麟角,所以在運(yùn)用或闡釋古代材料時,極不易達(dá)到融通、渾成之境,無論怎樣修飾,總不免給人以“古今兩張皮”的感覺。
嚴(yán)耕望先生在《治史經(jīng)驗談·論文體式》中以為:“論文寫作,不僅為作者表達(dá)意見,尤當(dāng)考慮讀者領(lǐng)受之便利。”今天的一些學(xué)者,自己之外,至多再考慮一下編者,至于普通讀者能否讀明白他們的論文,似乎不在考慮之列。放眼望去,不少著述都實(shí)在過分詰屈聱牙,艱深晦澀了。對于這樣的文章,一般讀者大多是敬鬼神而遠(yuǎn)之,偶或有幾個不信邪的,肯硬著頭皮看完,但也往往一頭霧水,不能得其要領(lǐng)。如此拿腔作調(diào)的文風(fēng),實(shí)在已經(jīng)是人文學(xué)科的一大公害了。
《南北朝史話》,論性質(zhì)不過一本普及性質(zhì)的讀物,但這樣力求淺顯的普及讀物,并不易寫。竊以為,今天的史學(xué)工作者們往往無暇做這樣的工作,即使肯做,文字上的功夫也未必就能應(yīng)付裕如。社會上一些粗通史書的作者,倒是憑一知半解就敢下筆,因為無拘無束,故而很能吸引歷史愛好者們追捧,但他們對史料的把握每有粗疏之處,有時候不免錯解了歷史,誤導(dǎo)了讀者。比較而言,像《南北朝史話》這樣既深入、又淺出,既親切、又準(zhǔn)確的普及讀物,今天實(shí)在是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