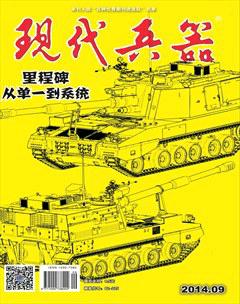東瀛魔翼



日本“心神”驗(yàn)證機(jī)到真正五代機(jī)的距離有多遠(yuǎn)
近日,日本高調(diào)公開了其最新一代驗(yàn)證機(jī)“心神”的照片和視頻資料,其中不乏一些頗有價(jià)值的內(nèi)容。雖然現(xiàn)在的“心神”距離真正的五代機(jī)仍然很遙遠(yuǎn),但作為驗(yàn)證機(jī),它所揭示的發(fā)展?jié)摿θ匀恢档梦覀兠芮嘘P(guān)注。
研發(fā)定位
尺寸和噸位一直是影響戰(zhàn)斗機(jī)造價(jià)的關(guān)鍵因素之一。按照一般規(guī)律來說,戰(zhàn)斗機(jī)越小,其結(jié)構(gòu)制造費(fèi)用也越低;更輕的重量可以讓戰(zhàn)斗機(jī)選用推力更小、價(jià)格更低的發(fā)動(dòng)機(jī),而且耗油率上的經(jīng)濟(jì)優(yōu)勢(shì)會(huì)在批量裝備以后的使用中體現(xiàn)得極為明顯。這也是第二、三代戰(zhàn)斗機(jī)中都不乏空重控制在6~7噸內(nèi)的輕型飛機(jī)的原因所在。
但是,過小的尺寸噸位也會(huì)對(duì)飛機(jī)的作戰(zhàn)性能帶來很大的負(fù)面影響:飛機(jī)沒有足夠的機(jī)身內(nèi)部空間裝載燃油和電子設(shè)備,掛載的武器重量和數(shù)量也有嚴(yán)格限制。尤其是對(duì)于第五代戰(zhàn)斗機(jī)來說,“輕型五代”這一概念實(shí)際上不可能存在,因?yàn)樵诠こ碳夹g(shù)上已經(jīng)無法做到。無論是隱身性能的雷達(dá)反射特征控制要求,還是強(qiáng)化超音速飛行持續(xù)能力的低阻力要求,都迫使五代機(jī)必須采用彈倉內(nèi)置武器設(shè)計(jì)。如果飛機(jī)沒有足夠大的尺寸和噸位,根本無法在機(jī)身內(nèi)安排出足以容納多枚空空導(dǎo)彈、精確制導(dǎo)炸彈的空間用于設(shè)計(jì)彈倉。在某國對(duì)于新一代戰(zhàn)斗機(jī)的探索研究過程中,設(shè)計(jì)人員曾經(jīng)對(duì)低成本型五代機(jī)的噸位尺寸控制做過較為深入的研究。方案迭代的結(jié)果顯示,10噸空重已經(jīng)是五代機(jī)的下限;這個(gè)數(shù)字是在飛機(jī)采用重量最小的無尾三角翼布局,放棄超機(jī)動(dòng)能力和損失一部分短距起降能力后才得到的結(jié)果。
對(duì)于日本的戰(zhàn)斗機(jī)研發(fā)來說,它的作戰(zhàn)環(huán)境和假想目標(biāo)都非常明確,就是在東海、日本海上空與俄羅斯、中國的戰(zhàn)斗機(jī)交戰(zhàn),并具備打擊上海等中國東部沿海地區(qū)、俄羅斯遠(yuǎn)東邊界地區(qū)的能力。這種背景要求下,日本新一代戰(zhàn)斗機(jī)在執(zhí)行對(duì)地攻擊任務(wù)時(shí),作戰(zhàn)半徑至少要達(dá)到800千米以上。從“心神”來看,日本新一代戰(zhàn)斗機(jī)采用了常規(guī)布局設(shè)計(jì)。由于多出一對(duì)平尾和飛機(jī)長度要更大等因素,其重量比無尾三角翼布局要高不少。即使是考慮到日本領(lǐng)先世界的材料工藝,可以通過高比例的先進(jìn)復(fù)合材料大幅度減輕結(jié)構(gòu)重量,其空重至少也要接近12噸才能滿足要求。但是根據(jù)現(xiàn)有信息,“心神”樣機(jī)的起飛重量也不過8噸左右,空重甚至不到6噸,顯然與此標(biāo)準(zhǔn)相差極大。筆者認(rèn)為,“心神”樣機(jī)尺寸特別大、明顯屬于雙座設(shè)計(jì)的座艙蓋,是解釋這一矛盾的關(guān)鍵所在。
和單座飛機(jī)相比,雙座飛機(jī)會(huì)在性能上出現(xiàn)很明顯的損失:飛機(jī)不僅需要付出很大的重量代價(jià)來安裝多出的彈射座椅、儀表臺(tái)、更大面積的座艙蓋等設(shè)備,還損失了相當(dāng)可觀的原本用于裝載燃油的機(jī)內(nèi)空間。事實(shí)上,隨著航電系統(tǒng)的高度綜合化、自動(dòng)化,1名飛行員就足以駕駛戰(zhàn)機(jī)執(zhí)行復(fù)雜的作戰(zhàn)任務(wù),這也是美國、中國、俄羅斯現(xiàn)有五代機(jī)均無雙座設(shè)計(jì)的根本原因。“心神”樣機(jī)采用雙座設(shè)計(jì),噸位尺寸又特別小,這就只有一種解釋:現(xiàn)階段的“心神”既是承擔(dān)氣動(dòng)外形/飛行控制系統(tǒng)試飛任務(wù)的驗(yàn)證機(jī),同時(shí)也是日本新一代教練機(jī)的原型機(jī)。這實(shí)際上是一種很聰明的策略,進(jìn)可攻退可守。無論將來政治局勢(shì)對(duì)“心神”項(xiàng)目如何影響,日本都不會(huì)徹底荒廢掉這一項(xiàng)目的投資和技術(shù)成果。
在順利的情況下,“心神”樣機(jī)試飛完成后,會(huì)進(jìn)一步投入全尺寸戰(zhàn)斗機(jī)型的研制。事實(shí)上。這就是照抄F-35戰(zhàn)斗機(jī)的發(fā)展經(jīng)驗(yàn)——最早的X-35驗(yàn)證機(jī)噸位和尺寸都比今天的F-35小很多,而且同樣沒有內(nèi)置彈倉。如果我們僅以現(xiàn)在的樣機(jī)來評(píng)斷日本“心神”的未來水平,那么就和用X-35來評(píng)斷F-35的作戰(zhàn)性能沒有兩樣了。即使是項(xiàng)目發(fā)展不順,日本也會(huì)將現(xiàn)有的“心神”樣機(jī)稍加修改——比如去除矢量推力結(jié)構(gòu)后投入批量生產(chǎn),作為新一代高級(jí)教練機(jī)使用。
氣動(dòng)布局
日本在“心神”上采用常規(guī)布局設(shè)計(jì)和F-2戰(zhàn)斗機(jī)有很直接的關(guān)系。F-2戰(zhàn)斗機(jī)是三菱公司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合作研制的產(chǎn)品,實(shí)際上就是在美國提供F-16設(shè)計(jì)技術(shù)的支持下,日本半仿半研而成的放大改進(jìn)型號(hào)。在F-2的研制過程中,三菱公司掌握了常規(guī)布局三代機(jī)的關(guān)鍵設(shè)計(jì)技術(shù),比如邊條翼的渦流增升設(shè)計(jì)、電傳控制技術(shù),為今天的“心神”驗(yàn)證機(jī)奠定了基礎(chǔ)。
“心神”在氣動(dòng)布局的總體設(shè)計(jì)上接近F-22,但是在機(jī)翼與尾翼的核心設(shè)計(jì)上卻截然不同。F-22采用棱型平面機(jī)翼設(shè)計(jì),機(jī)翼的后緣帶有很大的前掠角度;這不僅使機(jī)翼獲得了更好的強(qiáng)度和剛度特性,而且機(jī)翼與機(jī)身的連接長度大大增加了,機(jī)翼受力能夠更多更均勻地分擔(dān)給機(jī)身。在機(jī)翼大幅加長以后,為了避免平尾向后超過噴管太多,引起重量的大幅度增加,設(shè)計(jì)人員將機(jī)翼的襟翼內(nèi)側(cè)切除了一個(gè)缺口,使平尾的前端正好切入進(jìn)來。
切入式平尾設(shè)計(jì)使F-22不僅避免了嚴(yán)重超重的窘境,而且緊湊的外形也為側(cè)向隱身和減低整體阻力帶來了非常優(yōu)越的性能改善。但這一設(shè)計(jì)也存在嚴(yán)重的弊端:經(jīng)過前機(jī)身和機(jī)翼的氣流對(duì)平尾的干擾特別嚴(yán)重,這使F-22在俯仰控制時(shí)的非線性問題特別嚴(yán)重,并引起了一連串的問題,包括墜機(jī)。后來F-22電傳飛控軟件經(jīng)歷過反復(fù)多次更新,與此關(guān)系極大。
俄羅斯T-50在機(jī)翼、平尾的設(shè)計(jì)上很大程度參照了F-22,其優(yōu)缺點(diǎn)都大體類似。所不同處在于,由于在氣動(dòng)研究和飛行控制領(lǐng)域上差距較大,俄羅斯人需要額外在進(jìn)氣道前沿設(shè)置可動(dòng)邊條,以便對(duì)渦流升力進(jìn)行主動(dòng)控制,從而有效削弱俯仰控制的非線性問題,保證飛行安全。
“心神”選擇梯形機(jī)翼,縮短了機(jī)翼根部的長度;這樣可以在飛機(jī)長度不增加的情況下,保證平尾與機(jī)翼之間不直接干涉。雖然這種設(shè)計(jì)是典型的三代機(jī)水平,而且對(duì)于機(jī)翼的結(jié)構(gòu)特性和整機(jī)壽命沒有什么貢獻(xiàn),但是大幅度減小了飛行控制上的風(fēng)險(xiǎn),應(yīng)該說是一種比較務(wù)實(shí)的做法。此外,在進(jìn)氣道設(shè)計(jì)上,日本此次公布的視頻中采用了模糊處理。此前“心神”全尺寸模型上采用的加萊特進(jìn)氣道已經(jīng)公開過,并無保密必要,因此本次樣機(jī)采用了DSI無附面層隔道設(shè)計(jì)的可能性很大。這種進(jìn)氣道現(xiàn)在已經(jīng)得到了廣泛使用,除了重量優(yōu)勢(shì)特別明顯外,在隱身上也優(yōu)于F-22和F/A-18E/F的加萊特進(jìn)氣道;雖然進(jìn)氣道上下邊沿與機(jī)身側(cè)面的夾角會(huì)形成反射特征點(diǎn),但這與加萊特那種附面層隔道形成的深腔效應(yīng)反射相比簡直不值一提。不過,日本現(xiàn)階段對(duì)DSI進(jìn)氣道的優(yōu)化能力到底如何,目前只能存疑。endprint
在氣動(dòng)布局的其他方面,“心神”做得較好:整體流線相當(dāng)簡潔、流暢自然,不僅在機(jī)身各平面的過渡上找不到處理不良的地方,而且在后機(jī)身的面積分布和收縮過渡上處理的也不錯(cuò)。與其相比,“鶻鷹”的尾撐在機(jī)翼下方形成帶有強(qiáng)反射特征的直角棱邊凸起,不僅后機(jī)身面積過大,還需要設(shè)置尾錐來減弱尾噴管之間的干擾阻力。
從整體設(shè)計(jì)上來評(píng)價(jià),“心神”現(xiàn)階段的氣動(dòng)布局設(shè)計(jì)是比較合理的;雖無驚才絕艷的亮點(diǎn),卻勝在沒有什么錯(cuò)誤。如果“心神”在放大以后還能保持這種水平的話,它將具備較大的性能潛力;只要設(shè)計(jì)方優(yōu)化到位,在RCS、阻力、升力性能上都能做出不錯(cuò)的表現(xiàn)。
飛控系統(tǒng)
從日本公布的采訪視頻來看,“心神”項(xiàng)目的論證過程中始終將超機(jī)動(dòng)能力放在一個(gè)很重要的位置,這無疑會(huì)對(duì)其飛行控制系統(tǒng)提出很高的要求。
對(duì)于飛行控制系統(tǒng)的動(dòng)力部分來說,飛機(jī)的大部分活動(dòng)部件,比如水平尾翼、襟副翼、方向舵這些都需要液壓系統(tǒng)來進(jìn)行驅(qū)動(dòng);液壓系統(tǒng)的功率越大,舵面偏轉(zhuǎn)的速度也就越快,飛機(jī)反應(yīng)便越敏捷,越適合超機(jī)動(dòng)飛行。比如F-22的液壓系統(tǒng)總功率達(dá)到560千瓦,是F-15的兩倍。而根據(jù)某國《2008—2009年航空科學(xué)技術(shù)學(xué)科發(fā)展報(bào)告》中公開的研究進(jìn)展和性能指標(biāo)進(jìn)行推測,“威龍”的液壓系統(tǒng)總功率應(yīng)該在600千瓦左右。
在功率指標(biāo)越來越高的情況下,為了減小液壓系統(tǒng)的體積和重量,對(duì)于第五代戰(zhàn)斗機(jī)來說,液壓系統(tǒng)的工作壓力從210千克/平方厘米提升到280千克/平方厘米已經(jīng)是通行的設(shè)計(jì)標(biāo)準(zhǔn),F(xiàn)-22、“威龍”、T-50的液壓系統(tǒng)都是采用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作為恒定工作壓力。日本作為傳統(tǒng)的液壓強(qiáng)國,泵、閥、密封件等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上一向技術(shù)先進(jìn),要做到這點(diǎn)不存在任何難度。
實(shí)際上,因?yàn)樵O(shè)計(jì)時(shí)間的差異,五代機(jī)的技術(shù)并不一定就全面比所有的三代機(jī)先進(jìn)。比如F/A-18E/F液壓系統(tǒng)采用的就是210~350千克/平方厘米的可變壓力工作體制,一般飛行情況下使用低壓,而進(jìn)行高機(jī)動(dòng)飛行時(shí)自動(dòng)轉(zhuǎn)換到最大壓力。“心神”的液壓系統(tǒng)是和目前五代機(jī)一樣采用28兆帕恒壓工作體制,還是采用35兆帕的智能變壓工作體制,還要等將來日方披露信息后才能知曉。
而對(duì)于負(fù)責(zé)信號(hào)傳輸處理的電傳部分來說,“心神”很有可能采用3~4余度數(shù)字電傳系統(tǒng),無模擬電傳備份。這基于兩個(gè)原因:首先,現(xiàn)代數(shù)字電傳系統(tǒng)的可靠性已經(jīng)非常高,保留額外的備份系統(tǒng)沒有必要。其次,采用先進(jìn)氣動(dòng)設(shè)計(jì)的現(xiàn)代戰(zhàn)斗機(jī)本身控制律就較為復(fù)雜,而且研制過程中反復(fù)修改調(diào)參更是無法避免的現(xiàn)象;要在軟、硬件修改無法分離的模擬電路中完成這些工作,技術(shù)難度非常高,無謂花費(fèi)的人力、時(shí)間、財(cái)力代價(jià)都太大。
“心神”樣機(jī)從一開始就具備矢量推力系統(tǒng),日本官方宣傳視頻中也刻意強(qiáng)調(diào)了超機(jī)動(dòng)飛行能力。通過這兩點(diǎn)分析,“心神”的電傳功能肯定會(huì)包括建立在飛行控制系統(tǒng)、發(fā)動(dòng)機(jī)控制系統(tǒng)交聯(lián)基礎(chǔ)上的過失速區(qū)域控制能力。考慮到某國目前受限于發(fā)動(dòng)機(jī)問題,“威龍”尚未使用矢量推力發(fā)動(dòng)機(jī),日本甚至有可能在一些關(guān)鍵技術(shù)上比該國更早開始試飛探索。
在F-22和JAS-39的時(shí)代,由于設(shè)計(jì)手段和設(shè)計(jì)人員的思維習(xí)慣、技能傳統(tǒng)所限,飛機(jī)控制律編寫都是在傳統(tǒng)的單回路設(shè)計(jì)方法上展開的。其設(shè)計(jì)難度大,而且效果越來越不能滿足先進(jìn)氣動(dòng)設(shè)計(jì)飛機(jī)進(jìn)行復(fù)雜機(jī)動(dòng)飛行的需要。日本在數(shù)學(xué)和自動(dòng)控制理論領(lǐng)域一向有非常高的水平,“心神”在控制律設(shè)計(jì)中應(yīng)用新的多變量控制理論,對(duì)飛控進(jìn)行系統(tǒng)化的多變量、多回路綜合處理將會(huì)是必然選擇。
但是,電傳飛控的特殊之處在于,控制律軟件其實(shí)本質(zhì)上就是設(shè)計(jì)單位將飛機(jī)氣動(dòng)設(shè)計(jì)以數(shù)學(xué)形式展現(xiàn)出來,即所謂的飛控氣動(dòng)一體。但是,現(xiàn)階段氣動(dòng)水平研究仍然非常有限,對(duì)于過于復(fù)雜的流場(比如過失速下機(jī)翼氣流分離后的狀態(tài))無法進(jìn)行模擬計(jì)算,這一方面只能依靠風(fēng)洞試驗(yàn)和實(shí)際試飛的反復(fù)經(jīng)驗(yàn)積累來指導(dǎo)氣動(dòng)、飛控的設(shè)計(jì)修改。因此,就算在先進(jìn)設(shè)計(jì)方法、工具上日本并不欠缺,甚至在具體性能比“猛龍”等新型先進(jìn)戰(zhàn)斗機(jī)所應(yīng)用的還要好一些,最終控制律的設(shè)計(jì)水平高低,依然極大地取決于研制單位的經(jīng)驗(yàn)積累程度。在這一方面,日本的三菱公司要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某國的相關(guān)研究所。
總的來說,“心神”飛行控制系統(tǒng)的硬件系統(tǒng)和指導(dǎo)理論、設(shè)計(jì)工具都將會(huì)是相當(dāng)先進(jìn)完善的,但具體的性能仍然要以實(shí)際試飛為準(zhǔn)。而且對(duì)于日本來說,要將“心神”的飛行控制發(fā)展到他們預(yù)期的完善程度,將是一個(gè)非常漫長而艱巨的任務(wù)。
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
日本在現(xiàn)代戰(zhàn)斗機(jī)結(jié)構(gòu)制造上一直擁有著非常高的水平。比如在重型三代機(jī)的生產(chǎn)能力突破上,日本生產(chǎn)F-15J/DJ就要遠(yuǎn)遠(yuǎn)早于某國的“側(cè)衛(wèi)”系列。在這個(gè)過程中,日本掌握了非常強(qiáng)的鈦合金加工能力。
作為冷戰(zhàn)時(shí)期美軍在越戰(zhàn)遭受巨大損失后不惜血本搞出來的主力制空機(jī)型,F(xiàn)-15在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上很少考慮成本問題。在F-15機(jī)體材料中,鈦合金比例達(dá)到26.5%,而且這些關(guān)鍵的承力部件往往制造難度非常大。比如F-15機(jī)身承力隔框就是用6AL-4V鈦合金在3.5萬噸鍛壓機(jī)上鍛造的,寬度達(dá)到3.05米。在其中心腹板的厚度只有1.5毫米的情況下,腹板兩側(cè)筋條厚度1.3~2毫米,高度卻達(dá)到64毫米。腹板兩面的凹槽共計(jì)42個(gè)。然而,形狀如此復(fù)雜的承力構(gòu)件,精加工余量卻只有2.3毫米,加工難度之大遠(yuǎn)非蘇-27可比。
然而,F(xiàn)-15J/DJ畢竟只是美國授權(quán)日本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對(duì)于提升日本的自主設(shè)計(jì)能力幫助不大,這種局面在F-2戰(zhàn)斗機(jī)研制時(shí)得到了改觀。二戰(zhàn)以后,日本航空并未像德國一樣一蹶不振,而是迅速復(fù)蘇并自行研制了多款軍用飛機(jī)。有了這些設(shè)計(jì)經(jīng)驗(yàn)作為基礎(chǔ),日本在F-2研制過程中很快就吃透了F-16的相關(guān)設(shè)計(jì)規(guī)范,不僅掌握了傳統(tǒng)金屬材料結(jié)構(gòu)的損傷容限設(shè)計(jì)等三代機(jī)結(jié)構(gòu)技術(shù),而且還利用自身全球領(lǐng)先的化纖水平優(yōu)勢(shì),為F-2更換了復(fù)合材料機(jī)翼。
雖然此后日本一直沒有開發(fā)過新的戰(zhàn)術(shù)飛機(jī),但是在航空復(fù)合材料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制造上,其積累經(jīng)驗(yàn)、探索先進(jìn)設(shè)計(jì)理論的腳步卻從未停止過。日本擁有世界上最頂級(jí)的高性能纖維和基體材料提供商,他們?cè)谂c各大航空企業(yè)合作的過程中既是原料提供者,又是復(fù)合材料結(jié)構(gòu)的代工制造者,也是相關(guān)設(shè)計(jì)研發(fā)的參與者,同時(shí)更是復(fù)合材料結(jié)構(gòu)出現(xiàn)失效后的反饋信息接受者。在飛機(jī)的復(fù)合材料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制造領(lǐng)域,日本有著極強(qiáng)的技術(shù)能力。endprint
這些能力現(xiàn)階段并未直觀地體現(xiàn)在“心神”驗(yàn)證機(jī)上。根據(jù)日本公布的視頻來看,這架驗(yàn)證機(jī)為了降低成本,幾乎沒有使用復(fù)合材料結(jié)構(gòu),絕大部分結(jié)構(gòu)都是鋁合金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心神”能繼續(xù)發(fā)展去下,它在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制造方面不會(huì)遇見大的難題。
發(fā)動(dòng)機(jī)選擇
“心神”在發(fā)動(dòng)機(jī)上最為引人矚目的外形特征,就是采用折流板結(jié)構(gòu)的矢量推力控制系統(tǒng)。這種系統(tǒng)由于結(jié)構(gòu)簡單可靠,易于實(shí)現(xiàn),以往也常用在驗(yàn)證機(jī)上,比如著名的X-31驗(yàn)證機(jī)。但對(duì)于裝備型號(hào)來說,折流板對(duì)于發(fā)動(dòng)機(jī)的推力損失太大,自身形成的超音速干擾阻力又太高,極不適合于超音速飛行,因此從未實(shí)用過。
基于正常的技術(shù)規(guī)律來說,筆者可以肯定在未來的更為成熟的“心神”上,其矢量推力結(jié)構(gòu)必然要更換為類似蘇-30MKI的軸對(duì)稱偏轉(zhuǎn)噴管,或者類似F-22的二元噴管設(shè)計(jì)。然而問題的關(guān)鍵也在這里,“心神”在發(fā)動(dòng)機(jī)上究竟有多大的選擇余地?
“心神”現(xiàn)階段使用的是全重644千克的小型渦扇發(fā)動(dòng)機(jī)。根據(jù)日本公布的結(jié)構(gòu)示意圖,以及日本發(fā)動(dòng)機(jī)引進(jìn)歷史來看,其基本設(shè)計(jì)應(yīng)該是源于英、法聯(lián)合研制的阿杜爾發(fā)動(dòng)機(jī)。通過改善結(jié)構(gòu),比如增加風(fēng)扇和壓氣機(jī)的級(jí)數(shù);使用先進(jìn)的材料減重,并達(dá)到極高的1900K渦輪前溫度,“心神”發(fā)動(dòng)機(jī)的最大推力從不到3.5噸增加到了5噸。可以肯定的是,這臺(tái)小發(fā)動(dòng)機(jī)受基本結(jié)構(gòu)和尺寸所限,不可能再有大幅度的推力增加。
然而,10噸的最大推力絕不可能承擔(dān)起一款真正五代機(jī)的動(dòng)力要求。對(duì)于“心神”的未來發(fā)展來說,目前看起來有一定可行性的唯一途徑,就是在F-2戰(zhàn)斗機(jī)所采用的通用電氣F110-GE-19發(fā)動(dòng)機(jī)基礎(chǔ)上進(jìn)行仿制改進(jìn),增加矢量推力結(jié)構(gòu)。這款發(fā)動(dòng)機(jī)日本不僅使用維護(hù)經(jīng)驗(yàn)豐富,而且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生產(chǎn)組裝能力。如果這一假設(shè)成真,在具體的矢量推力結(jié)構(gòu)選擇上,雖不能確定日本人的觀點(diǎn)如何,但至少他們制造具備實(shí)用水平的兩元噴管應(yīng)該不成問題。根據(jù)俄羅斯中央空氣動(dòng)力流體研究院撰寫的《超音速飛機(jī)空氣動(dòng)力學(xué)和飛行力學(xué)》所述,蘇聯(lián)早年在矢量推力的選擇上更傾向于兩元噴管,因?yàn)閲姽芎秃髾C(jī)身一體化設(shè)計(jì)帶來的高速減阻效果十分優(yōu)越。但是,在關(guān)鍵的耐熱陶瓷材料上蘇聯(lián)始終無法突破,體積太大、重量超重?cái)?shù)百千克以至于毫無使用價(jià)值。
不過,當(dāng)“心神”達(dá)到這種高度時(shí),必然會(huì)對(duì)美國F-35形成非常嚴(yán)重的沖擊。即使日本不對(duì)外銷售“心神”,僅僅是F-35對(duì)日銷量的萎縮,也會(huì)對(duì)美國造成嚴(yán)重的經(jīng)濟(jì)損失和干預(yù)能力下降。已有的事實(shí)證明,美國在這方面是非常敏感的。比如挪威在F-35與JAS-39改進(jìn)型號(hào)猶豫的過程中,美國就通過停止向瑞典提供相關(guān)雷達(dá)部件的措施來破壞瑞典和挪威的交易。也難怪很多人認(rèn)為,“心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款政治型號(hào),只是向外宣示日本軍事發(fā)展決心和實(shí)力,而且又能在美日軍貿(mào)中為自己添加重量的一個(gè)砝碼。
當(dāng)“心神”從現(xiàn)在的驗(yàn)證樣機(jī)發(fā)展成完全體的中型甚至重型五代機(jī)時(shí),它的性能將會(huì)達(dá)到怎樣的程度?美國會(huì)支持日本發(fā)展到哪一步,最后能否容忍定型的“心神”戰(zhàn)斗機(jī)出現(xiàn),沖擊F-35的對(duì)日銷售?目前披露出來的信息仍然太少,我們只能在保持警惕的同時(shí),靜觀后續(xù)發(fā)展。
(編輯/一翔)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