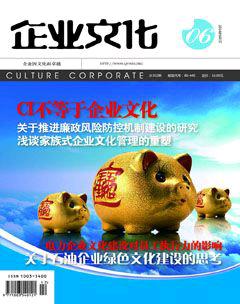論公司自治與國家強制的立法選擇
摘 要:公司作為私法主體,在其對內的治理及對外的營業中應當貫徹和秉承意思自治的理念;同時,公司作為一種特殊的私法主體,由于其人合性與資合性,其內部的組織結構和對外的行為又應受到國家強制性的立法規制。
關鍵詞:公司自治;公司章程;國家強制
引論:“公司”這一概念的外沿十分廣泛,公司法意義上的公司,有獨立的法律擬制人格,具有私法主體屬性。因此,民法領域的意思自治同樣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但是,公司與一般的民事主體不同,并不是簡單單一的私法主體,其具有人合性與資合性的特殊性質,對于前者,公司在運行中需要調整各個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對于后者,公司也應對其資本有相應的保障,承擔著相應的社會責任。
一、公司章程與公司自治——從“章程之爭”第一案談起
公司章程,指記載上述基本規則的書面文件。[1]公司章程自治也由此成為私法領域意思自治原則在公司法上的集中體現,其具體可以解釋為如下內涵:
第一、公司發起人有著訂立公司章程的自由,有著選擇與哪些對象一起訂立章程的自由;
第二、公司成立后,股東大會享有根據公司經營環境的變化適時修改公司章程的自由;
第三、股東有權決定公司章程的內容,通過章程規定公司的組織機構及經營活動的相關事項,如公司經營范圍、組織機構、解散事由等。
1998年發生的我國證券市場“章程之爭”第一案——大港油田收購愛使案,引發了理論屆關于公司自治與國家強制之間的沖突與選擇的爭論。 1998年,大港油田集團公司下屬天津煉達集團有限公司、天津大港油田重油公司和天津市大港油田港聯石油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對上海愛使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收購過程中,愛使公司通過修改公司章程提高了反收購能力,后由于其修改的內容違反《公司法》相關規定,被證監會確認違法,三家公司獲得了與其所持有的股份相應的權利。對此,有學者提出,公司章程的自治性是相對的,無論是制定或者修改公司章程,都不得違反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與國家強制性法律規范相沖突的部分均為無效。公司章程不行剝奪或者變相剝奪股東固有權利,應為股東實現其權利提供保障。2005年《公司法》修訂后,公司自治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法律上的授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公司自治的限制應當取消或弱化。對公司章程自治加以限制是為了維護公司制度的公平正義,權衡股東之間、股東與高管之間、股東高管與員工之間的利益沖突,促使公司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二、公司章程自治的擴張與異化
2005年《公司法》的修訂徹底改變了我國以往管制為主自治為輔的立法理念,極大的增加了對于公司自治的授權性規定,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1、授權章程記載任意事項,優先于公司法的任意性規范而適用,經典表述為“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
2、授權章程在法律授權性規范的框架下記載相對必要事項,以填補大量授權性空白規定,此類條款的經典表述就是“除本法另有規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規定”。
3、明確規定章程是判斷當事人行為的效力與責任的依據,此類條款的經典表述為“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應當……”[2]
在《公司法》修訂后,公司章程的作用得到的彰顯,公司發起人、股東可以在綜合考量外部市場、公司內部結構等方面之后,自由訂立和修改章程,公司章程自治的外延極大擴張。
就目前而言,公司章程自治的異化條款大概有如下幾類:
對于章程的異化條款,雖然經過了股東大會的表決,具有其程序的法定性,但是這類章程的條款與公司章程自治的價值內涵沖突,與《公司法》的立法理念相背離,而且,這一類章程條款的受眾,也就是權利受到侵害的個體或群體,其固有權利受到了侵害。因此,這一類章程條款不應當得到法律上的確認。前文敘述的“章程之爭”第一案雖然發生在《公司法》修訂之前,但該案中的法律問題到今天一直存在。公司自治應當保護,2005年《公司法》的修訂的確是立法的進步而非倒退,但是,在放開對于公司自治束縛的同時,公司自治的界限應當明確,國家強制的介入也應同時適用。
三、公司章程自治與國家強制
《公司法》兼具公法與私法的雙重屬性,這即體現在公司章程的制訂、修改中的國家強行法限制和自由選擇權利之上。對于國家強制與公司章程自治之間的邊界,有學者將其劃分為基本邊界、價值邊界。[3]
國家強制對于公司章程自治的限制通過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予以作用,同時國家強制在司法實踐中也考慮公序良俗與公共利益。公司章程不得以任何借口否定或規避法律強制性規定和公序良俗對其的適用,即使該章程是股東意志的體現。[4]這是公司章程自治與國家強制之間的基本邊界;同時,國家強制反映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的規制,其著眼點在于正常安全的經濟秩序利益以及宏觀上公司整體的運作效率,而公司章程自治則體現了國家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其著眼點在于個人自由價值以及微觀上公司個體的運作效率,國家強制與章程自治的價值邊界,即是公平與效率、個人自由與社會公益這兩組價值之間的平衡點。
因此,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公司章程自治與國家強制之間勢必要進行相應的選擇,在有的條款中可以達到平衡,但有的條款中必然需要有所側重甚至摒棄。
四、公司章程自治與國家強制的立法選擇及完善建議
美國學者愛森伯格在《公司法的結構》中完整闡述了公司章程自治與國家強制之間立法傾向及選擇的規則體系。
在閉鎖公司,由于公司章程中的規則就通常由制定者討論得出,因此應當允許股東自己決定其自治規則,這取決于其股東范圍的局限性。因此,其章程中所有權與控制權之間的委托代理權限及資產盈利的分配就應當以賦權型規則和補充型規則為主,而關于高管人員的信義義務及中小股東的權利保護應當以強制性規則為主。
而在公開公司,由于股東人數眾多,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股東和管理層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因此,與閉鎖公司不同,關于股東與高管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公司的組織機構及公公司信息披露、中小股東權利保護等內容均應采強制性規則,而僅有利潤分配等規則一般為賦權性規則。[5]
筆者認為,愛森博格對于公開公司與閉鎖公司區分立法選擇方向的劃分應屬允當,我國現行《公司法》也采用了一種方式。如前文所述關于授權章程記載任意事項,優先于公司法的任意性規范而適用的條款。
由此,我們可以總結出,我國《公司法》在公司自治與國家強制的立法選擇上應區分對待,對此,我國《公司法》已經涵蓋了這一思想,應在進一步的立法或修訂中予以秉承:
1、有限責任公司、不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自治范圍應廣于上市的股份公司;
2、公司章程中的內部事項自治程度應大于外部事項;
3、公司章程上的普通事項自治程度大于基本事項;
4、公司章程訂閱的自由大于公司章程修改的自由。[6]
但是,就目前立法而言,實踐中章程自治的異化仍然存在,大股東濫權侵害中小股東或特定少數股東利益,大股東修改章程限制公司外部治理或規避企業社會責任。因此,在我國進一步的立法中,應當對相關內容有所規制:
1、章程修改不得刪除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2、非經股東同意,章程修改不得給少數股東課以新義務,對此,個別國家、地區的公司法有明確的規定,而我國公司法沒有明確規定;
3、非經股東同意,章程修改不得變更該股東的既得權益,此項規定在我國公司法尚屬空白。
4、非經其他股東同意,章程修改不得給部分股東設定新權利。 [4]
5、規制大股東通過修改章程限制公司外部治理,減少內部人控制之可能性。
6、禁止股東通過修改章程規避企業社會責任。
結論:誠然,作為私法主體的公司,章程自治理應在其日常運行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公司存在,利益沖突即存在,僅僅依靠公司章程自治必然會導致章程自治的異化,從而導致利益沖突一方不法獲利,而另一方利益受損。國家強制的作用此時得到彰顯,其所追求的就是公司內部及公司與第三人,公司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平衡。不過,公司的本質是營利的,過分限制股東對利益的追逐,或者對公司苛以過多的社會責任也并不妥當。對于公司而言,國家強制僅僅是輔助作用,具有其適用的最后性,但卻維護著公司諸方面利益沖突的底線。而且,法律的進步總是謹慎的,立法的進步永遠無法涵蓋實踐中產生的新變化。就公司法領域而言,由于其兼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對于其立法的空白地帶,無法適用公法領域的“法無明文規定即禁止”,而適用私法領域的“法無明文規定即允許”亦非允當。因此,對于相關糾紛的處理,需要綜合考量公司利益、股東利益、債權人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等諸多利益關系,而非僅僅考慮公司章程自治或法律強制性的規定。
注釋:
[1]李建偉 《公司法學》第二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第101頁
[2]李建偉 《公司法學》第二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年版 第105至106頁
[3]參見管人慶 《論公司章程自治的邊界》 載于《法學論從》2009年5月,第68頁
[4]徐燕 《公司法原理》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5]【美】M.V.愛森博格著,張開平譯 《公司法的結構》 王保樹主編 商事法論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第390-442頁
[6]郭奕 論公司章程自治的界限 載于浙江社會科學 2008年第4期 第53頁
[7]參見李建偉 《公司法學》(第二版) 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年版 第108頁
參考文獻:
[1]【美】M.V.愛森博格著,張開平譯 《公司法的結構》 王保樹主編 商事法論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郭奕 論公司章程自治的界限 載于浙江社會科學 2008年第4期 第53頁
作者簡介:孫躍(1990-),男,天津市人,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學士,北京化工大學民商法碩士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