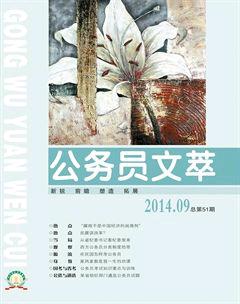“腐敗不是中國經濟的潤滑劑”
張翃
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經濟與腐敗問題的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魏德安認為,腐敗與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不是因果關系而是轉折關系;腐敗與既得利益集團緊密相聯,要推進改革必須反腐。
從“蒼蠅”到“老虎”,反腐在中國當前的公共話題中幾乎成為了主旋律。這場轟轟烈烈的反腐行動,將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腐敗和反腐敗,給中國帶來哪些啟示?中國反腐之戰行動的方向何在?財新記者日前采訪了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魏德安( Andrew Wedeman)。
魏德安教授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經濟與腐敗問題,著有《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從毛澤東到市場:中國的尋租、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化》等書。
魏德安認為,腐敗和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不是因果關系,而是轉折關系。如果說“發展型腐敗”曾在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的經濟起飛期,起到過某種助推作用——并為此付出巨大代價,中國的腐敗發展到今天,已成為“掠奪性”的,于經濟增長無益。并且,腐敗與既得利益集團緊密相聯,要推進改革,必須反腐。
魏德安說,比起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反腐是動真格的。中國的反腐能力也越來越系統化和講求方法。但政治體制、行政體系的特征都為中國反腐提出了重大挑戰。這既需要當代領導人的智慧,更需要未來幾代人的持續努力和完善。
“一兩次反腐行動不可能根除腐敗,任何政治體系都不能絕緣。”魏德安說,既要“抓腐敗”,也要“威懾腐敗”,將腐敗的念頭扼殺于搖籃。魏德安認為,對于反腐,中國需要有些耐心。這意味著,中國不僅需要致力于修建規則與法律,更需要培養出廉潔的文化。反腐必然是持久戰。
“發展型腐敗”與“掠奪型腐敗”
財新記者:你的書中提出一個概念“發展型腐敗”(developmental corruption)日本、韓國、臺灣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發展型國家”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發展型腐敗”幾乎是“發展型國家”的一個難以分離的組成部分。你認為中國今天腐敗的特點則是“掠奪型腐敗”(predatory corruption)。這兩者有何關鍵不同?
魏德安: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經濟增長的基礎都建立在政治穩定上。這三個經濟體在開始經濟發展的初期,都面臨著一個高度四分五裂的不穩定政治體系。政治領導人要從經濟中榨取金錢、經濟機會和資本,用來收買保守右翼的忠誠。三個政權都是通過這種方法獲得穩定。
中國不是這樣。中國共產黨能夠保持政治穩定,不需要通過上述那種腐敗方式。中國當前的腐敗,是更常見的那種腐敗類型,也就是官員利用權力中飽私囊。
財新記者:你的觀點是“發展型腐敗”比較可以接受,而“掠奪型腐敗”比較不能接受?
魏德安:我可不想被引用說“發展型腐敗是好事”。“發展型腐敗”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是不得不接受的,那就是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就會出現政治動蕩,以及由此導致的低經濟增長。日本、韓國和臺灣的經濟都為“發展型腐敗”付出了代價。
在一個完美的世界里,沒有腐敗是最好的,但現實是所有體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害于腐敗。所以,問題在于怎樣去最小化腐敗造成的傷害。這也是中國目前要面臨的挑戰,因為誰也不可能全面根除腐敗,但是怎樣才能遏制腐敗?對于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來說,這是一個關鍵問題。
財新記者: 日本、韓國和中國的臺灣地區是否找到控制它們的“發展型腐敗”的方法?
魏德安:“發展型腐敗”時期在臺灣、韓國已經過去了。臺灣和韓國現在的腐敗,更多還是那種典型的“掠奪型腐敗”。每個政治體系都會有這種腐敗,問題只在程度的不同,還有政治領導人處理這些腐敗個例的意愿的不同。
日本則不能說渡過了“發展型腐敗”的階段,悲哀的是,至今它還無法擺脫派系庇護主義的“操縱政治”,以及與之相連的腐敗。日本20多年來經濟增長停滯,就是因為還在繼續受害于自民黨和強大的經濟利益集團之間過于緊密聯系的后遺癥。
財新記者:日本未能脫離“發展型腐敗”,后果是什么?
魏德安:日本經濟花了20多年還沒有抬頭,沒能推動那些結構性改革——今天安倍要推行的經濟結構性改革有很多是已經說了20多年的了。正是因為這種腐敗削弱了政治的力量,削弱了政治領導人引領經濟發展方向的能力。
我們總以為腐敗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但是其實它也可以是很不易察覺的。它可能導致的結果是政治的軟弱和政策的無能,正如日本。
財新記者:那么韓國呢?韓國的腐敗曾經如此嚴重,前總統盧武鉉的自殺也與其卷入家族腐敗的政治丑聞漩渦有關。在你看來,韓國做了哪些事情來克服腐敗的問題?
魏德安:韓國在上世紀80年代對銀行進行了私有化。在此之前,總統基本上控制了銀行的信貸。如果你想要銀行貸款來支持你的企業發展,那你就得支持執政黨。同時,到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時,韓國的市場經濟也更為成熟,特別是在成功融入全球經濟之后,以前那種政商關系就發生了改變。
今天,韓國也還是有腐敗,臺灣也還是有腐敗。雖然韓國和臺灣已經過了以前那種“發展型腐敗”的階段,但其實是由一種主導的腐敗形式轉移到另一種主導的腐敗形式。
財新記者:當前中國領導人也非常強調市場經濟改革。這和反腐之間是怎樣的關系?
魏德安:改革與反腐二者是相輔相成的。腐敗就是官員可以利用手中權力從經濟中榨取金錢。經濟受自由裁量權力的影響越大,腐敗的機會就越多。我們也要認識到,現有體系中形成了許多既得利益,很多也是腐敗的受益者。所以要打破這些既得利益,必須反腐。
美國經驗:行政專業化+培養廉潔文化
財新記者:有很多人將今天的中國與美國1880年—1920年的“進步時代”相比。你認為二者有相似嗎?
魏德安:是的。很粗線條地說,到了19世紀晚期,美國已經有了一個相當現代的、較為發達的政治體系。但是美國的行政體系還是受到了被權力拉著跑的缺陷的掣肘。19世紀的時候,只要換了一個黨執政,那行政部門幾乎得全體被解雇,換成自己黨內的人。但是當你需要發展一個現代的科層制和技術官僚的時候,你不能就這樣一下子炒掉所有專家。所以,美國開始建立一個職業性的行政部門,將行政部門和政治上層建筑區隔開來。
中國要做的就是建立起一個專業化的行政部門。老實說,這是需要時間的。需要時間來想清楚,要怎樣的監管體系,才能限制住官員濫用手中權力的可能性。很多事情是很瑣碎的,如建立預算、審計制度,建立起規則和監管來確保官員不能一手遮天,權力分散于不同主體。
美國創造專業化的公共行政體系,是從19世紀70年代到甚至可以說20世紀60年代,才真正完成了這個過程,歷時將近一個世紀。
不能失去耐心,以為只要創造出一些規矩和法規,就能把腐敗控制住。要控制住腐敗是得有規則和法規,但是更需要的是發展出一種腐敗可恥的文化,這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中國是在往正確的方向上走。
中國必須像現在這樣通過大規模的反腐行動來排除腐敗官員、震懾那些想要腐敗的官員,與此同時,也必須改造國家的官僚體系、行政體系和政治文化。這樣的過程往往緩慢,不乏挫折,但不能失去耐心。
財新記者:你認為,中國有條件完成美國所做到的這種行政體系的改良嗎?
魏德安:如果你看美國今天的情況,共和黨緊盯著奧巴馬政府是不是做錯了什么事。中國沒有這樣的結構。但是就不可能反腐嗎?我認為不是。看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也可以說是一個一黨制的國家。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成立廉政公署的時候,還只是一個殖民地。不是不可能,只是挑戰更大。
抓腐敗不如威懾腐敗
財新記者:你的書寫于2012年中國新領導班子上臺以前。你看中國這一輪的反腐,和你以前的研究有何不同?
魏德安:是的,我的書寫于2011年左右。2012年底中國宣布這個反腐行動的時候,我本來沒有太高期待,但現在看來,這是中國自1978年以來歷時最長的一次反腐行動,而且不斷地在查高層官員,強度很高。從系統性上說,此次的反腐行動也都比以前更為突出。
財新記者:此次反腐也反到了軍隊,這是否也是前所未見的?
魏德安:多年來關于軍隊腐敗的報道、跡象或起訴案件都很少。所以,新的中國領導班子大力在軍隊高層進行反腐,這也是一個不同于以往的事情。這種決心終結腐敗的信號是很重要的。
財新記者:你的書中也寫到,比起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對于反腐是比較認真的。這個區別很明顯嗎?
魏德安: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區別。每當中國有高官被調查或被限制行動,很多人都說,看,腐敗有多嚴重。但在很多發展中國家,腐敗只是在人們的傳言中,沒什么人真的受到查處。在中國,不僅人們傳言腐敗的存在,而且有大量腐敗官員正在被查處。
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很少會起訴腐敗官員,只是出于政治原因才起訴。而在中國,我們看到,每一天,各個層級的官員都可能受到查處。這就把中國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反腐區別開來。
財新記者:和你當時做研究的時候比,你如何評估中國當前的反腐能力?
魏德安:變化一直都有。跟幾年前相比,投入了更多的人力,反腐努力加強。自從上世紀80年代腐敗現象出現,中國開始改革公檢法體系和紀委系統。中國的執法和檢察體系里還有很多不足,但是我想每年中國都在嘗試改善這些體系。不過當你們改善這些體系的時候,腐敗者也在嘗試更好地掩蓋自己的行為。這是場賽跑,我的感覺是,中國的反腐能力在這場比賽中至少沒有落后。
財新記者:如你所說,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反腐運動是政治驅動的,缺乏堅實的制度性基礎,你是否擔心中國的反腐也出現這種情況?
魏德安:中國今天的反腐并不是政治驅動的。這場反腐行動包含了更大范圍內的努力。到2012年,所有人都已經逐漸認識到,腐敗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必須要有所作為。
財新記者:反腐應該怎樣更制度化?
魏德安:如果說反腐要轉到一個更加制度驅動的過程,比如加強檢察院、國家審計署、軍委紀委等的作用,這會是好事。我想比起“抓腐敗”更重要的是“威懾腐敗”,既要懲治腐敗,又要防治腐敗,要讓腐敗越來越難掩藏,越來越不能腐、不敢腐。
目前在中國,人們還是在大量使用現金,紅包或購物卡可以送來送去,這就產生了很多難以追蹤的現金流。在現金使用相對較少的社會,這個問題就會小得多。當然,更重要的是還是官員財產公開。
(摘自《財新 新世紀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