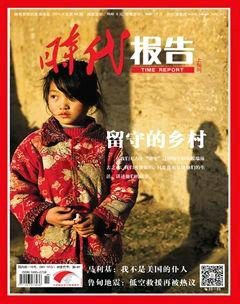芯片上的千軍萬馬
山旭+吳旭+杜尚華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是數千年來中國軍人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在現代信息技術環境下,即使使用“田忌賽馬”的戰術,也需要根據馬匹、騎手和賽道等等因素,先期進行充分的計算和模擬。
作為解放軍最新推出的全軍級別重大典型,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軍事運籌研究中心自上世紀80年代建立至今,“30多年來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利用技術探究現代戰爭的制勝機理。”
從1983年的一臺電腦、一個人,至今,這個數十人規模的團隊正在追求與智能指揮相關的先進技術。
他們還要在技術中融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獨有特點,比如政治工作對軍隊的影響,從而使作戰實驗系統更加真實、全面。
三十而立,這樣一個特殊的機構,是中國軍隊信息化建設歷程的一個縮影。
不見戰機、火炮、坦克,揮灑于鍵盤和硅片上的汗水、心血,同樣是為了一個目標:科學地打仗。
陸軍第47集團軍某旅參謀長張道寧中校,在2001年第一次見識了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軍事運籌研究中心的成果。這也是他所說的,該中心給他的部隊帶來的“三次訓練轉變”的第一次。
彼時,他還是一名年輕參謀,剛剛從大比武中獲勝歸來。休息未定,就被告知要與其他骨干參謀參加“陸軍參謀作業系統”培訓。這是一款由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運籌研究中心開發的解放軍第一個參謀工作軟件系統。
“那是我們部隊第一個列裝的軟件,電腦能夠替代參謀本人嗎?聞所未聞。”張道寧等人充滿懷疑,要求與該系統比武。
如今這已是常識,手工作業怎么可能與自動化對抗?
第二次是2002年,張道寧的部隊與另一個旅對抗。演習結束時,雙方首長為了裁決結果爭論得面紅耳赤,更是對導調組提出了意見。
當時正好有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軍事運籌研究中心的人員在場,“據他們說這個東西可以用計算機裁決,立刻在現場組成了科研小組。”張道寧回憶道,其后這個小組到他的部隊調研過上百次,終于研發出了解放軍第一個部隊演習評估系統。“那天演示,態勢回放、戰損情況一覽無余,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三次是2013年,張道寧所在的旅與另一個骨干部隊進行實兵對抗。
他們在演習前提出了多種戰法,但是苦于無法判斷實際效果。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軍事運籌研究中心為他們提供了合同戰斗實驗系統,“就是一種作戰實驗系統,可以進行模擬兵力推演、戰法推演,我們通過推演結果再修改作戰方案。”
對抗中,張道寧的部隊輕松擊敗對方。“后來總結,對方旅長覺得我們的戰法、風格發生了很大變化,認為我們提前拿到了他們的作戰方案。”得知真正原因后,對方恍然大悟。
距現代軍事運籌學誕生至今正好100年。1915年,英國工程師F.W.蘭徹斯特在《戰斗中的飛機》一文中首先提出,可以用常微分方程組的方式描述雙方兵力消耗的過程,這就是著名的“蘭徹斯特方程”。
不過直到二戰末期,“蘭徹斯特方程”才被軍事決策者所關注。那時J.H.恩格爾以琉璜島戰役的數據為基礎和系數,完善了“蘭徹斯特方程”。結果它的運行結果與作戰中的實際兵力變化吻合。
此后,恩格爾用歷史上的著名戰役不斷印證“蘭徹斯特方程”的可行性,后者也逐漸完善,摻雜進更復雜的要素、系數和理論。
不過,在一戰中一系列利用數學提升作戰能力的嘗試中,生理學教授A.V.希爾建立的英國國防部作戰研究部,在配置雷達和提升高射炮效率方面取得了參與實戰的成果,它是最早的現代軍事運籌組織。
二戰中,盟國大多成立了軍事運籌組織。比如美國專門成立了提升反潛作戰效果的機構,用計算得到擊沉潛艇的最佳戰術。
最終,到上世紀60年代,計算機的應用不僅使“蘭徹斯特方程”更為復雜和完善,也使作戰模擬仿真替代數學模型,成為現代軍事運籌學的主流。
“上世紀70年代,計算機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軍事變革,計算機技術和武器平臺有機結合,使硅片制勝的時代到來。”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政委張華偉少將說。
而在解放軍,最早的軍事運籌實踐一般被認為是上世紀50年代對炮兵火力計劃的研究。錢學森歸國后,根據對西方嘗試的了解,在他主導的國防部五院成立了第一個軍事運籌研究機構——作戰研究處。
《錢學森傳》等資料中顯示,上世紀70年代后期,錢學森正式提出了軍事運籌學和系統工程對于解放軍發展的重要性。
他在著名的“戰爭是一門科學”的闡述中這樣說:“在軍事科學,基礎理論層次是軍事學,技術理論層次是軍事運籌學,應用技術層次是軍事系統工程。”
1979年7月,錢學森應邀在總部機關領導同志學習會上作了長篇講演,把計算機作戰模擬技術推薦給解放軍。
他說:“戰術模擬技術,實質上提供了一個‘作戰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里,利用模擬的作戰環境,可以進行策略和計劃的實驗,可以檢驗策略和計劃的缺陷,可以預測策略和計劃的效果,可以評估武器系統的效能,可以啟發新的作戰思想。”
同時,“在模擬的可控制的作戰條件下進行作戰實驗,能夠對有關兵力與武器裝備使用之間的復雜關系獲得數量上的深刻了解。作戰實驗,是軍事科學研究方法劃時代的革新。”
這篇講演,成為中國軍事科學領域一個超前性的預告。軍委領導很快拍板,在軍事科學院成立了軍事運籌研究機構,錢學森本人親自領導的中科院力學所也參與了相關研究。
在高層布局之外,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軍事運籌研究中心,成為這種超前理念的自發實踐者。
1983年,蘭州軍區技術人員馬開城調到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領導問我能干什么,我說搞軟件開發。領導說怎么搞開發,我說得有電腦。”他回憶說。
不得不佩服當時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領導的遠見。很快,一臺耗資13萬元的電腦買了進來,這在當時相當于200個團職干部一年的工資。endprint
用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的第一臺電腦,馬開城和先后到來的同事們陸續研發出來了微機輔助裁決系統、合同戰術訓練模擬系統..
所有這些,都是解放軍信息化和軍事運籌科學的第一次。而輔助決策系統,已經帶有錢學森的理想色彩,它也是解放軍第一個可以指揮多個軍兵種的科學運籌系統。
“像輔助決策系統,里面的主要內容,今天仍是研究熱點。”該中心作戰模擬仿真教研室教授劉非平告訴記者。
劉非平是馬開城的第一個專業同事。到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前,他是野戰部隊的宣傳干事。如今,他已經是這里最資深的研究人員之一。
至于馬開城本人,之前一直從事技術工作,在軍事上是個“門外漢”,剛開始時連許多軍隊標號都不認識,觀摩演習更是看不出“門道”。
他找軍事指揮專業的專家教自己,甚至在49歲已帶博士生的情況下,又攻讀了作戰指揮學博士學位。
三年后,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配發了一批電腦,馬開城的專業伙伴隊伍壯大了起來。到上世紀90年代,他一直作為科技教研室下屬一個小組的團隊,也正式成立了一個教研室,而且有了14個人的規模。
在從1983年至今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軍事運籌研究中心的一系列成果中,主要分為指揮訓練、作戰指揮、作戰實驗幾個方面。而作為最新的嘗試,是名為“雙化”的概念。
馬開城說,這可以簡單理解為之前信息化系統的集大成之作。
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擁有電腦的解放軍,正逐步實現信息化指揮、作業以及信息化訓練,與此同時,努力達到錢學森的理想。其實,在這幾個系統之間,往往有交叉之處。比如信息化指揮系統也擁有作戰驗證的模塊,可以部分實現作戰實驗的功能。
在公開向媒體展示的展板中,作戰實驗系統已經進入“人在環”與“人不在環”結合的嘗試。
所謂“人不在環”,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在模擬對抗時,與一支參演陸軍部隊一同協作的“電腦部隊”空軍、陸航、其他陸軍部隊,等等,可以進行仿真智能運行。
比如識別敵方威脅大小、進行實戰化攻擊..總之,這些“不在環”的“電腦部隊”可以像真正的軍隊一樣作戰,從而完全模擬一場戰斗或戰役的進程。
如果在指揮模擬對抗中,一個參與對抗的指揮員可以選擇一支“電腦部隊”親自指揮,就是“人在環”;其他“不在環”部隊智能運行。當然,他可以隨時更換“在環”部隊進行指揮。
這種仿真作戰實驗說起來容易,卻有著極其復雜的系統。比如,對于戰場上的偶發事件,到底應該如何設定?
.《戰爭論》的作者克勞塞維茨曾說,戰爭是充滿不確實性的領域。戰爭中行動所依據的情況有四分之三好像隱藏在云霧里一樣,是或多或少不確實的。
所以,作戰實驗系統其實是在模擬“一團迷霧”。
比如在加入政治工作對軍隊影響的嘗試中,依托了西方軍隊“士氣”的因素。“一般說,戰損越高士氣越低,但是像電影《英雄兒女》中的王成,打到最后一人卻是士氣最高漲的時候。”馬開城說,所有這些,都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
這是充滿嘗試的30年,而且,“這期間正是世界新軍事革命從萌芽到蓬勃興起的時期。面對西方軍事強國加速領跑的嚴峻形勢,這個團隊始終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危機意識、使命意識,進行了后發者的奮起直追。”張華偉說,.這些嘗試、實踐和追趕,最終還是希望促使解放軍在真實的戰爭中達到唯一目標:打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