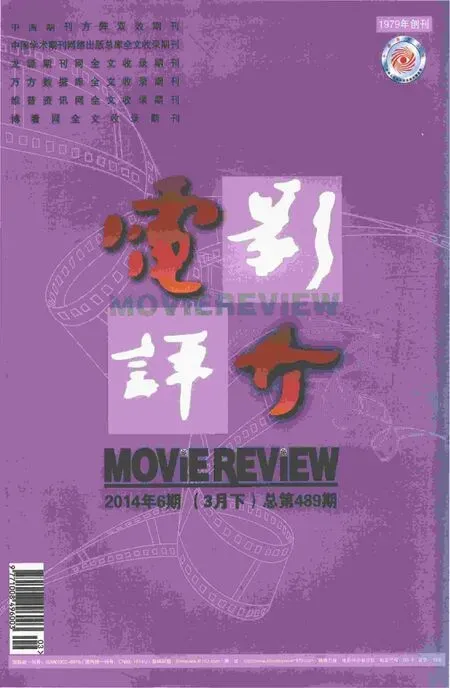《無人區》敘事表達的硬傷
□文/吳玉霞,新疆藝術學院影視戲劇學院副教授,博士

電影《無人區》劇照
2009年寧浩導演拍攝了《無人區》,該片被擱置4年后2013年12月3日上映,上映-周就創下了1.4億元的票房。雖然有人贊譽它是內地少有的佳作,但筆者認為《無人區》在藝術上雖有獨創新之處,但在敘事表達上卻存在一些硬傷。
一、人物形象塑造顯得凸凹不平,缺少感人的魅力
在敘事性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處于核心地位,人物形象豐富生動,故事就生動感人。寧浩曾說:“對我來說要在人物上有更多的訓練、學習,因為過去電影都集中在事件上,人物偏弱。”[1]的確,《無人區》暴露出寧浩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不足。
首先,潘肖的性格發展變化缺少邏輯性,顯得太突兀。
《無人區》中的律師潘肖遠赴西部,為了錢,昧著良心幫助老大(多寶杰飾)逃脫法律的制裁。面對敗訴警察對他的指責,他毫無愧疚之心,反而志得意滿。潘肖對老大一直強調自己和對方不一樣,對方是動物,自己是人。但從本質上看潘肖和老大是一樣貪婪自私的,存在的區別只在于殘忍程度不同而已。一個如此自私冷漠的人的要轉化為一個“英雄”,其中必定要有非常特殊的事件來作為轉折點。影片中潘肖經過無人區遭到老大報復,可謂危機重重,在極端惡劣環境中他與妓女相遇,為了生存不得已互相合作。但是,影片后面卻讓潘肖為了救妓女而“舍生取義”。導演為了完成所謂“救贖”思想演繹,讓潘肖轉化為“舍生取義”的“英雄”不是說不行,關鍵是潘肖何以從一個自私自利的黑心律師變成可為他人獻出生命的“英雄”,這個轉變是怎么形成的?其中令潘肖發生徹底轉變的“事件”(“撬動點”)是什么?影片中所制造的轉變關鍵事件缺少強有力的說服力,影片的敘事在這方面是空洞無力的,所以人物性格發生那么大的轉變很難令人信服。
二、其他人物形象缺少豐富性和立體感
《無人區》主要反映人性善惡的問題,影片中“善”與“惡”的斗爭的張力應該是非常緊張激烈的。因此,產生矛盾的人物形象一定要詭譎多變,豐富多彩才能達到這樣的藝術效果。可是,《無人區》中除了潘肖之外,其它人物形象都很單薄。比如黃渤飾演的角色,感覺他就是完全按照多寶杰的命令執行盜獵、殺人活動的一個工具而已,沒有任何個性化特征,也很難出彩。而多寶杰飾演的老大,本應該是矛盾斗爭的主動挑起者,事件變幻的驅動者。但是影片卻把他塑造成一個簡單的“壞人”典型而已。他的性格特征似乎只有貪婪、兇殘。影片為了強化他貪婪兇殘的特點,主要展示了他三次用車撞死人。如果說第一次用車突然撞死警察還能表現他的兇殘、膽大包天的特點外,第二次用車撞死敲詐他的女人就顯得愚蠢,殺雞焉用牛刀?第三次用車撞死傻子簡直就是滑稽可笑。這些情節并沒有使得這個人物形象豐富、復雜、生動起來,從而產生很高的藝術魅力。
余男飾演的妓女本應成為影片的“關鍵”和“亮點”,但是她能留給觀眾深刻印象的只是她的那一段鋼管舞和被活埋的慘烈。其余部分對這個人物的鋪墊太少,她和潘肖之間的情感互動也不夠,人物形象太過單薄,缺少深刻性。因此潘肖為了救她而舍生取義的轉變顯得不可信,沒有發揮出能夠使人物轉變的強有力的支撐,自然也缺少震撼人心的魅力。
三、敘述混亂,致使主題思想表達不清
探討人性善惡是《無人區》的主題,透過這個主題寧浩要表達的主題思想是什么?影片表達不清。為了強化人性善惡的演變,寧浩在《無人區》中放棄了自己擅長的“多線程敘事結構”,嘗試用“線性敘事”來敘述故事。故事一開始就通過主人公潘肖的旁白講了他高中老師所講述的兩只猴子摘桃的故事。這個老師講述的兩只猴子摘桃的故事揭示了這樣一種思想:人性本惡,但有向好的可能,這個向好的可能的基礎就是利他主義。潘肖出場,影片繼續以潘肖的口吻陳述道:“在我成為一名合格的律師之后,我又想起了那個關于猴子的故事,而現在我特別想告訴我的老師,人之所以為人,不是因為放棄自私,而是因為人會用火。”說明潘肖與高中老師的觀點是有很大分歧的。影片如果按照這種敘事方式來講述故事,那么敘事邏輯就要通過一系列事件來演繹這兩種觀點的交鋒。上映版《無人區》開頭以旁白敘事表明這部影片應該是主人公潘肖的回憶,但影片中潘肖與卻“舍生取義”犧牲,妓女幸得逃生,回到城市當上了舞蹈教師,過上了自己期待的生活。這樣敘事邏輯發生了混亂,導致以下問題:
首先,影片以潘肖的旁白來敘事卻讓潘肖死亡,造成觀眾的迷惑。
影片一開始就以潘肖回憶的口吻進行敘事,潘肖就應該是一個線索性的人物,那么潘肖最后的結局不應該是死亡了,而應該是在與“動物”斗爭中因“利他”的原因獲救,于是思想發生轉變,走向自我“救贖”之路,這樣敘事邏輯才是清晰合理的。但是,導演讓潘肖在斗爭中死亡了,敘事線索性人物犧牲了,線索就斷了,敘事角度就混亂了,這樣勢必造成主題思想的無所適從。筆者認為,如果以潘肖的旁白開篇敘事,潘肖作為線索性人物就不能走向死亡,而是思想轉變后“獲救”,完成自我“救贖”,這樣才能實現導演前面設置的兩種觀點交鋒的敘事邏輯,巧妙地與我們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相契合,而且也不違背必然律和可然律的藝術創作規律。
其次、影片“補拍”的結尾戲和故事敘事不統一,使故事主題思想混亂。為了使影片通過審查,2010年初,《無人區》在北京“補拍”了約5分鐘的結尾戲。余男飾演的妓女作為一名幸存者,在一個布滿柔和光線的舞蹈教室里,終于如愿以償,當上了舞蹈教師助理,獲得新生。誠然,這段補拍是充滿了溫暖的善意,似乎滿足了觀眾美好善良的心愿。但是,余男最后這個結局和寧浩想要表達的寓言是什么關系?這段補拍實際上破壞了電影的敘事風格、敘事邏輯,使得觀眾不明白導演的主題思想到底是什么。
總之,盡管寧浩的《無人區》在類型片方面進行了探索,在影像風格方面進行創新,寧浩在電影領域努力實現自我突破。但是上映版《無人區》在敘事表達上存在的人物性格塑造凸凹不平、人物形象不生動以及主題思想表達模糊不清這些的“硬傷”,使得寧浩這部力求實現自我突破的影片沒能夠成為一部完美的佳作,沒能夠超越先前他的“瘋狂系列”,這不能不說是一份遺憾。
[1]然然.《無人區》四幕劇:寧浩獨白[J].電影,2010(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