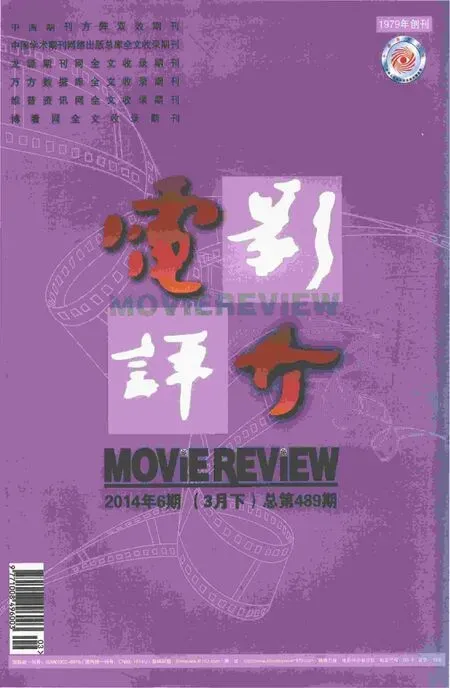從存在主義視角看電影中的暴力觀
□文/陳敏敏,江西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碩士生

電影《圣瑪利亞女孩》海報
1992年在圣丹斯電影節(jié)上,一部名為《Reservoir Dogs》的影片吸引了眾多電影人的評論,這部影片是導演昆汀·塔倫蒂諾的處女作,從他的這部早期作品中,我們已經不難看出昆汀獨特的黑色元素的電影風格。影片吸引我們的有其流暢的場面調度、調侃的多人對話、豐富的人物關系構建、以及復雜的敘事結構,當然,還有它的重要屬性——暴力的訴求。如今,當代影視作品中暴力一詞越來越多的呈現在傳統(tǒng)的現代美學形式之中,對其美學定義的探究也在不斷的深入,而與此同時由于商業(yè)因素與消費因素等的介入與裹挾,其中的美學精神已很難完美存現和表達,而呈現更多的卻是無盡的狂躁、野蠻與裸露。
一、自我意識——暴力的侵蝕
在當代電影的發(fā)展浪潮中我們越來越多的接收到暴力觀的侵襲,“暴力”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意指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等權利的強暴行為。可以看出暴力包含的元素可以是殘忍、血腥、非人道等。從人類的生理層次上說 ,暴力行為是先天性的。西方現代行為學創(chuàng)始人康拉德·洛倫茨在《論侵犯性》一書中談到:人的好斗性是一種真正的無意識的本能。這種好斗性即侵犯性 ,有其自身的釋放機制,同性欲和人類其他本能一樣,會引起特殊的、極其強烈的快感。”[1]弗洛伊德也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解釋了人對暴力熱衷的原因。在《文明及其缺撼》一書中,弗洛伊德說道:“在所有這些后面的那一點真理——人們是如此急于否定它——即人類并非是溫和友善的盼望著愛的生物,并且在受到攻擊時只是簡單地保護自己,但是大量存在的侵犯性不得不被認為是本能天性的一部分。”[2]從弗洛伊德的角度上說,人對暴力具有一定的熱衷性,它源于人的原始欲望,因此潛在的心理指導行為性的暴力產生。而無論從生理還是精神分析層面來講,暴力都是對自我意識的一種辨析,也就是說我們的暴力意識以主體為起始點,以他者為出口點,它的存在是先于我們意識自身的。
自電影誕生之初,暴力意識就初步顯影在作品之中,1903年的鮑特導演的《火車大劫案》,這部在新澤西拍攝的西部片,充滿動作、暴力、幽默及特效。本片在全美和全世界都大受歡迎,也成就了“五分錢戲院”的熱潮。也正是因為人們對于暴力場面這個無意識的體驗首次在銀幕上得到間接的宣泄,以至于對當時“暴力銀幕”的宣泄產生了一種迷戀。1913年在格里菲斯導演的《慈母心》中,女人的孩子因為丈夫的疏于照顧而去世,她獨自在花園精神錯亂地走動。突然撿起一只枯枝,向四周瘋狂揮打。這樣一系列的爆發(fā)性蠻狠動作,透露出她被壓抑的情感,心理的打擊促使她用最原始的暴力意識去摧毀四周青綠的生命以至從中獲得自我意識的緩解和填充。從格里菲斯的這部作品中不難看出人的非理性暴力意識發(fā)源于自身,這種積壓性的暴力意識的產生是因為“他人意識”的存在,我感覺到了“他人”,然后反思到“自己”,而在這種反思中更加夸張的隱射和補充了自身的蒼涼與空洞,這里的“他人”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體、社會、乃至宇宙。
所以,每當遇到刺激時,我們往往首先都是在“個人意識”的對象里建立起一個虛擬的他者,并以那個他者反觀我們自身,這樣原始的暴力意識也就自然而然的產生了,它是一種彌補的方式,也是一種牽制自身精神淪陷的方式,因為自我意識得不到彌補,后期的暴力性沖突則會以井噴的方式顯現,無論是電影中還是正在觀看電影的觀眾都需要這樣的意識牽制和彌補。我們與外界事物交遇時的存在方式,會有各種刺激和連帶牽引出我們自身的最原始的暴力意識噴發(fā),這樣的現象在早期的西部片、警匪片、恐怖片等電影中都能本色和真實的體現。
二、你我共存——暴力的哲辯性
薩特曾說過:“人與人的主體共在,容易走向兩種極端:一個極端是自己任別人擺布,還有一個極端是自己任意擺布別人。”[3]也就是:他人即地獄。六七十年的世界電影,沒有了二戰(zhàn)痛徹心肺的悲痛,也沒有社會慌亂時陰霾籠罩的惶恐,但這卻是一個悲觀的年代,嘲諷和恐慌彌漫四周,社會的感染、人權的沖突等撕裂了眾人的思緒。因而在這個時期,電影進入了一個探討關乎于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共在與共存的暴力觀哲理視界。
改編自小說大師安東尼·伯吉斯的小說《發(fā)條橙》是著名導演庫布里克最暴力的作品,充滿暴力傾向的少年阿歷克斯邪惡冷酷又迷人,影片風格在構建視覺上采用隨性的紀錄片式,從他的作品中可以深刻的看到對于自我生存現狀的悲觀傾向以及傳統(tǒng)價值的失望。他的作品人物多半表現無理性,懦弱,自私自利,腐敗野蠻,充斥著破碎的暴力觀意識,而這樣的非理性行為則是在社會的刺激中的一種自我反射而導致在人與外界交往的矛盾之中走向擺布與被擺布的兩個極端,這也正好印證了庫布里克所說:“他的電影只對人的殘暴本質感興趣,因為那才是人的真實形象。”[4]導演馬丁·斯科塞斯的作品《窮街陋巷》也是一部充滿暴力性的作品,反映的是作者小時候周遭的生活環(huán)境。他的角色努力想掙脫狹窄生活的環(huán)境,一切只能用暴力解決,因為沒有別的出路。其它作品中一貫是局外人,為了被認可而奮斗,如《出租車司機》、《紐約,紐約》、《好家伙》等等。影片粗獷風格與角色生活之粗礪相互呼應,人物所顯現出來的那一絲人性閃光之處,則是對自我人生與價值的一種最好的原始救贖。這些影片無不反映了人與人、人與社會相處艱難的人生苦惱——自己要么把別人當客體,要么自己變?yōu)閯e人的客體,一旦這樣的角色不能夠很好的實現,唯一能做的就是采取最自我的方式——暴力解決。當然這種與他人或社會共存時不可避免的矛盾沖突,不僅僅是你死我活的硬暴力決斗,還有情感上的軟暴力,外部矛盾是暴力,情感沖突也是暴力。這種認識到需采取暴力才能解決的矛盾方式也被薩特稱為“為他之在”。首先,他人的注視作為我的對象性的必要條件,摧毀了一切為我的對象性。他人的注視通過世界達于我,不僅改造了我的本身而且完全改變了世界。我在一個被注視的世界中被注視。
因為此時銀幕上展現的暴力方式不僅僅是本體純粹意識的凸顯,而更多的是上升到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沖突層面和解決層面之上,往往觀眾在觀看的同時也會恰當的隱射出自身的暴力沖突意識而產生同情或理解或不安。
三、自在與自為——暴力的美學精神
電影是一門獨特的藝術,它不同于其它傳統(tǒng)藝術的最大差別就在于它對于現實的揭示和記錄。因此,當人們將電影中暴力的思辨性不斷向前探究的過程中,其美學層面的意義也逐漸清晰,在當代世界電影中,尤其在推崇人文哲理、注重宗教與自我救贖的亞洲電影作品里更為突出和深刻。
暴力與色情是人們評價韓國導演金基德影片時用得最多的兩個詞匯,他的作品中男性大多數為暴力的化身,而女性的身份多為妓女或類似妓女般出賣肉身,影像風格血腥而又暴力。金基德將愛與痛作為創(chuàng)作的精神內核,作品《圣瑪利亞女孩》摘取了54屆柏林電影節(jié)最佳導演銀熊獎,影片講述了一個女孩在父親的幫助下找回自我、走向自我成熟的故事。片中父親為了不讓女兒在受任何身心的傷害,私下逐個痛打跟其女兒上過床的男子,以此來阻止女兒的行為,并代替法律和道德來對他們進行審判和懲罰。血腥、暴力一直是金基德鐘情的題材,他總是將鏡頭推向和對準人類原欲的最深層。更為重要的是,在影片暴力的廝殺的背后,更多的是探討宗教性愛救贖與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矛盾以及人性中的原罪與救贖等的問題。這也是薩特所說的自為存在,時間、空間和因果性、規(guī)定性、個體性、結構性,都是人在與世界接觸時主動存在的產物,是人的存在狀態(tài)的反映,而萬物有兩種存在——自在存在與自為存在。自在存在是獨立于人的意識之外的存在,它是混沌的,靜止的,不可描述的,無任何因果性、規(guī)定性的未知實體;而“自為存在”則是按自身的意愿否定、分辨、分離,把無限充實并靜止不動的“自在存在”部分虛空掉,使之成為有差別、相互分離,因而相互聯(lián)系,可以運動的各種事物。就金基德影片中的主人公的暴力觀,大都是將自身的自在存在潛移默化中向自為存在的世界轉變中逐漸清晰的認識自己了解自己,因此痛苦與救贖的旅程也就艱難的開始著。樸贊郁導演的《我要復仇》、《老男孩》、《親切的金子》三部影片則是對人性惡與暴的集中表現。人性的惡是人的潛在心理所決定的,人的本性從善到惡的轉變過程,也是內在心理動機的轉變,這就是所謂的自在存在到自為存在的轉化,也就是意識的本能轉化。無論是金基德作品《圣瑪利亞女孩》中的倚雋、《漂流欲室》中的女店主,還是樸贊郁作品《我要復仇》中的Kyu,仰或是《老男孩》中的吳大秀,這些人物原本的生活是簡單的,看似靜止的,卻又不時的被身邊的世界給打碎,他們的意識也開始涂抹上了純粹的以暴制暴的惡性,這是一種看似合理的細膩轉化的過程。那些被意識顯現出來的暴戾,并不是原本就在“自在存在”中的,而是意識在對“自在存在”中的虛無所做的事實篩選。
我們來到這個世上本身虛無的主體,而在與社會生存的道路上不得不對大千世界下意識地主動塑造,使之清晰明了,因此這些影片中人物的自我塑造本是自身存在的一種不得已方式。其實,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在這樣一個壓迫式的轉換中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自身既定存在狀態(tài)的一個改造過程,只是改造的過程是以暴力的方式去化解而已罷了。
結語
暴力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一個哲學問題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它在世界百年電影長廊中占有舉重若輕的地位。如今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圖解的時代,相對于文字,影像的功能更能夠準確直觀的傳達當代人的思想和理念。對于暴力觀的美學研究,電影藝術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當今世界充斥著大量的暴力元素,而作為人的自我意識之本能,我們不能一味的回避其暴力性,也不能一味的推崇暴力,而是應該在兩者之間做出我們正確的價值判斷和人性引導。縱觀電影的歷史,我們不難發(fā)現電影在圖解和構建暴力這一原始元素時它所追從的路徑基本是:本我——我與他人——自我,這樣一個過程的演變和轉化,也就是將暴力拆解以及將其與美學精神組合的過程中。我們要始終明白,暴力在美學精神層面上的體現不是肢體上的血腥殘暴,而更多的是情感與信念相背時的意識沖突,它凸顯的是人性的善惡掙扎和深刻的省思這一主題。如薩特說的:“世界從本質上來說,是我的世界。沒有世界,就沒有自我性,就沒有人;沒有自我性,就沒有人,就沒有世界。”暴力觀的美學性建構又何嘗不是這樣的呢!
[1](奧)康拉德·洛倫茨.On Gression[M].紐約,1963:127.
[2](奧)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撼[M].傅雅芳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131.
[3]張會軍,黃欣.崛起的力量:韓國電影研究[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
[4]陳曉云.電影理論基礎[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