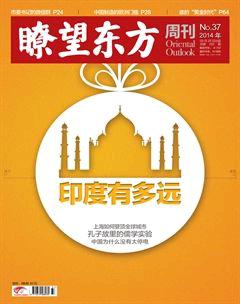十年防疫記
劉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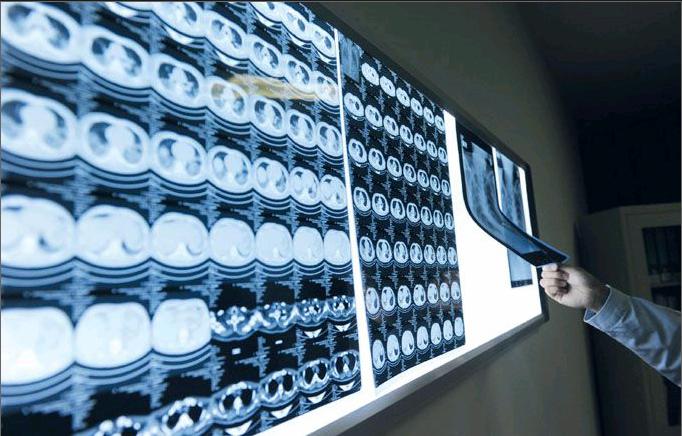
遙遠地方的每個人,其實都與我們有關。對吳曦來說更是如此。
埃博拉,這在非洲肆虐的疫情,不時也會讓她感同身受,偶爾記憶閃回。
作為一名“抗非典戰士”以及非典患者,曾經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急診科護士,11年前的4月,吳曦還身在一家非典隔離醫院。
北大人民醫院曾是非典重災區,急診科是重中之重。
那時,吳曦目光所及極其單調,心情在明暗之間反復切換,對聲音則無比敏感。院子里的布谷鳥經常從凌晨叫到天明,她會感到一絲欣喜,“新的一天終于來了!”
如今,2014年夏末,吳曦陪著兩歲的寶寶,用她的話說:“每天都有驚喜!”幸福溢于言表。
而彼時,北大人民醫院正準備向非洲派出援外醫療隊。此前,已有來自北京多家醫院的醫護人員趕赴西非。
世界衛生組織多名官員反復表示,中國從抗擊非典到應對禽流感疫情過程中形成的對疫情快速全面反應的經驗,可適用于全世界。
我靠的是“精神防護”
2003年4月17日,吳曦記得,那天急診科護士王晶走到分診處對她說:“給我一只體溫表,好像有點兒燒。”
數值顯示這個姑娘確實在發燒。隨后她住進了隔離病房,還穿著白大褂。
很快,患者越來越多、越來越急。防護服、設備供應開始缺乏。
“當時,央視柴靜采訪我,問采取了哪些防護措施。我只是說了一個詞:‘精神防護。”北大人民醫院急診科主任朱繼紅對《瞭望東方周刊》回憶說。
朱繼紅后來做流行病學調查時發現,附近北方交通大學校醫院的防護設備都比自己的醫院要好。“他們是鐵路系統的,有資源,直接調了一火車皮防護設備過來。”
“壓力很大。之前危機意識不強,等危機真來的時候,大家都亂了,束手無策。當時衛生部門印發的指導手冊是以前資料攢的,派不上太大用場。”吳曦回憶說。
現在回想起來,朱繼紅也覺得,最初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很多人知識儲備都不夠,希望用勇氣去戰勝疫病。
北大人民醫院被隔離的第一天,曾有人提議組織一些集體活動以體現樂觀主義精神,被時任副院長的王杉制止。
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如此分析:當時“由于我國傳染病發病率已經降得較低了,可供研究的病例樣本變少了,很多傳染病的癥狀大夫都沒見過”。
起初,北京人民醫院還能對每一例病人都進行流行病學調查,把受感染的來龍去脈搞清楚。隨著患者越來越多,一切開始陷入混亂。
同事不斷病倒,也有人請假不來上班。
2003年4月21日,吳曦被確診感染。兩天后,整個北大人民醫院被隔離,吳曦等被轉移到一家醫院治療。
作為第一梯隊成員,朱繼紅進入隔離區工作。領導說進去一個月就出來,然后隔離三周就可以回歸社會。
朱繼紅吃住都在醫院,睡在解剖室,滿屋子福爾馬林的氣味。
在從隔離區撤離之前的那天晚上,一名同事辭職。那天白天,朱繼紅還找他談話、鼓勁,并且許諾:“就撐一晚上,天亮之后我帶你們出去。”
最終,醫務人員心理失守。在今天的描述中,這是他們認為最可怕、最不愿回首的事情。
“像一盆冷水一樣,哐當下來。大家就都醒了,也嚴肅、嚴謹了。”吳曦這樣總結非典對于醫務工作者的影響。
醫院能拒絕病人嗎
隔離前那個晚上,吳曦想回急診科看看,“拿幾套病號服、輸液針帶著給大家也好”。
站在科室門口,凄涼場景讓她永難忘記,“窗戶哐當響,屋里亂七八糟,風涼颼颼讓人瘆得慌。”
在隔離醫院住院期間,她寫了一本日記。“想起來就寫,想起什么就寫什么……”
她把窗外布谷鳥的叫聲錄下來作為手機鈴聲,直到前兩年換新手機,才換了鈴聲。
2003年5月28日,吳曦出院。她把在隔離醫院使用的所有東西都扔掉了——除了日記。但是,那以后她從未打開過這個本子。
回家的那天,吳曦擔心被另眼相看,提前一站從送她的救護車上下車步行。
路過一處報攤,她看見當天《北京青年報》用一個整版的照片和文字介紹了王晶殉職的故事。
“當時就崩潰了,僅僅一個月,居然已經是隔著兩個世界,只不過我幸運地活了下來。”吳曦說。
她開始鍛煉身體,準備回醫院上班。但是生活還翻不了篇。她被檢查出雙側股骨頭損傷,肺功能也受到不可修復的損傷。
她曾忐忑著想返崗,起初也被同事好意婉拒。后來,“命運終于撕開一道口子,有陽光進來了。”吳曦回到了醫院,在多個部門工作過,還做過院長秘書。2010年她參與籌建了北大人民醫院客戶服務處。現在該處123個人,由吳曦主要負責。
吳曦等人起初被稱為“抗非典戰士”、“抗非典英雄”,“后來醫院就稱他們‘對人民醫院有突出貢獻工作者,他們也想回歸普通生活。”如今已擔任北大人民醫院院長的王杉說。
11年過去,“我們作為中心城區的三甲醫院,一旦發現傳染病一轉就走。只要疑似,馬上就轉。這也算亡羊補牢吧,至少可以避免在同一個地方栽兩個跟頭。”朱繼紅說。
事實上,“人民醫院至今仍保留著一個傳統,從來不拒絕病人。”朱繼紅說,“非典疫情告急后,也曾勸說病人不要入院,但如果患者執意要進,我們也沒有拒絕。”
朱繼紅認為,這是北大人民醫院在2003年4月院內感染大暴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時,最初就是由于患者隱瞞接觸史,從而導致院內感染情勢惡化。
另一個情節是,一家中央媒體的內參批評了北大人民醫院有“拒收行為”,后者因此受到高層批評。事后證明,這次“拒收”其實就是規勸患者去其他醫院,以避免在形勢已經非常嚴峻的北大人民醫院受到感染。
種種因素之下,北大人民醫院自己成為非典最嚴重的受害者之一。endprint
在經歷非典、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疫情考驗之后,北大人民醫院建設了敏感的應急處置能力和傳染病防控制度。現在患者已經很難隱瞞自己的情況。
而對于整個醫療衛生體系來說,醫院要處置好自己無法處理的傳染病人,已成共識。當然,這并不代表著將病人推出醫院大門。
2013年5月21日,在家屬隱瞞禽類接觸史的情況下,北大人民醫院收治了一名6歲男童。
該患兒就診期間,醫院依照規范采集標本送疾控中心集中檢測,經北京市區兩級機構很快確診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兒迅速被送至北京地壇醫院觀察治療。與患者密切接觸的50人也在短期內被核實,并且全部實施醫學觀察措施。
非典精神是什么
而在2003年4月,想把患者“轉出去”,送到更合適的醫院,難上加難。后來因院內感染情勢惡化,王杉多次向高層寫信,主張整體隔離北大人民醫院。
他認為:“傳染病科學防控重要的兩個基本原則是切斷傳播途徑、控制傳染源。如果首先想著是治療傳染病,那是違背規律,順序顛倒。”
4月20日晚,中央免去張文康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4月21日,曾光代表首都非典聯合指揮部到醫院調查。
“準備進核心區的時候,陪同人員中很多人臉都白了。”曾光對本刊回憶說,“最后就我、王杉,還有另外一人進去了。”
連續三個小時調查了九個非典污染區之后,曾光得出結論:人民醫院已經被嚴重污染,醫院反映的情況屬實。
“我當時的判斷是——這就像地震到來,這個時候帶著人們跑出去才是對的,喊‘挺住、‘戰勝地震的口號,沒有用。”曾光說。
在曾光代表首都非典聯合指揮部召開的現場辦公會上,王杉說著說著就急了:“以黨性和腦袋擔保自己所說屬實,誰要是再讓普通民眾進人民醫院就是犯罪。”
“那年我43歲,從沒說過這樣的話。從1980年做實習醫生起我就在人民醫院,實在是被現實逼得不管不顧了。”王杉言語間透著傷感,“看著身邊同事一個個倒下,那種場景實在太痛心了。傳染病防治基本原則得不到執行,而我卻無能為力。”
終于,北大人民醫院被感染的醫護人員得以離開“戰場”。
非典之后,原衛生部一次關于“非典精神”的新聞發布會期間,有媒體問王杉“什么是非典精神”,王杉脫口而出:“就兩個詞——科學、奉獻。”某種程度上,“科學”防控更為重要。
曾光表示:“西非的公共衛生功課做得太不足了,要不然不會惡化到這樣。”
在非典之后,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源重建公共衛生系統,疾病監測體系也已較為強大,基本都有現成預案,各政府部門反應迅速。
在王杉看來,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只是整體防控鏈上的一個環節。傳染病防控是全方位集團式的行動,政府應該發揮不可替代的戰略作用。
如今每當有疫情警報,王杉都會接到政府部門緊急詢查的通知,無論晝夜他們都會趕到現場。“有時候甚至有點‘過敏,但這種警惕是必需的,傳染病防控應該是常態。”
2013年,在一場關于“非典十年”的小型座談會上,曾光談了自己的體會:公共衛生問題歸根結底不是公共衛生機構的問題,而是政府行為的問題。
非典之后,全國衛生系統投入巨資加強防控系統建設。北大人民醫院“醫院感染主動監測實時預警管理系統”2012年投入試用,現在已經獲得國際HIMMS系統七級最高認證。
高燕在辦公室里向《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演示了這個系統:在電腦屏幕上就能對全院每個病人實現全過程實時、主動醫療追蹤,各種情況一目了然。只要有預警報告,高燕就能及時知道,然后提醒具體科室,甚至組織現場甄別。
這個流程在以前需要7~10天,現在采用這套系統,將院內感染管控從以前的事后管理改為實時預警。目前系統還在進行各種拓展。
感染科的現實
此次埃博拉疫情發生后,北大人民醫院在幾十分鐘內就組建起一支援非醫療隊,所有物資配備專業、齊全。
醫院內部各科室也做好了部署、演練,提高快速響應及疫情應急處置能力。
雖然“中國經驗”被作為典范,但是其提升空間仍然巨大,特別是路徑依賴、缺乏創新方面。
2004年,原衛生部出臺文件要求醫療機構組建感染科。至今大多數醫院的感染科建設投入不足,主要負責發熱門診和腸道門診,地位尷尬。
北大人民醫院感染科也是在那之后組建的。高燕除了是北大人民醫院感染管理辦公室主任之外,也是感染科創始人之一、現任科主任。
面對本刊記者,高燕脫口而出:“大多數醫院的感染科都是又破又窮,你要我說什么呢?”
在“第六屆抗感染高峰論壇”上,一位知名專家也表示:“很多醫院感染科至今還處在沒病房、沒病人、沒規范、少投入、被忽略的境地,說白了感染科不是能賺錢的部門。”
感染科的遭際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曾光告訴本刊記者:“李克強總理曾稱中國疾控中心是‘中國的寶貝,財政部門官員也認同,但是他們跟我們談項目、談資金的時候要拿政策來摳,就會發現缺乏落實細則。”
作為一線醫務人員,朱繼紅的感觸微觀、直接。他常以自身經歷跟念醫科的女兒聊些心里話:“醫務工作者要有擔當,要有悲天憫人的情懷。有擔當和沒擔當的結果會絕然不同,具體到醫療行為上可能就是生和死的差別。”
朱繼紅認為,從醫環境在惡化,醫務人員的職業素質、人文素質在下降,但他堅信這是階段性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