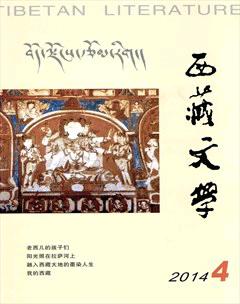癡迷格薩爾說唱 認(rèn)識(shí)格薩爾王(節(jié)選)
一個(gè)藝人,幾個(gè)聽眾,一方角落。讓土登初次認(rèn)識(shí)格薩爾的,是小時(shí)候八廓街上隨處可見的格薩爾說唱藝人。
說唱格薩爾的藝人大多來自康區(qū),以濃重的康巴口音說唱格薩爾,給人以震撼,仿佛有一種神秘力量能打通說者與聽者之間的心靈,人們只要順著說唱人的引領(lǐng),就能嗅到綠草的清香,看見英勇的格薩爾王,遇上斗智的場景,聽到戰(zhàn)場上的廝殺,而現(xiàn)實(shí)的一切不復(fù)存在,甚至忘記了自己是誰。
小時(shí)候,土登對(duì)格薩爾王本身的好奇遠(yuǎn)大于對(duì)藝人的關(guān)注。
懂事之后,知悉很多說唱藝人目不識(shí)丁,卻藏著一肚子的故事,轉(zhuǎn)寫下來竟有十幾部書時(shí),又為如此神奇之人落得乞討之地,極為不解,在土登看來連他們的家眷們也是那樣的神秘。
土登在功德林寺出家為僧后,知道了功德林寺的一個(gè)秘密:功德林寺內(nèi)是不準(zhǔn)說唱格薩爾的。原來,功德林寺內(nèi)供奉的一尊唐木欽護(hù)法神,屬霍爾部落的苯教神,后被蓮花生降伏為藏傳佛教的護(hù)法神。霍爾部落在《格薩爾》中是格薩爾的死敵。在寺內(nèi)說唱格薩爾王的英勇善戰(zhàn),怕冒犯了唐木欽護(hù)法神降禍于身。
功德林寺的這個(gè)規(guī)矩最終還是破了,那是在功德林僧人藏戲隊(duì)解散后的一次傳統(tǒng)“恰秀”林卡節(jié)上,功德林寺的主持打擦活佛親自破了這個(gè)規(guī)矩,請(qǐng)來了著名的格薩爾說唱藝人扎巴。
扎巴是西藏昌都人,由于家境貧寒,支不起差役,13歲離開家鄉(xiāng),以說唱格薩爾走遍西藏各地,據(jù)說他能說唱三十多部。他自稱前世是一只青蛙,格薩爾王征戰(zhàn)時(shí),大王的戰(zhàn)馬踩死了這只青蛙,格薩爾王下馬祈禱這只青蛙來世成為傳頌格薩爾事跡的“四大藝人”之一。扎巴生前曾多次囑咐家人,在他死后,一定要保存好他的天靈蓋,那上面有戰(zhàn)馬馬蹄的印跡。
一個(gè)目不識(shí)丁的人,記住這么長的史詩,已夠神奇,加上他神秘的身世,更讓土登等小僧們期待。扎巴一到林卡,大家就把他圍在中間。扎巴滿臉羞澀,和土登小時(shí)候見過的藝人非常不同,沒有故弄玄虛的表情,沒有闖蕩江湖的油滑,他性格靦腆,當(dāng)一雙雙期待的眼神聚到他的臉上,他的耳根子都紅了,眼睛不敢直視大家,額頭上滲出密密的汗珠。那時(shí)的土登雖小,也替扎巴擔(dān)心,怕他在眾人面前出丑。說唱開始了,扎巴拘謹(jǐn)?shù)谋砬樵絹碓绞嬲梗駪B(tài)越來越自然,漸漸地進(jìn)入角色后,肢體語言越來越豐富、表情越來越夸張,他的體內(nèi)仿佛置入了格薩爾王的魂靈,眼神不僅敢直視大家,而且時(shí)而兇悍,時(shí)而溫柔,不聽他的說詞,僅從他的神態(tài),就能感受到格薩爾王馳騁疆場的風(fēng)采。
扎巴的這一次說唱讓土登印象深刻。很長一段時(shí)間,扎巴的神態(tài)留在土登的腦海揮之不去,他迷上了格薩爾說唱。土登私下尋找會(huì)說唱格薩爾的人,這一找卻發(fā)現(xiàn)寺內(nèi)有多人暗地里說唱格薩爾。因?yàn)榇虿粱罘鹨呀?jīng)請(qǐng)過扎巴說唱格薩爾,大家也不避諱,還興致勃勃地把《格薩爾》的大概內(nèi)容講給土登聽。這之前,土登聽的都是片斷,這次有人這么完整地給土登講故事,他的興趣越發(fā)濃厚,特別是唱的部分尤其符合他的愛好,他萌發(fā)了學(xué)習(xí)說唱格薩爾的沖動(dòng)。
土登通過寺內(nèi)的僧人,打聽到功德林寺附近一戶人家,有《格薩爾》的手抄本。他順著別人提供的線索去找,沒費(fèi)多大勁就找到了那戶人家。這戶人家的房名為色木夏薩巴(新宅),戶主是當(dāng)時(shí)噶廈政府的孜仲根敦曲登。戶主根敦曲登非常喜歡《格薩爾》,因?yàn)槌B牎陡袼_爾》的緣故,他一度甚至迷上了騎馬,從功德林寺到布達(dá)拉宮短短的距離,也要策馬而去,展現(xiàn)騎士風(fēng)采,有次不慎從馬上摔下來傷了腿才罷了。孜仲本人住在這里的時(shí)間較少,家里通常只有他的傭人、一位親戚和一個(gè)僧人住著。
第一次冒然拜訪,土登心中忐忑不安,自報(bào)來意時(shí)也是語無倫次,好在孜仲的親戚多杰得知來意,只是稍稍愣了一會(huì),就很熱情地把土登迎進(jìn)家里。
這三人白天各忙各的,到了晚上才有時(shí)間坐在一起說唱格薩爾。土登只有違反寺規(guī),晚上溜出寺院,和這三人圍坐在火爐旁,聽孜仲的親戚多杰看著《格薩爾》的手抄本說唱。多杰不是說唱藝人,他說書時(shí)的神態(tài)舉止,沒有說唱藝人扎巴那般生動(dòng),但他說的是拉薩話,土登一聽就懂,更有吸引力了。每天晚上土登最怕的一句話就是:“古秀(對(duì)僧人的稱呼),今天到這兒吧。”這時(shí),他只能戀戀不舍地起身告辭。
那一陣子,格薩爾王始終盤據(jù)在土登的腦海中,特別是在他聽完《卡嶺之戰(zhàn)》后,他對(duì)《格薩爾》這部史詩有了不一樣的看法,起初他以為《格薩爾》中的戰(zhàn)爭場景,都是原始的刀槍棍箭,但在《卡林之戰(zhàn)》中,格薩爾王一會(huì)兒駕駛木制飛機(jī),一會(huì)兒利用大炮攻擊,上天入地的本領(lǐng)不光靠神魔相助,這樣的情節(jié)對(duì)于正值青春年少的土登有著極大的誘惑,他每日按時(shí)到色木夏薩巴“解渴”。
一來二去,土登和這戶人家的多杰成了好朋友,他們結(jié)束說唱的時(shí)間也越來越晚,有時(shí)天太晚,土登不顧寺規(guī),索性就住在他家。多杰對(duì)《格薩爾》十分入迷,即使他跟土登成為朋友,他也舍不得把手抄本借給土登,偶爾借了一晚上,第二天一見面就催著要,土登只能背誦那些唱詞。
土登渴望擁有一本《格薩爾》的愿望,一直到西藏民主改革之后才得以實(shí)現(xiàn)。那時(shí),他不但還了俗,還成了拉薩市青婦聯(lián)歌舞隊(duì)的演員。有一年,土登到當(dāng)雄縣演出,順便看望他的老朋友扎巴朗杰,正好在他家看到了一本手抄本《格薩爾》。土登捧在手上,左翻右看愛不釋手,他知道藏北牧民對(duì)《格薩爾》的熱愛比衛(wèi)藏一帶的農(nóng)民濃厚得多,不敢冒然言借,怕遭到拒絕。扎巴朗杰從土登的神態(tài),看懂了他的心思,爽快地說:“你要是喜歡就拿去看吧,我們這兒看說唱《格薩爾》的人很多,我可以借別人的。”就這樣,土登擁有了平生第一本《格薩爾》,雖然只是個(gè)手抄本,土登卻對(duì)它愛不釋手,很多個(gè)夜晚都是在它美妙的故事中走進(jìn)夢鄉(xiāng)的。
把格薩爾“請(qǐng)”上舞臺(tái)
很長時(shí)間里,說唱格薩爾,一直是土登繁忙的演出生活之外最大的愛好。
舞臺(tái)上,他展現(xiàn)的多是表演唱、舞蹈、相聲,或藏戲片段。偶爾也會(huì)有將說唱格薩爾片段搬上舞臺(tái)的想法,但專業(yè)文藝團(tuán)體不太支持表演非常民間的東西,加之,民間常有杰出藝人潛伏其中,土登怕自己露了拙。
民間的格薩爾說唱藝人分為兩種,一種自稱是格薩爾軍王派遣的說唱者,他們獲得格薩爾的故事頗具神秘色彩,有人稱是大病一場或一覺醒來,就記住了一部書甚至多部書的內(nèi)容。他們能說會(huì)唱,但大多不識(shí)半個(gè)藏文字母。曾到功德林寺表演的著名藝人扎巴就屬于這種情況,他留有一盒盒說唱格薩爾的錄音帶,有的還沒能從聲音轉(zhuǎn)化為文字,這一類人不能不稱之為是現(xiàn)代科學(xué)無法解釋的一個(gè)謎團(tuán)。還有一種情形是出于熱愛。這類人識(shí)藏文,得到格薩爾的故事文本后,以大地為舞臺(tái),以在群眾中進(jìn)行說唱為樂,自覺承擔(dān)文化傳播者的角色。無論哪種形式的藝人,都是格薩爾故事在民間的傳播者,他們把格薩爾的故事從草原講到農(nóng)區(qū),從鄉(xiāng)村講到牧場,無形中培養(yǎng)了一大批格薩爾迷。
土登一直想做一件開創(chuàng)性的事業(yè),把《格薩爾》搬上舞臺(tái),他相信這種形式必將使《格薩爾》的影響更大。
在西藏曲藝藝術(shù)形式中,除了土登一直從事的相聲藝術(shù),他最熟悉的就是格薩爾的說唱,格薩爾說唱藝術(shù)在民間的影響很大,讓演員取代民間藝人,以舞臺(tái)藝術(shù)的形式展現(xiàn)格薩爾的魅力,其風(fēng)險(xiǎn)性較大,要么贏得好評(píng),要么失敗告終,不像別的曲藝關(guān)注人少影響不大。另外,對(duì)于一個(gè)專業(yè)文藝團(tuán)體來說,說唱格薩爾在舞臺(tái)上的成功與否,對(duì)這個(gè)團(tuán)隊(duì)的聲譽(yù)會(huì)帶來直接影響。
幾番考量之后,土登始終覺得格薩爾的說唱最容易贏得觀眾,從他個(gè)人來講,這也是他比較熟悉的藝術(shù)形式,發(fā)揮余地較大。與團(tuán)里的其他領(lǐng)導(dǎo)溝通之后,大家謹(jǐn)慎地支持土登的想法,于是他決定冒冒風(fēng)險(xiǎn),把格薩爾說唱搬上舞臺(tái)。
有了這個(gè)想法后,土登的生活重心全部轉(zhuǎn)向格薩爾王,他不斷回憶曾經(jīng)聽過的《格薩爾》,拜訪同樣熱愛《格薩爾》的人,家里的錄音機(jī)也整日播放著民間藝人的說唱,有計(jì)劃地做著將說唱格薩爾搬上舞臺(tái)的前期工作。就在這個(gè)時(shí)候,自治區(qū)文化廳下發(fā)了舉辦首屆全區(qū)曲藝大賽的通知,土登敏銳地感覺到這是將說唱格薩爾搬上舞臺(tái)的最佳時(shí)機(jī),加快了節(jié)目的準(zhǔn)備工作。
《格薩爾》的哪一個(gè)片斷推上舞臺(tái)效果更好呢?在舞臺(tái)上,情節(jié)發(fā)展快,戲劇沖突尖銳的故事才會(huì)出彩。經(jīng)過一番思考,土登覺得《門嶺大戰(zhàn)》最符合舞臺(tái)要求,表現(xiàn)了門和嶺兩國將領(lǐng)的英勇善戰(zhàn),戰(zhàn)斗場景壯觀。
確定節(jié)目內(nèi)容容易,進(jìn)入實(shí)際排練卻遇到了困難,按文本內(nèi)容和民間藝人的說唱法,事前鋪墊很多,情節(jié)發(fā)展緩慢。而舞臺(tái)上,時(shí)間有限,情節(jié)必須更緊湊,戲劇沖突更尖銳,土登只能根據(jù)說唱文本,自己改編。
由于共同的愛好和興趣,土登一直跟喜歡說唱格薩爾的根敦曲登保持著來往,還俗成家之后,土登夫妻倆又在根敦曲登的色木夏薩巴旁邊租了一間房子。鄰里加上知音,友情特別深厚,在拉薩愛國青年聯(lián)誼會(huì)時(shí),倆人經(jīng)常一起參加活動(dòng),時(shí)常交流一些《格薩爾》的資料。文化大革命時(shí),格敦曲登在師訓(xùn)班當(dāng)教員,師訓(xùn)班緊挨著拉薩市歌舞團(tuán),他倆經(jīng)常見面,但說的都是家長里短,不敢再提說唱格薩爾的事,怕被當(dāng)成封建殘余分子。再后來,根敦曲登調(diào)到副食品加工廠當(dāng)管理員,土登就很難見到他了。在《門嶺大戰(zhàn)》的本子整理出來后,土登第一個(gè)想到的是格敦曲登,十分渴望能得到他的幫助。
拉薩城不大,土登認(rèn)識(shí)的人也不少,沒費(fèi)多大功夫,他騎著自行車找到了根敦曲登。歲月改變了面容,彼此之間的感情卻沒有任何變化,根敦曲登高興地把土登迎進(jìn)家里的那一刻,土登就深深地感受到了這點(diǎn)。土登的想法一說出口,根敦曲登就十分支持。他說:“這是件好事,我怎么會(huì)不支持你呢?”
從那天之后,時(shí)光好像回到了從前,他倆又熱烈地討論起了《格薩爾》,討論他的唱詞,區(qū)別康巴和安多人在說唱時(shí)的唱腔,尋找一種即粗獷豪放,又優(yōu)美動(dòng)聽,能被大多數(shù)接受并喜愛的說唱法。說到興致處倆人又情不自禁地唱出聲來,有時(shí)也為了某種不同的想法,發(fā)生爭論,根敦曲登為人平和謙遜,但在原則問題上十分固執(zhí)。在民間,說格薩爾之前,有四句頌詞是要用唱的形式表現(xiàn)。在舞臺(tái)上單純運(yùn)用民間的形式,土登覺得會(huì)有些單調(diào),就想把藏戲中一種稱為“覺”的調(diào)子借用過來,豐富節(jié)目形式。這一點(diǎn)上,根敦曲登是堅(jiān)決反對(duì)的,他認(rèn)為這樣會(huì)破壞說唱格薩爾的純粹性。
那段時(shí)間,土登也被各種憂慮困擾著,他是個(gè)喜歡和善于創(chuàng)新的人,放棄自己的創(chuàng)新思路很難,但又怕把握不好改編的尺度,達(dá)不到預(yù)期的效果。土登的同事們非常支持他創(chuàng)新的想法,認(rèn)為推上舞臺(tái)就一定要注重舞臺(tái)效果,不必拘泥于民間的形式。有了這樣的支持,他決定還是采用藏戲中“覺”的調(diào)子,這是一種非常優(yōu)美、非常西藏化的調(diào)子,神秘而又厚重。
土登籌備這個(gè)節(jié)目時(shí),西藏文化正因改革開放的春風(fēng)煥發(fā)生機(jī)之時(shí),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dòng)日益展開。他所熟悉的雪巴拉姆藏戲隊(duì)也獲邀在羅布林卡進(jìn)行演出,為了學(xué)習(xí)藏戲中的“覺”調(diào),土登像雪巴拉姆藏戲隊(duì)的編外演員,按時(shí)進(jìn)駐演出場地,抓住演出的間隙,向他的好友、雪巴拉姆藏戲隊(duì)隊(duì)長瑪依啦,以及他所認(rèn)識(shí)的老演員們學(xué)習(xí)。藏戲演員們遠(yuǎn)遠(yuǎn)地看到土登,就知道要被他纏住了,好在土登特別會(huì)處事,沒有一人表現(xiàn)出厭煩情緒,他們還錄了一盤帶子送給土登。這樣,土登一有空就可以跟著錄音學(xué)習(xí),節(jié)省了不少時(shí)間。很多年以后,堆龍措美的一位小學(xué)老師也對(duì)藏戲的“覺”調(diào)很感興趣,土登把那錄音帶復(fù)制了一份送給他。
為給說唱段子配樂,土登又找到了著名的音樂家邊多。他有很深的西藏民間音樂底蘊(yùn),對(duì)格薩爾說唱也有研究,土登認(rèn)為他是最適合為說唱段子配樂的人。給說唱格薩爾配樂,沒有先例,對(duì)邊多是個(gè)挑戰(zhàn),但他仍然高興地接受了這個(gè)“任務(wù)”,并且讓土登意外的是,他在很短的時(shí)間內(nèi)拿出了曲譜,真可謂是天時(shí)地利人和。
格薩爾的說唱在牧區(qū)遠(yuǎn)比拉薩流行,但在全區(qū)首屆曲藝比賽上,土登說唱的《格薩爾》大放異彩,不僅收獲了獎(jiǎng)項(xiàng),也收獲了觀眾。在此之前,很多傳統(tǒng)藝術(shù)在舞臺(tái)上失去了蹤影,土登的說唱節(jié)目達(dá)到了久旱逢甘霖的效果。土登到甜茶館喝茶,碰到一個(gè)年輕的小伙子,他看到土登,主動(dòng)走到土登跟前說,原以為《格薩爾》很枯燥,聽了您的說唱,才發(fā)覺太美妙了。當(dāng)然,節(jié)目出來以后,也有人對(duì)此頗有批評(píng),認(rèn)為這種藝術(shù)的“嫁接”,使說唱格薩爾變成了四不像。
《格薩爾》登上大舞臺(tái)
差不多與首屆曲藝比賽相隔一個(gè)月之后,自治區(qū)第一屆文代會(huì)召開,在這次會(huì)議上,西藏戲劇曲藝家協(xié)會(huì)正式成立,土登被當(dāng)選為協(xié)會(huì)的副主席。
身為西藏戲劇曲藝家協(xié)會(huì)的負(fù)責(zé)人,土登對(duì)繁榮發(fā)展西藏曲藝有了更多思考。說唱格薩爾在首屆曲藝比賽上的成功,給他和他在拉薩市歌舞團(tuán)的同事們極大的鼓舞,他們決定乘勢而上,推出多人說唱格薩爾節(jié)目。
這一次,土登整理改編了格薩爾之《卡嶺域吉》。這個(gè)節(jié)目的創(chuàng)新比之前土登獨(dú)角演出的《門嶺之戰(zhàn)》大了許多。從一人說唱變成了五人說唱,有了簡單的角色分工,故事的發(fā)展猶如舞臺(tái)話劇一般一目了然。在形式上采用藏族最常見、最喜愛的扎年琴彈唱方式,使格薩爾的說唱與衛(wèi)藏地區(qū)的音樂文化有了很好的銜接。
這個(gè)節(jié)目推出去后,獲得了觀眾的歡迎,更讓人歡喜的是,通過這次演出,參與演出的演員們愛上了《格薩爾》。在下鄉(xiāng)演出的間隙,常常有同事請(qǐng)土登說唱格薩爾,這對(duì)喜歡說唱格薩爾的土登來說,是一種幸福。土登的同事龍日就是其中陷得最深的一個(gè),他在演出這個(gè)節(jié)目之后,迷上了格薩爾說唱,他說,在說唱格薩爾時(shí),常有被一種無形力量牽引的感覺。
1982年,首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曲藝大賽的通知發(fā)到西藏曲協(xié)。這是西藏戲劇曲藝家協(xié)會(huì)成立后,第一次收到參加全國曲藝比賽的邀請(qǐng)。自治區(qū)各級(jí)領(lǐng)導(dǎo)對(duì)此高度重視,責(zé)成拉薩市歌舞團(tuán)代表西藏參加本屆比賽。無論是作為西藏曲協(xié)負(fù)責(zé)人的身份,還是作為拉薩市歌舞團(tuán)團(tuán)長身份,亦或是作為一名曲藝藝術(shù)愛好者,土登深感這是推介西藏曲藝的大好機(jī)會(huì)。團(tuán)領(lǐng)導(dǎo)班子成員商議后,決定精心排演一臺(tái)曲藝節(jié)目,從中選出最優(yōu)秀的節(jié)目參加全國比賽。
為參加這次比賽,市歌舞團(tuán)在挖掘民間藝術(shù)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新內(nèi)容與形式,編排了多個(gè)曲藝作品,但最出彩的還是格薩爾之《卡嶺域吉》。編排這個(gè)節(jié)目時(shí),土登將原本五人彈唱《卡嶺域吉》改成了八人彈唱,增強(qiáng)舞臺(tái)氣勢,并根據(jù)角色性格,在曲調(diào)上作了不同的設(shè)計(jì),以人物的性格,或溫婉悠揚(yáng),或鏗鏘有力,實(shí)現(xiàn)了八個(gè)將領(lǐng)八種調(diào)子。
節(jié)目的排練過程充滿樂趣,也充滿爭執(zhí)。在排演五人彈唱格薩爾之《卡嶺域吉》前,演員們對(duì)于《格薩爾》的了解特別少,土登作為了解這方面知識(shí)的人,更多的是在扮演傳授者的角色,同事們也樂于聽取土登的任何建議,經(jīng)過排演五人彈唱《卡嶺域吉》后,演員們對(duì)《格薩爾》發(fā)生了濃厚興趣,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傾注于對(duì)《格薩爾》的了解,有意識(shí)地從民間學(xué)習(xí)這方面的知識(shí),而這些知識(shí)又幫助他們演繹角色,在排演的過程中加入了各自的理解,每個(gè)人都堅(jiān)持自己的想法,排練變得相當(dāng)艱難。有時(shí)為了某個(gè)承轉(zhuǎn)啟合的調(diào)子,誰也說服不了誰,爭論得面紅耳赤,排練的進(jìn)展就慢了許多。在這樣的爭論中,也總有靈感激發(fā)出來,節(jié)目本身得到不斷完善。也就是從那時(shí)候開始,拉薩歌舞團(tuán)曲藝隊(duì)有了約定俗成的規(guī)矩:不論什么節(jié)目,排練之前集體討論,每人都發(fā)表見解,吸納精華后進(jìn)行修改,再立架子。他們的很多優(yōu)秀節(jié)目其實(shí)就是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
這個(gè)節(jié)目在蘇州舉行的第一屆南方片區(qū)曲藝優(yōu)秀節(jié)目觀摩演出中大放異彩,內(nèi)地的同行們對(duì)劇情不甚了解,但對(duì)節(jié)目形態(tài)、編排、譜曲、表演給予肯定,在活動(dòng)期間推出的簡報(bào)上進(jìn)行了點(diǎn)名表揚(yáng),后來又榮獲了金獎(jiǎng)。在演出的間歇,常有內(nèi)地同行向土登了解《格薩爾》,對(duì)神奇的史詩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
這一次在蘇州的演出,給了土登極大的信心,此后,他醉心于對(duì)《格薩爾》的改編整理,先后推出了八個(gè)說唱格薩爾王傳的節(jié)目。
真金頂戴百寶藝帽
每個(gè)格薩爾說唱藝人都有一頂“仲夏”,稱為真金頂戴百寶藝帽,這是格薩爾藝人的道具,也是格薩爾藝人的標(biāo)志。
在首屆全區(qū)曲藝比賽前夕,表演說唱《格薩爾》的土登也想制作一頂帽子,他小時(shí)候在八廓街生活時(shí),看見過藝人們戴著帽子說唱,但印象不深記憶模糊不清,不知道具體有些什么配飾。隨著首屆比賽的日益臨近,土登心急如焚,有人提議他去找著名說唱藝人扎巴借用一頂。土登在功德林寺當(dāng)僧人時(shí),聽過扎巴的說唱,相信他一定能幫助自己。
不說唱狀態(tài)下的扎巴,是個(gè)十分靦腆的人,話不多喜歡笑。土登作了一番自我介紹,他笑得更歡了,他說:“‘阿達(dá)啦誰不認(rèn)識(shí)呢?”原來他看過土登在自治區(qū)籌委會(huì)成立慶祝演出上表演的工布舞。這么一說,土登擔(dān)心被拒絕的心情就不復(fù)存在了。他委婉地向扎巴提出借用藝帽。扎巴的眼睛一下子暗淡了,笑容也消失了。土登忙說:“我不是借來演出的,你給我看一下,我仿照樣子自己制作一頂。”扎巴很久沒有說話,土登以為他還在考慮之中,就說:“我讓人照張像就還給你。”
他卻搖了搖頭說:“不是我不借給你,我的說唱藝帽在‘文革期間毀掉了。”
土登不敢再說什么,怕說到他的痛處,只好匆匆告辭。
為了尋求制作帽子的依據(jù),土登又找到一肚子民間故事的益西丹增,他對(duì)民族服飾很有研究。他獲知土登的難處,哈哈大笑了半天后說:“這很簡單,你去找一本《霍爾嶺之戰(zhàn)》,里面有一大段專門講述宗巴帽子的來歷、樣式、裝飾等等。”
聽到這個(gè)消息,土登非常興奮,跨上自行車就往西藏師院(西藏大學(xué)前身)跑,那里有一個(gè)《格薩爾》搶救辦公室,土登相信找到他們就可以找到本子。搶救辦公室的大旦增是土登的老朋友,可他卻讓土登失望了,他說,搶救辦公室的藏書里沒有《霍爾嶺之戰(zhàn)》這個(gè)本子,更讓人氣餒的是,他還說,他找遍了拉薩的大小書店,也沒有找到這本書。大旦增是研究格薩爾的專家,他的話不能不信,可土登還是心有不甘,從這家書店找到那家書店,八十年代初期,拉薩的書店也就數(shù)得著的幾家,他把所有的書店轉(zhuǎn)了個(gè)遍,也沒有找到《霍爾嶺之戰(zhàn)》。
為了找到這本書,土登幾乎拜訪了他所知道的喜愛格薩爾說唱或?qū)Υ擞醒芯康娜耍玫降幕貜?fù)都是一致的:沒有。有一次,他在跟朋友聊天時(shí),得知自治區(qū)文管會(huì)的嘎瑪也很喜歡《格薩爾》。“或許他那里會(huì)有藏書。”朋友這樣提醒土登。這時(shí),土登對(duì)找到《霍爾嶺之戰(zhàn)》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他像例行公事一樣敲響了嘎瑪家的門。那天,嘎瑪家有很多客人,都是從他的家鄉(xiāng)康區(qū)來拉薩朝佛的親戚。嘎瑪見平日只在舞臺(tái)上見過的土登親自登門,十分高興,熱情地招待他。倆人寒喧了半天,土登才轉(zhuǎn)入正題。嘎瑪說,他曾聽藝人說唱過《霍爾嶺之戰(zhàn)》,記得有一段專門講宗巴贊帽,遺憾的是他沒有這本書。土登再一次失望之極,出于禮節(jié),他努力克制失望的情緒。
土登和嘎瑪用衛(wèi)藏方言聊天,嘎瑪?shù)挠H戚們都是使用康巴方言,不太能聽懂倆人的談話,也不參與倆人的談話。就在土登臨走之時(shí),嘎瑪?shù)牡艿苄÷暤貑枺銈儎偛攀遣皇窃谡劇痘魻枎X之戰(zhàn)》。嘎瑪說,是呀,怎么啦?他的弟弟說,我這里有一本,不知你要的是不是這本?“不會(huì)吧。”土登以為自己聽錯(cuò)了話,把腦袋往前湊了湊。只見嘎瑪一下子興奮起來,說,那你趕緊拿出來呀。當(dāng)嘎瑪?shù)牡艿馨岩槐尽痘魻枎X之戰(zhàn)》下冊(cè)遞到土登跟前時(shí),他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接過書定睛一看,這是一本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霍爾嶺之戰(zhàn)》,或許是因?yàn)榻?jīng)常拿來閱讀,或許是因?yàn)闀r(shí)常帶在身上的緣故,磨得已經(jīng)很舊了。
回到家,土登迫不及待地拿出紙和筆,抄寫書中贊帽那一段。這一段比土登想像的還要長,他的眼睛不太好,不能連續(xù)抄寫,停停寫寫抄了好幾天,抄完一大本稿紙才總算抄好了。
《霍爾嶺之戰(zhàn)》中,宗巴贊帽這一段竟用了892行詩文大意是:除去人間形形色色總共四十七種帽子的式樣,真金頂戴百寶藝帽應(yīng)具有包容須彌山、四大洲、一座橋、一面湖和六十二座山的標(biāo)志,帽上應(yīng)有三十五種珍寶裝飾,要綴縫十六種飛禽家禽翎子。帽子的尺寸大小書中也有規(guī)定,并將帽子置于宗巴人體的六十五處部位,闡明了帽子的內(nèi)涵。
完全按照宗巴贊帽的內(nèi)容制作帽子,不僅需要很多東西,而且需要較長時(shí)間,而首屆全區(qū)曲藝比賽在即,土登只能做個(gè)最簡單的。他拿著抄好的《宗巴贊帽》,找到拉薩很著名的裁縫白章啦。白章啦年輕時(shí)是功德林寺拉讓所屬裁縫,土登和他很熟悉。此前,應(yīng)土登之邀,他為拉薩市歌舞團(tuán)設(shè)計(jì)制作過不少服飾。土登把書中的內(nèi)容逐一解釋給白章啦,白章啦也被這頂神奇的帽子深深地吸引住了,很愿意制作這頂帽子。沒過幾天,他就告訴土登帽形設(shè)計(jì)出來了。土登一看十分滿意,就和他一同上街尋找材料。這頂帽子,他縫得很仔細(xì),當(dāng)他把帽子送到土登家時(shí),土登興奮得說不出話來。
首屆全區(qū)曲藝比賽之時(shí),正是改革開放之初。當(dāng)土登一身格薩爾時(shí)代的將領(lǐng)服飾,頭戴真金頂戴百寶藝帽出現(xiàn)在舞臺(tái)上時(shí),很多人都被這樣的效果震憾了。因?yàn)樵谑陝?dòng)亂中,《格薩爾》因其宗教和神話色彩,被打成毒草,屬于嚴(yán)格禁止之列,很多藝人的服飾在“文革”期間毀掉了。
比賽結(jié)束沒多久,土登的老朋友、著名格薩爾說唱藝人扎巴和那曲格薩爾說唱藝人阿達(dá)到拉薩開會(huì),土登把新制作的帽子帶到他們所住的賓館,請(qǐng)他們對(duì)帽子改進(jìn)制作提提意見。他倆仔細(xì)看著帽子,連聲贊嘆制作得精細(xì)、漂亮,這頂帽子在倆人的手上傳來傳去,愛不釋手。土登知道扎巴的藝帽在“文革”中毀掉了,很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提議戴上這頂帽子,各說一段宗巴贊帽。扎巴不無擔(dān)心地說,很久沒說唱格薩爾,更別提宗巴贊帽,一定記不起來了。阿達(dá)也附和著說,肯定想不起來,很多年沒說了。拗不過土登的熱情,扎巴先戴上帽子說唱了一段《宗巴贊帽》,就像土登年少時(shí)看到的那樣,扎巴剛開始有些拘謹(jǐn),慢慢地就完全進(jìn)入了狀態(tài),手勢瀟灑,表情豐富,一點(diǎn)都不像很多年沒說過格薩爾的樣子。說唱完畢,扎巴緩緩地取下帽子拿在手上撫弄著說:“真神奇,剛才沒戴帽子之前,我都忘記該怎么開頭了,戴上帽子后所有的唱詞都想起來了,這頂帽子確實(shí)神奇。
從事表演工作以來,土登不知道自己穿過多少套演出服,戴過多少頂演出帽,唯有這頂說唱藝帽給他的印象最深,不僅是因?yàn)樗谱鹘?jīng)歷曲折,更主要的是它所包含的象征意義。即使沒有演出任務(wù),土登也喜歡把這頂帽子拿出來,仔細(xì)地清潔,然后再細(xì)細(xì)地品味一番。
1987年,土登接到了赴英國演出的任務(wù)。那是英國舉辦的一場說唱史詩的活動(dòng),邀請(qǐng)世界各國的史詩說唱藝人,在英國倫敦伊麗莎白皇宮獻(xiàn)演。接到任務(wù)的那一瞬間,土登有些茫然,他從來也沒有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到國際舞臺(tái)上表演。對(duì)一個(gè)演員來說,追尋最大的舞臺(tái)是永遠(yuǎn)的夢想,一旦它出現(xiàn)在眼前,又不免有些怯場的感覺。
靜心思考了幾天后,土登才慢慢被這個(gè)任務(wù)所富有的意義所激動(dòng)。他想,這是自己在國際藝術(shù)舞臺(tái)上的第一次表演,也是西藏史詩第一次出現(xiàn)在國際舞臺(tái)上,應(yīng)當(dāng)全力以赴,用最好的狀態(tài)把《格薩爾》演繹好,讓更多的人了解西藏文化的燦爛。
節(jié)目的選擇沒費(fèi)任何精力,《宗巴贊帽》在第一時(shí)間走進(jìn)了土登的腦海。制作帽子的過程中,土登已被《宗巴贊帽》美妙的唱詞深深地打動(dòng),他要向外國觀眾介紹這頂格薩爾說唱藝人的帽子,它是藏族民間藝術(shù)的結(jié)晶,其制作過程涉足之廣,歷時(shí)之長,取材之精,用料之多,施計(jì)之巧,是史無前例獨(dú)一無二的。
在英國演出,代表著中國的形象,土登希望能展現(xiàn)最好的一面。他決定完全按照《宗巴贊帽》,做一頂真正名符其實(shí)的真金頂戴百寶藝帽,這樣,故事中的帽子就能復(fù)原,說唱起來,也沒有任何缺憾,說到哪里就可以指到哪里。
按照《宗巴贊帽》的唱詞,帽子上必須點(diǎn)綴十六種鳥的羽毛,其中一些鳥類在高原上是見不到的,難度由此可見,但讓土登放棄制作帽子想法,似乎比尋找羽毛更難
當(dāng)時(shí)的拉薩,百姓生活剛剛開始好轉(zhuǎn),還沒人有閑情養(yǎng)鳥,找只鳥比什么都困難。土登發(fā)動(dòng)親戚朋友尋找羽毛,他們也很“敬業(yè)”,時(shí)常向土登通報(bào)哪條街上哪戶人家的陽臺(tái)上掛著個(gè)鳥籠子,土登就騎著個(gè)自行車高興地往提供的地址跑去,好幾次碰上的都是主人家當(dāng)廢物掛在陽臺(tái)上的空籠子,也有人莫名其妙看著土登,然后重重地關(guān)上門,讓土登一陣尷尬。
一天,一位親戚給土登帶來了準(zhǔn)信,說是親眼看見羅布林卡的一位“古尼”(僧人)養(yǎng)有鸚鵡。羅布林卡的“古尼”只有幾個(gè),土登到羅布林卡一打聽,馬上就找到了他。他得知鸚鵡的羽毛用于制作藝帽,就爽快地同意了土登的請(qǐng)求。他不想傷害鸚鵡,就把土登帶到鸚鵡跟前,讓土登自己揪一根羽毛。也許是太過興奮的緣故,土登變得笨手笨腳,揪了幾次都沒成功,鸚鵡煩躁地在籠內(nèi)掙扎著鳴叫著,“古尼”看到這里心有不忍,就說,算了吧,不要揪了,它叫得我心疼,有羽毛掉下來我就給你攢著。土登不好再固執(zhí),只好放手。后來,土登的親戚在區(qū)社科院找到了一戶養(yǎng)有鸚鵡的人家,那家人送給他好幾根鸚鵡羽毛,都是些很短的毛,土登把幾根連到一起用在了帽子上。
公雞的羽毛看似好找,找一個(gè)成色好的卻也不易。下鄉(xiāng)演出時(shí),土登鉆遍了老鄉(xiāng)家的雞窩,也沒有找到一根中意的羽毛。有一天,他到市醫(yī)院看病,看見職工生活區(qū)有人養(yǎng)雞,有一只白公雞的羽毛特別好看,很長很白且很柔軟。他前后左右看了看,也沒什么人,真想伸手揪一根下來。想歸想終究沒敢那樣做,大小也是一團(tuán)之長,為個(gè)羽毛出點(diǎn)什么事太不好看。或許是土登在雞籠前站得太久,有人把他當(dāng)成偷雞賊報(bào)信給了雞的主人,他急急忙忙趕來了。白公雞的主人是位進(jìn)藏干部,會(huì)說一點(diǎn)藏話。土登說想要一根羽毛時(shí),他用奇怪的眼神看著土登。土登只得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說了一遍。他聽后笑著說,原來是要一根羽毛,我以為是什么大事呢,你等我把雞殺了吧,那樣撥下的羽毛才更完整。土登擔(dān)心他會(huì)忘記這等雞毛蒜皮之事,然而沒過多久,當(dāng)土登再次找到他時(shí),他把一根完整的純白色的羽毛交到土登手里,讓土登感動(dòng)不已。
羅布林卡是土登的福地,雖然沒能揪到鸚鵡毛,卻認(rèn)識(shí)了很多人,這些人古道熱腸,為土登尋找羽毛提供了很多幫助。
夏天,有鳥兒在羅布林卡棲息,羅布林卡的朋友及時(shí)通知了土登。等土登趕過去時(shí),只有鶴和水鳥在水中嬉戲,他把鶴和水鳥從這頭趕到那頭,又從那頭趕到這頭,等它們圍攏到一起時(shí),又揮揮手上的長桿子,鳥兒四處飛散,偶爾會(huì)有幾根羽毛脫落下來,這樣,土登忙了整整一下午,才總算收齊了鶴和水鳥的羽毛。土登正忙時(shí),羅布林卡的“古尼”經(jīng)過這里,看到土登忙著撿羽毛,一臉惋惜地說,要是早幾天來就好了,那時(shí)還有黃鴨吶,不知什么原因后來全都死掉了。土登忙問那些死鳥是怎么處理的?“古尼”說,“樹葬”了。土登問他能不能指一下是哪棵樹。“古尼”特別理解土登的心情,就把他領(lǐng)到一棵大樹下,還為他找來一根長木桿。土登用這根長木桿把死黃鴨取下來,揪了幾根毛后,按照“古尼”的意思又把它放到了樹上。
過了幾天,土登聽說一只貓頭鷹掉到羅布林卡里,他又急急忙忙往羅布林卡跑,不巧的是貓頭鷹已經(jīng)死掉了,西藏大學(xué)生物系的一名教師趕在土登之前要走了死貓頭鷹,說是用來做標(biāo)本。土登又跑到西藏大學(xué)去要.這一去收獲不小,不僅要到了貓頭鷹的翎子,這位生物老師聽說土登在制作藝帽,需要各類鳥的羽毛后,把自己收集的異鄉(xiāng)鳥的翎子送給了土登,真是因禍得福。
大雕、布谷、松雞、馬雞四種鳥的翎子是林周縣的一個(gè)親戚送的。他是一位統(tǒng)戰(zhàn)人士,喜歡做善事,在當(dāng)?shù)厝司墭O好。他知道大雕、松雞和馬雞常常停在懸崖高處,就托牧羊人替他找了回來。布谷據(jù)說是“送”上門來的。這位親戚住在熱振寺旁的覺多鄉(xiāng),那里有很多“灑布“(一種植物),布谷喜歡吃“灑布”,經(jīng)常飛來這里,就被他家的貓捉到了。布谷在很多人眼里是神鳥,常有人專門去聽布谷鳥聲,認(rèn)為那樣會(huì)帶來好運(yùn)氣,他的家人也很敬畏布谷,把它供在佛翕上。
禿鷲的翎子是一位天葬師送給土登的。鷂鷹的羽毛,是土登跑了很多林卡才找到的。孔雀羽毛是從八廓街上的攤點(diǎn)上買到的。
托格薩爾軍王在梵天的洪福,土登得到親朋好友的鼎力相助,傳奇般地將藝帽所需羽毛逐一索取到手。
藝帽上除了羽毛,還要裝飾三十五個(gè)飾品。大多數(shù)飾品土登在拉薩街頭買到了。托底(避雷針)很難找,土登以前的同事強(qiáng)巴尊珠后來送了他一個(gè),幫他解決了一個(gè)難題,飾品尋找過程遠(yuǎn)沒有尋找羽毛那么麻煩。值得一提的是,藝帽的鳥面是西藏著名的畫家安多強(qiáng)巴畫的,他畫的鳥面別具一格。
按照《宗巴贊帽》,藝帽上除了上述配飾,還需要真金實(shí)銀點(diǎn)綴,這下可把土登給難住了。按照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初的生活狀態(tài),大多數(shù)人還只是剛剛解決溫飽,哪還有閑錢置辦金子之類奢侈品,在這樣的時(shí)候,打死土登也拿不出一小塊金子。他絞盡腦汁想辦法,終于想起到香港演出時(shí),主辦單位送過一塊渡金的紀(jì)念幣,也算是沾金吧,這時(shí)候就派上了用場。銀子,土登家里有一塊袁大頭,原本是想攢著打個(gè)銀器,也算是添個(gè)家當(dāng)。這時(shí),土登卻改變主意了,他的妻子通情達(dá)理,知道拗不過土登,就很爽快地“貢獻(xiàn)”了出來。
真金頂戴百寶藝帽的制作,花費(fèi)了土登不少的精力、時(shí)間,但它的制作過程,也讓土登獲益匪淺,通過尋找裝飾物,他更加深刻地認(rèn)識(shí)到《格薩爾》更深遠(yuǎn)的文化內(nèi)涵,這樣的感悟又使得他能夠更好地演繹《格薩爾》。
戴著這頂真金頂戴百寶藝帽,土登在英國倫敦伊麗莎白皇宮表演了時(shí)長55分鐘的《宗巴贊帽》,表演得出神入化,淋漓盡致,他深深地相信這是藝帽給予他的力量。
在伊麗莎白皇宮說唱格薩爾
1987年,作為中國藝術(shù)代表團(tuán)成員,土登有幸前往英國倫敦參加國際藝術(shù)節(jié)。
這次的旅行經(jīng)歷不太美妙,在二十余小時(shí)的長途飛行中,土登一直處于暈機(jī)狀態(tài),惡心和嘔吐使他的身子越來越虛弱。好不容易抵達(dá)倫敦后,情況并沒有像預(yù)期那樣好轉(zhuǎn),連續(xù)幾天,他無法正常進(jìn)食,更惱人的是整夜失眠,無法得到休息。由于語言不通,他原本就對(duì)說唱節(jié)目能否在英國取得成功擔(dān)憂,如今身體又如此不爭氣,讓他十分難過。
來自泰國、土耳其、緬甸、印度、摩洛哥、日本和中國等九個(gè)國家、四個(gè)地區(qū)的近百名藝術(shù)家已經(jīng)匯集在倫敦,正摩拳擦掌準(zhǔn)備向來自歐洲各國的觀眾展現(xiàn)本國精湛的傳統(tǒng)藝術(shù)。與土登一道表演民族古代英雄史詩的,還有印度和日本的史詩演唱家。
這次的演出對(duì)我國意義重大,因?yàn)檫@是英國首次向中國發(fā)出參加國際藝術(shù)節(jié)的邀請(qǐng)。而代表中國表演的土登,身體虛弱,眼看著演出日期臨近,他的心情異常緊張。中國代表團(tuán)團(tuán)長,以及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官員、翻譯都在為土登擔(dān)憂。
土登要表演的《宗巴贊帽》是《霍嶺大戰(zhàn)》的一個(gè)片段。說的是覺如通過賽馬登上嶺國的王位,成為格薩爾王不久,北方的魔王魯贊施用魔咒搶走了王妃美薩本吉。格薩爾王為了救美薩,不聽他人的勸阻,只身一人前往魔國。歷盡艱辛后,在美薩的幫助下殺死了魯贊魔王,但美薩在給格薩爾的食物中施加了忘鄉(xiāng)魔咒,使格薩爾王在魔國過著樂不思鄉(xiāng)的日子,一呆就是三年。在這期間,霍爾國的軍隊(duì)占領(lǐng)了嶺國,搶走了王妃珠牡。賈擦等嶺國英雄雖奮起抵抗,但因嶺國將軍晁同通敵,戰(zhàn)事以失敗告終,嶺國眾多英雄被殺,王妃珠牡被囚禁。聰明的珠牡派神鳥三兄弟去魔國尋找格薩爾大王。格薩爾王從神鳥那里得知消息后,變成民間說唱藝人宗巴三兄弟,對(duì)霍爾國國王、大臣及王妃等說唱宗巴贊帽,以藝帽動(dòng)人的故事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然后將老魔霍爾白帳王降伏。
整段說辭,看起來介紹帽子,實(shí)際上巧妙地以隱語和暗示流露出復(fù)仇的心境,表現(xiàn)好這段說唱,必須要表現(xiàn)好人物的心理。
為了表現(xiàn)節(jié)目的原生態(tài),土登在策劃這個(gè)節(jié)目時(shí),融韻白、唱腔、表演為一體,沒有加入任何樂器伴奏,節(jié)目時(shí)長55分鐘,節(jié)目難度之大,是他數(shù)十年藝術(shù)生涯中首遇,在正常的身體狀況下,他都感覺有些吃力,何況是在身體如此虛弱的情況下。無論身體如何不適,每天入睡前,土登還是要把自己關(guān)在酒店房間,獨(dú)自彩排一次《宗巴贊帽》,等到說唱接近尾聲時(shí),他總是感覺身體完全虛脫,沒有任何氣力了。
1987年7月17日的夜晚,對(duì)于大多數(shù)人,是個(gè)普通的夜晚,而對(duì)于土登,卻是極其重要的夜晚。這一天,土登代表中國,登上了英國倫敦伊麗莎白皇宮劇場的舞臺(tái),表演藏族史詩《格薩爾》。
皇室劇場的豪華,土登無心細(xì)細(xì)欣賞,異國觀眾的入場,他無意仔細(xì)觀察。他滿腦子都在想著如何將表演發(fā)揮到極致。他穿戴著制作精美、獨(dú)具風(fēng)范的格薩爾服飾和真金頂戴百寶藝帽候場時(shí),暗暗地為自己打氣,一定要演出格薩爾軍王的雄威。
當(dāng)主持人報(bào)出表演者是土登的剎那間,奇跡出現(xiàn)了,土登頭部的某根神經(jīng)似乎被打通了一般,幾天來的昏沉狀況消失了。土登像一名行走在草原的藝人,用最淳樸的方式做了開場。自此仿佛幻化成了格薩爾王變身的宗巴,沉重的身子骨立刻輕盈起來,他神情激越,聲音飽滿,宗巴贊帽中所有的人物一一出現(xiàn)在他眼前,他好像不是個(gè)藝人,而是他們中的一個(gè),心中激蕩著智慧。
說唱類節(jié)目靠的是精準(zhǔn)的語言,土登最擔(dān)心的是語言不通會(huì)使觀眾沒有興趣。雖說主辦方把節(jié)目的英文介紹單事先分發(fā)給了觀眾,但他的心結(jié)一直存在著。令土登驚訝的是,節(jié)目開場,觀眾鴉雀無聲,惟有土登的聲音在劇場回蕩。這和土登在拉薩演出時(shí)的場景大相徑庭,在拉薩,報(bào)幕員報(bào)出說唱格薩爾后,年輕人趕緊趁這個(gè)機(jī)會(huì)出去一下,出去時(shí)也不太小心,碰到椅子弄出很響的聲音。場內(nèi)時(shí)不時(shí)有人高聲議論一番或大聲咳嗽一陣,吃口香糖磕瓜子的,根本算不了稀奇。可在英國,一個(gè)語言不通的地方,卻讓土登真正感受到了對(duì)于藝術(shù)家的尊重。安靜的演出空間,使土登的熱情如涌泉噴發(fā),全場55分鐘,他一口氣說了下來,沒有感到一絲的疲憊,他感覺自己和宗巴已融為一體。
謝幕時(shí),土登高呼“吉吉,索索,拉杰羅!”場內(nèi)藏胞與土登同聲歡呼,全場沸騰,所有觀眾起身鼓掌祝賀演出成功。這是一次難忘的經(jīng)歷,掌聲經(jīng)久不息,面對(duì)著熱情的觀眾,土登的眼眶里積滿了淚水,四次返場答謝。
更讓土登感動(dòng)的還在后面。活動(dòng)主辦單位負(fù)責(zé)人、一位高大的英國人在向土登祝賀演出成功,連連贊嘆他“創(chuàng)造了歷史”的同時(shí),告訴他這么一件事:“剛才在您演出之時(shí),也許您注意到一對(duì)老夫婦離場了。他們這對(duì)老年夫婦沒有私車,家住得又遠(yuǎn),只能坐公交車回去,太遲了,趕不上公交車,不得已才先離場了。他們走之前讓我一定要向您解釋一下。”這是土登從藝以來,第一次聽到觀眾為離場表示歉意。他不知該怎么回答負(fù)責(zé)人的話,只有一遍遍地回謝這對(duì)夫婦對(duì)他的尊重。
事后,又有坐在臺(tái)下的藏胞告訴土登,這對(duì)老夫婦離場時(shí),怕弄出響聲,脫下鞋子提著走了。直到現(xiàn)在,一說到這對(duì)英國夫婦,土登就會(huì)感慨萬千。
在英國演出的成功,使土登對(duì)《格薩爾》的研究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格薩爾》的搶救與保護(hù)工作做點(diǎn)事情。很快,他的想法得到了《格薩爾》搶救辦公室的回應(yīng),他們把土登整理的宗巴贊帽翻譯成漢、英兩種文字,并幫助出版。1991年,他們又邀請(qǐng)土登參加第二屆《格薩爾》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土登在大會(huì)上宣讀了《把格薩爾說唱藝術(shù)從民間搬上舞臺(tái)走向世界》的文章,真實(shí)地介紹了自己與《格薩爾》的不解之緣。也許是因緣巧合,在這次會(huì)議期間,他突然有了一個(gè)想法,不能讓時(shí)間帶走所有關(guān)于格薩爾的記憶,他要給自己精心制作的真金頂戴百寶藝帽找個(gè)歸宿。后來,在格薩爾千年紀(jì)念活動(dòng)時(shí),他把真金頂戴百寶藝帽捐贈(zèng)給了西藏博物館,希望通過這頂帽子,讓更多的人了解格薩爾的故事。自治區(qū)有關(guān)部門對(duì)此次捐贈(zèng)高度重視,時(shí)任自治區(qū)黨委副書記李立國和自治區(qū)副主席次仁卓嘎專門參加了捐贈(zèng)活動(dòng)。
(本文節(jié)選自平措扎西的報(bào)告文學(xué)《藏地追夢人——土登的傳奇人生》)
責(zé)任編輯: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