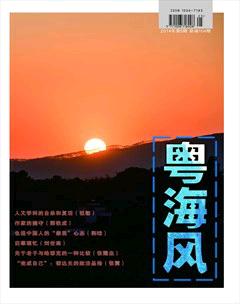人文學(xué)科的自殺和復(fù)活
【文胚】
中國古代詩論云“情乃詩之胚”;我這篇枯澀的文字是“惑乃文之胚”。
作為巴黎《歐洲日?qǐng)?bào)》專欄作家與文化記者的我,曾在巴黎采訪過許多人文學(xué)科的討論會(huì)。我感覺,所有人文的討論會(huì),和自然科學(xué)的學(xué)術(shù)會(huì)議迥然不同,相當(dāng)尷尬又無奈:人文學(xué)人們宣讀完論文后,常常會(huì)冷場(chǎng),論辯很難得展開。
原因既清晰但又讓人驚愕:因?yàn)槊科撐牡幕靖拍疃祭聿磺澹磉€亂。舉個(gè)例子吧,哈佛大學(xué)教授、當(dāng)代新儒學(xué)代表人物杜維明來巴黎宣講“文化中國”,僅“文化”這個(gè)概念當(dāng)下就有幾百個(gè)定義在被使用。若要展開討論,論辯者可以各自依據(jù)某個(gè)定義各說各話,無須偷換概念,就能在同一個(gè)概念下進(jìn)行違反邏輯學(xué)同一律的詭辯。如果要讓大家都集中到杜維明教授所下的文化定義上來討論,馬上就會(huì)對(duì)杜教授的定義的無法確定而展開無休止無結(jié)果的爭(zhēng)辯。因?yàn)椋谌宋膶W(xué)科所使用的自然語言符號(hào)體系中,根本就不可能下一個(gè)外延和內(nèi)涵均確定的概念定義。
根據(jù)信息論,所謂信息就是對(duì)不確定的消除。數(shù)學(xué)家兼哲學(xué)家羅素在他的《西方哲學(xué)史》(上冊(cè),第11頁)中說“一切確切的知識(shí)都屬于科學(xué)”,反之亦然,不確切的就是非科學(xué)。那么,人文學(xué)科的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不可能消除不確定,豈不成了沒有信息量的非科學(xué)的饒舌?
千古以追求發(fā)現(xiàn)真理為崇高目標(biāo)的人文學(xué)科,被說成是“沒有信息量”的論述,這太危言聳聽了吧?
本文就來慢慢解析這個(gè)聳聽的危言。
哲學(xué)的自殺
世上最大的動(dòng)物鯨魚會(huì)自殺;人文學(xué)科中的最博大的哲學(xué),居然也會(huì)自殺。
被譽(yù)為當(dāng)代哲學(xué)天才的維特根斯坦,在他的影響整個(gè)思想界的名著《邏輯——哲學(xué)論》的結(jié)尾處寫道:“哲學(xué)的正確方法,就是等別人發(fā)表形而上學(xué)的言論,然后向他表明那是胡說。”
傳統(tǒng)哲學(xué)認(rèn)為,哲學(xué)研究的是思維對(duì)存在、精神對(duì)物質(zhì)的關(guān)系問題,是對(duì)于整個(gè)世界(自然界、社會(huì)和思維)的根本觀點(diǎn)和體系,是關(guān)于世界觀的學(xué)說。這,當(dāng)然就是形而上的學(xué)說。現(xiàn)代哲學(xué)則界定稱:哲學(xué)的對(duì)象是人們?cè)S多信念的前提假設(shè),哲學(xué)的任務(wù)是不斷地向人們信念的假設(shè)前提進(jìn)行質(zhì)疑和挑戰(zhàn);所謂哲學(xué)家,就是從事這種質(zhì)疑和挑戰(zhàn)活動(dòng)并使用同樣可以受到別人批評(píng)檢驗(yàn)的合理方法的人[1]。無疑,現(xiàn)代哲學(xué)研究的還是形而上命題。
由此可見,無論傳統(tǒng)還是現(xiàn)代哲學(xué),其功夫全在做“形而上”(即解釋經(jīng)驗(yàn)范圍以外的問題)。這倒好,權(quán)威哲學(xué)家自己出來宣布哲學(xué)的形而上全是胡說,那不就是哲學(xué)的自殺嗎?那不是自廢武功嗎?難怪英國人把這驚世駭俗的維特根斯坦的結(jié)論叫做“奧康剃刀”[2]!
哲學(xué)就是用這把“奧康剃刀”自殺的。
引申開去,其實(shí)所有人文學(xué)科都是弄“形而上”的。這樣一來,“奧康剃刀”連帶把整個(gè)人文學(xué)科都給殺掉了。
以羅素、維特根斯坦為先導(dǎo)的邏輯實(shí)證主義,是用什么理由讓哲學(xué)自殺的呢?
邏輯實(shí)證主義維也納學(xué)派認(rèn)為,任何論述,只要不合規(guī)范(即不以邏輯和數(shù)學(xué)的規(guī)范陳述),或不能以經(jīng)驗(yàn)相檢驗(yàn),就毫無意義。他們首先繼承19世紀(jì)物理學(xué)家和科學(xué)哲學(xué)家恩斯特·馬赫提出的觀點(diǎn):既然我們是通過自己的感覺獲得有關(guān)科學(xué)事實(shí)的知識(shí)的,那么作為最后一著,科學(xué)必須成為感覺的描述。接著拿愛因斯坦的相對(duì)論和新的量子理論的成就來證明他們的“能檢驗(yàn)才有意義”的理論。愛因斯坦的相對(duì)論說明:除非你考慮如何驗(yàn)證關(guān)于同時(shí)性的論述,你就不能賦予諸如同時(shí)性這樣的概念以意義;也就是說,談?wù)撌录l(fā)生在同一時(shí)間的意義,取決于同時(shí)性是如何在觀察中被實(shí)際確立的。對(duì)于量子理論也是這樣。在量子論中,并未給予粒子同時(shí)具有精確的速度和準(zhǔn)確的位置的概念以任何意義,因?yàn)楦鶕?jù)海森堡的“測(cè)不準(zhǔn)原理”,測(cè)量速度會(huì)影響位置,測(cè)量位置則會(huì)影響速度,無法加以驗(yàn)證。他們由此斷定,有意義的論述只有兩種。一種是關(guān)于世界的經(jīng)驗(yàn)性論述,他們的意義在于能被驗(yàn)證。另一種是數(shù)學(xué)或邏輯陳述,此種論述純系自我驗(yàn)證,正確者是同義反復(fù),錯(cuò)誤者則自相矛盾。如果一個(gè)論述不屬于上述兩種類型,則該論述毫無意義。這樣,他們給了哲學(xué)、宗教和所有人文學(xué)科一條“無意義論述”的繩子,讓他們集體去上吊。然而在哲學(xué)上吊得奄奄一息時(shí),他們卻又松開了繩子,要哲學(xué)換一種活法,說:“哲學(xué)的任務(wù)變了,去當(dāng)自然科學(xué)的侍從,用現(xiàn)代邏輯分析的方法去澄清科學(xué)所使用的概念,以及區(qū)分科學(xué)論證的方法是否合理等等。”他們認(rèn)為科學(xué)做的是關(guān)于世界的論述,那是一級(jí)主題,哲學(xué)只能做二級(jí)主題——論述科學(xué)關(guān)于世界的論述。用吉爾伯特·賴爾的話說,哲學(xué)是“關(guān)于論述的論述”。
弄了幾千年的屬于最高智慧的哲學(xué),現(xiàn)在竟說不清道不明它謂何物了!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干脆連“哲學(xué)”的條目都刪除了。
依我看,哲學(xué)的“自殺”,不僅是因?yàn)樗拿}不可驗(yàn)證,還有比這更糟糕的、先天性的沉疴呢。
哲學(xué)和所有人文學(xué)科,使用的符號(hào)體系是自然語言(日常語言)。我曾寫過一篇題為《(自然語言的)概念在過飽癥中脹死》的散文[3],描繪了自然語言的概念,因?yàn)椴辉敢庠焯嗟男略~(概念),就在舊瓶里不斷裝新酒,即不斷地對(duì)老概念進(jìn)行新的界定,多少萬年積累下來,大部分概念的定義就不是一個(gè),而是幾十、幾百個(gè),于是“脹死”了。譬如“自由”這個(gè)概念,在古羅馬時(shí),其定義是“自由乃是從被束縛、被虐待中解脫出來”。到了19世紀(jì),研究人類自由史的英國艾克頓(Lord Acton)勛爵,就收集到了兩百多個(gè)關(guān)于“自由”的定義。何止是“自由”一個(gè)概念?像“美”“文化”“精神”“愛情”“思維”等等不勝枚舉的自然語言概念,全因?yàn)槎x太多而“脹死”。為何說“脹死”呢?定義越多,外延就越大。按照邏輯學(xué),外延越大,內(nèi)涵就越小,當(dāng)外延趨向于無限大,例如像中國的“道”,外延大到了無所不包、無所不在的地步,其內(nèi)涵就趨向于零,概念就“脹死”了。凡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話一定是內(nèi)涵等于零的廢話。所有概念,世代人們往里塞進(jìn)去了各種風(fēng)馬牛不相及的內(nèi)涵,甚至是相互抵牾的內(nèi)涵,使得概念充滿著歧義。今天若要進(jìn)行詭辯,根本用不著像古希臘詭辯家那樣去偷換概念,完全可以在使用同一概念下利用歧義而違反同一律進(jìn)行詭辯。最有趣的例子是,當(dāng)下國際上關(guān)于“人權(quán)”的對(duì)話,都是各國依憑各自的定義,在同一概念下進(jìn)行著“義正詞嚴(yán)”的違反同一律的詭辯。
凡正確的邏輯推理和論證,必須在所有概念沒有歧義的前提下才能進(jìn)行。標(biāo)志人文學(xué)術(shù)水準(zhǔn)的所謂的合乎邏輯的“學(xué)理性”,因?yàn)槠淙粘UZ言符號(hào)體系中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無法確定的先天性缺陷,而被連根拔掉了。
不靈的藥方:人工語言
自然科學(xué)的符號(hào)體系都是人工的、數(shù)學(xué)化的,每個(gè)概念都有消除了歧義的定義。在這樣條件下的邏輯操作才是有意義的。
邏輯實(shí)證主義的哲學(xué)家們,他們中的多數(shù)是“兩棲型”的學(xué)者——既是自然科學(xué)家,又是哲學(xué)家。如,羅素是數(shù)學(xué)家,維特根斯坦是數(shù)理邏輯學(xué)家,石里克是物理學(xué)家,卡爾普納是數(shù)理邏輯學(xué)家,很自然會(huì)把數(shù)理邏輯那套方法論引申到人文學(xué)科中來。他們?cè)噲D給哲學(xué)等換一套“人工語言”,以用來治療自然語言的先天性歧義之病。經(jīng)過他們幾代人的工作,還真形成了一個(gè)“人工語言學(xué)派”。
其成效如何呢?
《西方文化百科》[4]一書對(duì)此介紹如下:
人工語言學(xué)派是分析哲學(xué)中的一個(gè)派別。這一派認(rèn)為,日常語言是模糊不清的,因此主張借助數(shù)理邏輯的符號(hào)體系造出一個(gè)理想的人工語言。最早提出這一主張的是弗雷格。羅素和懷特海在《數(shù)學(xué)原理》一書中,實(shí)際構(gòu)造了這樣一個(gè)人工語言系統(tǒng)。前期的維特根斯坦和維也納學(xué)派的成員們,也持這一觀點(diǎn),特別是卡爾納普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設(shè)想過兩套具體方案。一套是“現(xiàn)象主義的語言理論”,注重個(gè)人的直接經(jīng)驗(yàn),注重對(duì)經(jīng)驗(yàn)和現(xiàn)象的直接描述。但它解決不了一些自然科學(xué)理論性概念無法直接觀察的問題和個(gè)人經(jīng)驗(yàn)缺乏的公共性問題。于是他又提出第二套“物理主義的語言理論”。主張證實(shí)一個(gè)科學(xué)命題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翻譯成物理語言。凡是不能翻譯成物理語言的命題都是沒有意義的。物理語言指的是以觀察為根據(jù)并描述時(shí)間空間狀態(tài)的語言。這種語言的最大好處是具有公共可觀察性,即用這種語言描述的事件,在原則上可以被所有人共同觀察到。他們提出用物理語言統(tǒng)一全部科學(xué)的口號(hào)。但是,物理主義語言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尤其是對(duì)于思想、精神、觀察不到肉體變化的感知覺、心理現(xiàn)象的研究,都使它無能為力。
“人工語言”的設(shè)計(jì)終于以失敗告終了,沒有能為哲學(xué)和所有人文學(xué)科的符號(hào)歧義病找到仙丹靈藥。
可能有些人文學(xué)家很不以為然,嗤之以鼻,稱他們?cè)缇陀辛私鉀Q概念歧義的法門。在立論之首,他們就對(duì)自己使用的概念進(jìn)行了精確的界定,從混沌的日常語言概念中獨(dú)立了出來。在這個(gè)外延和內(nèi)涵都確定了的概念體系下,所進(jìn)行的合乎邏輯規(guī)則的推理,當(dāng)然就能得到具有學(xué)理性的真理。
不,人文學(xué)者根本不可能打開這個(gè)法門,是空想。
人文學(xué)者在界定自己的概念時(shí),必然要應(yīng)用混沌的日常語言中的“類概念”和“種概念”。例如,黑格爾給“自由”下的定義是“主觀意志和客觀規(guī)范合二而一”,他使用的日常語言中的種概念是“主觀意志”和“客觀規(guī)范”,使用的類概念是“合二而一”。無論種概念“主觀意志”與“客觀規(guī)范”,還是類概念“合二而一”,在日常語言中又都有著上百個(gè)以上的定義,充滿歧義,這又得再給它們下定義。可是在對(duì)它們進(jìn)行定義時(shí),又必須在日常語言中選擇相關(guān)的種概念和類概念,而這些種概念和類概念又充滿歧義……。這樣無限循環(huán)下去,完全是一個(gè)無可窮盡和毫無結(jié)果的界定過程。因此,人文學(xué)者大言要對(duì)自己使用的概念做到“無歧義的界定”,那是一個(gè)自欺不欺人的“烏托邦”。
人文學(xué)科還有三個(gè)不可能具有確定性的“宿命”
學(xué)問之初,無論中外,人文學(xué)科和自然科學(xué)是混在一起的。
在人類語言的語詞上把哲學(xué)家和自然科學(xué)家分開是19 世紀(jì)才發(fā)生的事。1833年,在英國劍橋大學(xué)召開的英國科學(xué)促進(jìn)會(huì)上,著名的科學(xué)史家威廉·休厄爾才仿照“藝術(shù)家”(Artist)一詞,造了個(gè)“科學(xué)家”(Scientist),用來稱呼像法拉第那樣在實(shí)驗(yàn)室中探索自然奧秘的人們。在這之前,像伽利略、牛頓等歷代研究自然的人都稱為自然哲學(xué)家。牛頓在1687年出版的純屬于自然科學(xué)的力學(xué)巨著其書名就叫《自然哲學(xué)的數(shù)學(xué)原理》。直到1809年進(jìn)化論的先驅(qū)馬克出版的生物學(xué)代表作,還叫《動(dòng)物哲學(xué)》,人文和自然科學(xué)到此還是個(gè)“連體兒”。
人類怎么會(huì)弄出個(gè)哲學(xué)和科學(xué)來的呢?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學(xué)》篇中解釋道:“當(dāng)今人們開始從事哲理的思考和探求,都是由于驚異。他們最初從明顯的疑難感到驚異,便逐步進(jìn)入到那些重大問題上的疑難,例如關(guān)于日月星辰的現(xiàn)象和宇宙創(chuàng)生的問題。感到困惑和驚異的人想到自己無知,為了擺脫無知,他們就致力于思考。因此,他們這樣做顯然是為了求知和追求學(xué)術(shù),而不是為了任何實(shí)用的目的。”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有天賦的好奇心,有強(qiáng)烈的給自己產(chǎn)生驚異的對(duì)象的解釋欲望,無論是人文學(xué)科還是自然科學(xué),在開始都是受好奇心驅(qū)使的,以求得一個(gè)沒有實(shí)用目的的滿意解釋。
人們對(duì)日月星辰等天體現(xiàn)象的驚異,對(duì)控制個(gè)體行為的風(fēng)俗習(xí)慣的驚異,起初都是用宗教和神話來詮釋的。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詮釋由神來創(chuàng)世造物,由神來為人類制定道德秩序。在西方,自古希臘人發(fā)明了邏輯之后,他們率先用人的合乎邏輯的思維——自然哲學(xué)——去解釋人的驚異。
當(dāng)然,自然科學(xué)中的歐幾里德的幾何學(xué)、阿基米德的杠桿原理和浮力定理都在開始時(shí)就被實(shí)用了,這就是科學(xué)史上的所謂“工匠傳統(tǒng)”。但是,它們還是離不了所謂“哲學(xué)傳統(tǒng)”。一直到17世紀(jì)的笛卡爾,將自然科學(xué)數(shù)學(xué)化,用數(shù)學(xué)演繹的符號(hào)體系代替日常語言的推理體系,才獲得了定量的精確性。后來,牛頓繼承伽利略倡導(dǎo)的實(shí)驗(yàn)加數(shù)學(xué)的方法,提出實(shí)驗(yàn)歸納和數(shù)學(xué)演繹的方法,于是開啟了現(xiàn)代科學(xué),使得自然科學(xué)從自然哲學(xué)中逐步獨(dú)立出來,成為主要是為了征服自然的有實(shí)用目的的科學(xué)。
當(dāng)現(xiàn)代自然科學(xué)出現(xiàn)之后,哲學(xué)等人文學(xué)科,就剩下解釋人的精神領(lǐng)域的“形而上”地盤了。
用數(shù)學(xué)加實(shí)驗(yàn)的自然科學(xué),具有可重復(fù)性、可預(yù)測(cè)性的準(zhǔn)確性。它在人類物質(zhì)生產(chǎn)中不斷創(chuàng)造奇跡的事實(shí),尤其是產(chǎn)生了工業(yè)革命的輝煌成果,使得人文學(xué)科的古典光輝——柏拉圖所說的哲學(xué)家為王的光輝——黯淡下來。這樣,一種模仿自然科學(xué)方法論的“泛數(shù)學(xué)主義”流行開來。這個(gè)人文新潮流認(rèn)為,數(shù)學(xué)不僅統(tǒng)領(lǐng)整個(gè)自然科學(xué),還要統(tǒng)領(lǐng)整個(gè)人文學(xué)科和社會(huì)科學(xué)。德國當(dāng)代哲學(xué)家、思想史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在《人文科學(xué)的邏輯》一書中舉例證明了這種“泛數(shù)學(xué)主義”的存在:“格老休斯(Hugo grotius)所制定的現(xiàn)代自然法(Naturrecht),就是建立在法律知識(shí)與數(shù)學(xué)知識(shí)之間存在著的一項(xiàng)徹底的類比之上的;而斯賓諾莎則建造了一個(gè)嶄新的倫理學(xué),這一倫理學(xué)以幾何作為其取法的典范,并且借著幾何的典范去描繪出其目標(biāo)與途徑。……因?yàn)橹挥腥绱耍瑪?shù)學(xué)性思維之網(wǎng),才能以用同樣的方式去把物體世界與心靈世界、去把自然的存在和歷史的存在予以全部籠罩。”[5]
卡西勒接著就指出,對(duì)于這種在人文學(xué)科中應(yīng)用的類比式的泛數(shù)學(xué)主義,18世紀(jì)的意大利思想家維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就開始說“不”了。
人文學(xué)科是在價(jià)值和意義上做功夫的,價(jià)值和意義怎么能用數(shù)學(xué)方程式表達(dá)呢?
這便是人文學(xué)科不可能獲得像自然科學(xué)那樣準(zhǔn)確的宿命之一。
之二是,人文學(xué)科更不可能做到像自然科學(xué)那樣的實(shí)驗(yàn)和觀察實(shí)證。自然科學(xué)的對(duì)象是物質(zhì)世界,具有性質(zhì)上的恒常性與法則上的恒常性,因此可以通過可重復(fù)的實(shí)驗(yàn)或觀察,去驗(yàn)證由邏輯推出的和用數(shù)學(xué)表達(dá)的理論。我們稱這種實(shí)驗(yàn)驗(yàn)證為“自然科學(xué)理論的實(shí)驗(yàn)自洽”。人文科學(xué)的對(duì)象——廣義的人文學(xué)科一般指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象和文化藝術(shù)的研究,在西方,通常認(rèn)為包括語言、哲學(xué)、歷史、文學(xué)和其他藝術(shù)的研究等——大凡是不可重復(fù)的有生命的“個(gè)別”,根本不可能進(jìn)行可重復(fù)的實(shí)驗(yàn),宿命地沒有保證命題有可靠的“實(shí)驗(yàn)的自洽性”。
之三是,人文學(xué)科沒有自然科學(xué)體系里的“公理自洽”。在歐幾里德的幾何學(xué)中,理論前面就有被我們千萬次經(jīng)驗(yàn)不證自明的五條公理。凡根據(jù)公理按邏輯推出的所有定理都是正確可靠的。我把它稱之為“公理自洽”。可是,所有人文科學(xué),只有理論前的假設(shè),如老子的“道”、黑格爾的“絕對(duì)理念”、薩特的“存在”等,這些假設(shè)都不是不證自明的公理,因此就不能保證從理論前的假設(shè)所邏輯推導(dǎo)出的各種命題的可靠正確。人文學(xué)科宿命地不具備“公理自洽”性。
一言以蔽之,由于不可能將充滿歧義的日常語言改變成沒有歧義的數(shù)學(xué)符號(hào)體系,由于沒有自然科學(xué)式的理論前的“公理自洽”或理論后的“實(shí)驗(yàn)自洽”,人文學(xué)科宿命地就不可能具有自然科學(xué)那樣可驗(yàn)證的確定性。所謂人文學(xué)科的“邏輯上的學(xué)理性”,不過是個(gè)不能保證理論確定性的“花架子”而已。
馬克思經(jīng)過可謂嚴(yán)謹(jǐn)?shù)倪壿嬐评恚暦Q發(fā)明了科學(xué)的共產(chǎn)主義理論,對(duì)資本主義的崩潰進(jìn)行了預(yù)測(cè),對(duì)如何實(shí)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進(jìn)行了設(shè)計(jì)。然而,經(jīng)過近一個(gè)世紀(jì)的國際性實(shí)踐,還是像柏拉圖邏輯推理出來的“理想國”一樣,是個(gè)烏托邦。在冷戰(zhàn)期間,西方國家有多少蘇聯(lián)和東歐問題的研究所,有多少關(guān)于這方面的專家,可是,沒有一個(gè)研究所和沒有一位專家對(duì)1989年開始的東歐及蘇聯(lián)的共產(chǎn)制度解體做出預(yù)測(cè)。
即使是以日常語言為符號(hào)體系的社會(huì)科學(xué),譬如熱門的經(jīng)濟(jì)學(xué),也是與人文學(xué)科一樣有著三個(gè)“宿命”的。世界上沒有一位研究亞洲經(jīng)濟(jì)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在1997年對(duì)正在興旺發(fā)達(dá)[為此,李光耀在大聲疾呼要以“亞洲(威權(quán))價(jià)值”取代西方民主價(jià)值]而突然爆發(fā)的東南亞國家貨幣危機(jī),提出任何預(yù)警報(bào)告。同理,美國以及全球那么多獲得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金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沒有一位能對(duì)2008年在美國發(fā)生的次貸經(jīng)濟(jì)危機(jī)做出預(yù)測(cè)。
然而有趣的是,柏林墻倒了之后,成百上千個(gè)國際政治學(xué)者馬上站出來用“邏輯嚴(yán)謹(jǐn)”的學(xué)術(shù)語言給世人解釋柏林墻為什么會(huì)倒;在亞洲國家貨幣危機(jī)與美國次貸經(jīng)濟(jì)危機(jī)發(fā)生之后,立即就有成百上千個(gè)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科學(xué)地”證明發(fā)生的機(jī)理是什么。
上述這些例子,不是證明人文學(xué)者、社會(huì)學(xué)者智能低下而無為,而是證明這類以日常語言為符號(hào)體系的學(xué)科,因?yàn)槠湎忍烊毕荩豢赡苡袦?zhǔn)確預(yù)測(cè)之為。
中國的人文學(xué)科是怎么做的?
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在《智慧之路》中提出一個(gè)人類文化的“軸心時(shí)代”的觀點(diǎn),他認(rèn)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600年中,出現(xiàn)了希臘的畢達(dá)哥拉斯、德莫克利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老子、孔子等一大批哲人,他們排除了人類神秘的“原始思維”對(duì)宇宙的神話解釋,開始用理性思維對(duì)自然、社會(huì)和人進(jìn)行審視和沉思。[6]
可是,雖然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與古希臘思想家們同在“人類文化軸心時(shí)代”之中,但因?yàn)闆]有能發(fā)明亞里士多德的邏輯的最核心部分——三段論證法[7],因而他們做人文理論的方法與古希臘思想家的邏輯論證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從春秋戰(zhàn)國的老子、孔子開始,直到清朝的王夫子、戴震,兩千多年的中國人文學(xué)科都沒有進(jìn)入邏輯操作。他們的方法是在自己極其豐富廣博的人生閱歷基礎(chǔ)上進(jìn)行寧靜了悟,待獲得解釋人文對(duì)象的超常心得時(shí),不懂得使用邏輯論文文體闡述,而是用“隨感散文”文體表達(dá)出來。
約公元前6世紀(jì)的老子,是中國有史記載的第一位思想家。他的五千言《道德經(jīng)》開創(chuàng)了道家學(xué)派。他在《道德經(jīng)》中介紹了做學(xué)問的方法:“不出于戶,以知天下,不窺于牖,以知天道”(第四十七章)。不出門、不望窗外就能知天下、知天道,當(dāng)然是自己靜心了悟而得的了。比老子小二十多歲的創(chuàng)立儒家學(xué)派的孔子,他也是主張“仁者靜”(《論語·雍也篇》)、“學(xué)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xué)則殆”(《論語·為政篇》):合起來就是靜思。這種靜思的方法,在他的學(xué)生曾子那里,表現(xiàn)為“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xué)而篇》)。這一天三次反省,當(dāng)然不是邏輯推理,而是沉思感悟。
老子、孔子開創(chuàng)的以“靜心了悟”的方法來做人文學(xué)問的規(guī)范,就此傳之千秋。莊子提倡的達(dá)到最高的“真人”境界的“坐忘”(《大宗師》)方法,相當(dāng)于一面做氣功,一面穎悟得道。荀子總結(jié)出以“虛一而靜”(《解弊》)的思維方法達(dá)到“大清明”的徹悟,就是要虛心、專一、清靜。把儒學(xué)神化的董仲舒,他那套“天人感應(yīng)”的神秘主義理論——“名教”,是怎么弄出來的呢?他自己沒有說,宋代史學(xué)家司馬光用詩為他總結(jié)出來了:“吾愛董仲舒,窮經(jīng)守獨(dú)幽。所居雖有園,三年不游目。邪說遠(yuǎn)去耳,圣言飽滿腹。發(fā)策登漢庭,百家始消服。”(《司馬文公文集·讀書堂》)由此可見,董仲舒也是“守獨(dú)幽”三年才得到的大悟。儒學(xué)第二里程碑“理學(xué)體系”的集大成者朱熹,他的“格物致知”的方法,便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朱子語類》卷15),格物窮理多了,忽然在某一天融會(huì)貫通而達(dá)到大徹大悟。這個(gè)“格物”,就是對(duì)著萬物冥想,把心里本來就存有的“理”給激活,達(dá)到頓悟。悟出“心外無物”和“滿街都是圣人”的完成儒家“心學(xué)體系”建構(gòu)的王陽明,就是在他35歲那年,被貶到貴州龍場(chǎng),日夜端坐,靜思默想,忽然在一天夜里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這便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龍場(chǎng)得道”的佳話。(《王文成公全書》卷32,《年譜》)被稱為中國近代民主主義思想啟蒙者(著有可和盧梭《民約論》相媲美而比盧梭早一百多年的《明夷待訪錄》)、寫出中國第一部學(xué)術(shù)史巨著《明儒學(xué)案》《宋元學(xué)案》的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黃宗羲,是在他參加8年抗清的浴血戰(zhàn)斗失敗之后,經(jīng)40年靜心感悟造就的思想碩果(黃璽炳:《黃梨洲先生年譜》)。清代另一位中國古代思想集大成者、提出“太虛一實(shí)”、用太虛之氣解釋宇宙的王船山,在36歲那年,先是隱姓埋名躲到深山的苗族和瑤族的山洞里,后來隱居衡陽蓮花峰和石船山下,“晨夕杜門,靜心思索,開始了三十余年的著作生涯”(《十大思想家》第196—197頁)。他的八百多萬字的《船山遺書》,全來自一個(gè)和老子、孔子一樣的“靜悟”。由此可見,兩千多年的時(shí)間跨度,無論是儒道佛哪個(gè)學(xué)派,中國思想家治人文學(xué)科的方法全沒有進(jìn)入邏輯,而是一個(gè)“悟”字了得!
正是因?yàn)樗枷氤晒欠f悟之果,選擇的文體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邏輯論述,而是非常自由的詩性散文文體。老子用的是散文詩,孔子用的是散文式的語錄。這和柏拉圖的對(duì)話體是迥然不同的,柏拉圖的《理想國》雖然也是師生間的對(duì)話,但是每位發(fā)表的論證都是按邏輯方式進(jìn)行的,《論語》中的孔子和學(xué)生的對(duì)話,都是說自己的感悟(結(jié)論),不加任何邏輯論證。莊子的文體是散文式的寓言。以后的歷代思想家的文體,都是這種詩性散文文體。
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學(xué)科,其形而上的道(理念)和形而下的器(文體)是十分匹配的。
中國古代哲人沒有發(fā)明邏輯,只能用感悟來做人文學(xué)問,反倒歪打正著。因?yàn)椋宋膶W(xué)科用日常語言作為符號(hào)體系,沒法消除概念的歧義性,根本不能滿足進(jìn)入邏輯推理的條件,只能用靜悟之法。相反,西方人文學(xué)科歷代所用的邏輯操作,反倒是假冒的學(xué)理性,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方法論。
然而,在“西學(xué)東漸”之后,中國這套非邏輯體系治人文之學(xué)的方法和文體逐漸消亡了,應(yīng)運(yùn)而生的是學(xué)習(xí)西方的邏輯加實(shí)證的方法來做人文:這不是自殺,而是被他殺。
怎樣復(fù)活?
既然人文學(xué)科不可能提供像自然科學(xué)那樣確定的理論去設(shè)計(jì)未來,連所有的預(yù)測(cè)都是沒有邏輯依據(jù)的瞎猜,那么人文學(xué)科還有什么用?為什么幾千年來人文學(xué)科沒有消亡?
因?yàn)椋宋膶W(xué)科有著自然科學(xué)無法替代的兩大功能。
第一,解釋精神領(lǐng)域的疑問。
人類有一種“精神本能”,即對(duì)世界和自身不斷地提問、追問,力求得到自圓其說的解釋,以滿足人才具有的一種普遍的精神消費(fèi)——解釋欲。英國當(dāng)代著名哲學(xué)家、英國功勛勛章獲得者艾賽亞·伯林爵士把人的解釋欲稱作“這是一種完全自然的人的欲望;是被一些最富想象力、最有智慧和才華的人所深深體驗(yàn)到的。”[8]
從人類的認(rèn)識(shí)發(fā)展看,早在懵懵懂懂的人類“童年”,就開始問天問地問自己的問題了。問來問去,追問出了懵懵懂懂的回答,那便是神話、宗教、星象占卜、原始自然科學(xué)等的解釋。
后來,自然科學(xué)以其可重復(fù)實(shí)證的確切回答,不僅滿足了人類對(duì)于物質(zhì)世界的解釋欲,還具有預(yù)測(cè)和實(shí)用的偉大功能。
然而,自然科學(xué)卻無法滿足人對(duì)精神世界和社會(huì)領(lǐng)域現(xiàn)象的解釋。這兩個(gè)領(lǐng)域的解釋,一直由人文學(xué)科和社會(huì)學(xué)科來擔(dān)當(dāng)。由于其符號(hào)體系是日常語言,一直只能以得到“相對(duì)比較滿意的解釋”的標(biāo)準(zhǔn)來滿足人類。美國哲學(xué)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就說過:“所謂(人文學(xué)科的)真理,就是對(duì)于前人對(duì)其更前一輩的先前人的理論的解釋的再解釋的最高成果。”[9]
前面說過,政治學(xué)家沒能預(yù)測(cè)柏林墻的倒塌,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不能準(zhǔn)確預(yù)警東南亞和美國的經(jīng)濟(jì)風(fēng)暴,但是人類并不對(duì)人文科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求全責(zé)備。只要在柏林墻倒塌,以及亞洲金融風(fēng)暴發(fā)生后,人文學(xué)家社會(huì)學(xué)家能上電視、寫文章,做出成百上千個(gè)能自圓其說的解釋,使得大眾滿意,那也算是人文學(xué)科所特有的一個(gè)功德。
第二,振聾發(fā)聵地對(duì)社會(huì)時(shí)弊的批判,乃是人文學(xué)科的主功能。
當(dāng)社會(huì)處于危機(jī)時(shí)期,人們已經(jīng)感知到了嚴(yán)重的社會(huì)時(shí)弊的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某個(gè)敏感的人文學(xué)者,首先用日常語言,向處于危機(jī)中的大多數(shù)人大聲疾呼,對(duì)時(shí)弊提出有理有據(jù)的批判。這時(shí),人文理論就有著振聾發(fā)聵的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狀進(jìn)行顛覆的偉大功能。這是自然科學(xué)所不能為的。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思想家、藝術(shù)家以人文主義對(duì)于積弊千年的神權(quán)的批判,法國18世紀(jì)的啟蒙運(yùn)動(dòng)思想家對(duì)王權(quán)專制積弊的批判,中國“五四運(yùn)動(dòng)” 對(duì)于數(shù)千年舊禮教和舊文化積弊的批判等,都是人文主功能的偉大體現(xiàn)。
在西方,從亞里士多德對(duì)其老師柏拉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開始,在那里就萌生了人文的批判傳統(tǒng),充分發(fā)育出了人文的主功能。因此西方的人文史,學(xué)派林立,思想家輩出,對(duì)各個(gè)歷史階段社會(huì)的演進(jìn)起著“雄雞一唱天下白”的號(hào)角作用,為社會(huì)的新價(jià)值體系進(jìn)行“精神立法”。因此,西方把知識(shí)分子界定是具有獨(dú)立人格并能進(jìn)行獨(dú)立批判的文人。
然而在中國,自漢獨(dú)尊儒術(shù)以降,中國文人的主功能是“注經(jīng)”:證明圣人的話如何正確,證明皇帝的旨意如何圣明。主流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是爭(zhēng)當(dāng)“帝師”、軍師,一心幫著主子弄出個(gè)能夠?qū)戇M(jìn)歷史的什么安邦定國的“理論”來。直到今天還是如此。歷代中國人文學(xué)人,都被“注經(jīng)”的這把刀,將人文批判的主功能給閹割掉了。中國盛產(chǎn)在一個(gè)道統(tǒng)下的注經(jīng)派名士,很難涌現(xiàn)振聾發(fā)聵顛覆社會(huì)時(shí)弊的思想家。“陽痿人文”成了中國特色。即使在現(xiàn)在已經(jīng)消除了文字獄的臺(tái)灣地區(qū),那里的主流文人還是以當(dāng)“國策顧問”為殊榮。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春秋戰(zhàn)國之后,中國就不再產(chǎn)生有獨(dú)樹一幟的思想家,只有擅長注經(jīng)的“亞圣”“亞亞圣”……
當(dāng)然,在這里必須強(qiáng)調(diào),人文的批判,是在大多數(shù)人已經(jīng)感知到社會(huì)時(shí)弊叢生的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之上的批判,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樣,讓政治家操縱大眾的以文化為借口的暴力“批判”。從孔子批到愛因斯坦的“大批判”,不但沒有任何“社會(huì)時(shí)弊的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恰恰相反,是刻意對(duì)人類積淀的精英文化的摧毀,是人文的恐怖主義。
總之,如果人文學(xué)科不想自殺或被他殺,只能在以上這兩個(gè)功能,特別是社會(huì)時(shí)弊批判的主功能中復(fù)活。
幾句大實(shí)話
羅素說過一番很有趣的話。他說:哲學(xué)家的中心思想其本質(zhì)上都是非常簡(jiǎn)單明了的,之所以弄成晦澀的長篇大論,那是為了擊退那些實(shí)在的或想象的反論,是架在城墻上的機(jī)槍大炮,用來嚇唬任何潛在的論敵的。
我用了嚇唬人的長篇大論所討論的問題,其實(shí)也是極其簡(jiǎn)單明了的。人文的問題,既不是“水是由哪些元素構(gòu)成的” 那樣的屬于普遍經(jīng)驗(yàn)論的可用實(shí)證解決的問題,也不是“如何證明三角形兩邊之和大于第三邊”那樣的由數(shù)學(xué)和邏輯解決的規(guī)范化問題。它面對(duì)的是人類的價(jià)值、意義等精神領(lǐng)域的問題,無法用實(shí)證解決。人文學(xué)科不能建立起沒有歧義的人造語言,所以無法用規(guī)范的邏輯及數(shù)學(xué)解決問題。那么,所能用的辦法,就是面對(duì)著既不是經(jīng)驗(yàn)問題又不是邏輯問題的第三類精神問題,憑著自己在當(dāng)代最前沿的最豐富的物質(zhì)和精神的人生閱歷,去自由聯(lián)想,也就是去頓悟,然后,用當(dāng)代人喜聞樂見的非邏輯論證的文體把穎悟表達(dá)出來。其目標(biāo)是:提供較前人在某個(gè)問題上的更滿意的解釋;或者提出對(duì)當(dāng)代存在的時(shí)弊進(jìn)行令眾人心悅誠服的批判,以催化社會(huì)演進(jìn),如此而已。
請(qǐng)君別再相信哲學(xué)家或政治家會(huì)告知你可重復(fù)驗(yàn)證的“真理之上的普遍真理”。所謂“理論自信”不過是自我妄想。哲學(xué)理論、政治理論的主功能只可能是解釋與批判,從而導(dǎo)致對(duì)壞現(xiàn)實(shí)的改革或顛覆。
請(qǐng)君別再相信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有像天文學(xué)家告訴你何時(shí)發(fā)生日食那樣確定無誤的預(yù)測(cè),他只能猜測(cè)。這猜測(cè)不會(huì)比算命高明多少。他的真正的“武功”是對(duì)已是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的經(jīng)濟(jì)沉疴的解剖。
如果耶穌的復(fù)活是為了拯救人類,那么,人文的復(fù)活是為了拯救自己。
(作者單位:巴黎歐洲日?qǐng)?bào)記者)
[1]布萊恩·麥基:《思想家——當(dāng)代哲學(xué)的創(chuàng)造者們》,第2—4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版。
[2]奧康,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哲學(xué)家,他提出要對(duì)以往一切理論傳統(tǒng)進(jìn)行反省。他這個(gè)論點(diǎn)被人稱為“奧康剃刀”。
[3]祖慰:散文集《面壁笑人類》第59頁,臺(tái)灣三民書局1994年版。
[4]孫鼎國主編《西方文化百科》第102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卡西勒:《人文科學(xué)的邏輯》第12頁,臺(tái)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6年版。
[6]《現(xiàn)代思想史學(xué)派文選》第39頁。
[7]據(jù)中國學(xué)者金觀濤的研究,中國以研究邏輯著名的墨子,沒有發(fā)現(xiàn)形式邏輯最核心的原則——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證法。金觀濤、劉青峰著:《探索與新知》第285頁,臺(tái)灣風(fēng)云時(shí)代出版社出版。
[8]麥基:《思想家——當(dāng)代哲學(xué)的創(chuàng)造者們》第7—8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版。
[9]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 The Harvester Press,1982,p.92.China Fan Imb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