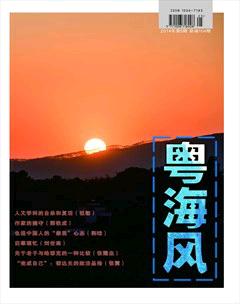我的導師唐啟運先生
蘇新春
啟運先生是我的碩士導師,出生于廣東電白,除了四年的北大求學生涯,一直工作生活在廣東,是一位地道的南方學者。在先生論著結集出版時,我參與了一些具體編務工作,也有了重新學習的機會,作為學生,實感榮幸。
先生是新中國培養(yǎng)起來的第一代語言學家。新中國成立那年他20歲,先是進入葉劍英元帥任校長的南方大學,在進入社會之初接受了責任與擔當?shù)膰栏窠逃?953年再讀北京大學語言學專業(yè)。那時的北大語言學,名師云集,匯聚了一批開宗立代的大家,先生問師于王力、岑麒祥、魏建功、高名凱、周祖謨、袁家驊等一代名師,獲得了完整而扎實的語言學知識架構,成為最負盛名的50年代北大語言專業(yè)畢業(yè)生中的一員。我在后來的學術活動中,屢屢會遇到當年與先生一起完成學業(yè)的何耿鏞、唐作藩、郭錫良、王理嘉、李行健、何九盈等前輩學者,他們都會說到與先生交往的陳年趣事,對先生當年的風華與銳氣留有深刻記憶。
先生治學范圍寬廣,關注著社會語言生活中的各種重大問題。那時的中國,久歷動蕩戰(zhàn)火初息,社會亟須穩(wěn)定;傳統(tǒng)文化劇變甚至丟失,新文化亟待重建;古白話文漸行漸遠,新白話文加速形成;繁體字初去,簡體字新立,中國語言學承擔著營造社會軟環(huán)境的繁重任務。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以社論的鄭重形式發(fā)表了《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一文,這是中國語言學社會責任的寫照。呂叔湘、朱德熙兩位先生隨之在《人民日報》連載數(shù)十文指導人們?nèi)绾握_使用語言文字,成為語言學社會擔當?shù)牡湫痛怼?955年10月的“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化學術會議”,接著的“暫擬漢語教學語法體系”“簡化字方案”“漢語拼音方案”“編纂出版《現(xiàn)代漢語詞典》”等,都是服務于社會的語言工程大項目。先生作為那個時期培養(yǎng)出來的學者,很自覺地把自己的研究與社會推進密切結合在一起。他關注著現(xiàn)實生活中幾乎所有的重要語言問題,如語言規(guī)劃、語言使用、語言教學、語言測試等。先生在《努力推廣普通話 積極推動拼音方案——紀念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問題學術會議四十周年》中回顧道:“華南師大中文系的語文工作者一直認真貫徹執(zhí)行國家關于語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責無旁貸地把推廣普通話和促進漢語規(guī)范化的工作作為己任,持之以恒地做有效的工作。在新的時期又得到了國家的表彰。1987年國家教委和國家語委召開全國高等師范院校推廣普通話工作會議,安排我們在大會上作了重點發(fā)言,讓我們介紹了推廣普通話工作的經(jīng)驗。1992年我們中文系又被國家語委授予‘語言文字工作先進單位的光榮稱號,這是廣東省高校中唯一獲得這個榮譽的。”先生長期擔任華南師大中文系主任之職,所起核心作用自在其中。1986年,國家語委把高考語文標準化考試的研究任務交給華南師大,先生親任廣東省高考語文標準化研究室主任,多年后該成果榮獲全國首屆教育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先生受命創(chuàng)辦《語文月刊》,在辦刊思想、宗旨定位、內(nèi)容與文風上,精心擘畫、身體力行,短短幾年,使它進入全國重點期刊之列,在同類刊物上形成京滬穗三足鼎立之勢。此外,先生還在《羊城晚報》上親自執(zhí)筆答讀者問,或欣賞佳文或評騭陋句,將語言規(guī)范化工作做到了第一線。
先生作為一名有深厚學養(yǎng)的語言學家,緊跟語言理論的最新發(fā)展,對關鍵、前沿、焦點問題屢屢參與討論,發(fā)表了重要意見。20世紀中國語言學中,語法學是一門顯學,特別是50年代,如何建構一個能夠為人們共同接受、進入高校課堂的教學語法體系,是各派學者共同努力的目標。大家對各種句子成分、句子類型、句子關系、語法單位、語法范疇,都進行了深入討論。先生在《中國語文》《語文學習》等重要刊物連續(xù)發(fā)表了《語法結構決定主語賓語》(1955)、《讀〈語法和語法教學〉》(1957)、《關于連動式和兼語式的取消論》(1958)等文章,先生當時還只是二十幾歲的年青學生,可觀點之通達、思路之開闊,對激爭紛起觀點的提綱挈領、融會貫通,卻顯出難得的宏達與清醒。在劃分句子成分的標準上,先生主張“確定主語賓語,應該依據(jù)詞序——漢語的基本的語法形式”,在“連動式與兼語式的關系”上,主張各有其合理性,“把這種在形式上在意義上都有分別的句子混而為一,是沒有理由的。連動兼語的格式有自己的特點,和一般的單句復句是不相同的,不是擴大的主從動詞詞組和復句所能包括的,因此應該當作特殊的句型處理”;對“把字結構”的句子功能,認為“‘把字結構根據(jù)介詞結構的通例,所屬應該是狀語,不是賓語”;對句子成分省略的規(guī)律,認為“省補留動,省動留補,或者兩者都省,在不同的情況下都是可能的,單說不能省動留補,既欠全面,也還沒有說出省動留補的條件”。這些觀點和主張,后來都成為語法研究主流學派的觀點。如果說先生在50年代現(xiàn)代語法理論建構中表現(xiàn)出來的還主要是扎實的理論功底、敏銳的問題意識和強大的邏輯思辨能力的話,那么在80年代發(fā)表的一組關于詞類活用、虛詞、句型的古漢語語法論文,則將那種輕筆落紙、單刀直入、條分縷析、理例相銜、語密論重的風格展示得一覽無遺。先生1985年起每年一篇論文刊于華南師大學報,連續(xù)五年,甫一墨成,旋及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廣為流傳,如此的傳播速率在語言學界甚為少見。
先生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另一學科是修辭學,特別是風格學的研究。毛澤東語言風格的研究源起何時,我沒有做過認真查考,但完整運用語言學理論進行系統(tǒng)分析,先生的研究無疑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早在1959年,先生所撰《毛澤東同志著作中的比喻》就先后在《中國語文》《紅旗》刊發(fā),《中國語文》在語言學界有著翹楚地位,而《紅旗》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地位更是不同一般。先生對毛澤東語言風格作了系統(tǒng)研究,涉及內(nèi)容有“鮮明的比喻”“辛辣的諷刺”“口語的運用”“古語的吸收”“諺語和成語”“精密的結構”“活潑的文辭”“豐富的詞句”“壓縮的語言”“關于文風的見解”十個方面,僅第2、第6—8個專題后來在《華南師范學院學報》(1960年2期)轉載時,篇幅就長達3.1萬字。他的《比喻結構的多樣性》(《語文知識》1957年7期),后被黃伯榮主編的全國高校教材《現(xiàn)代漢語》列入?yún)⒖假Y料。在“文革”最為蕭瑟的1972、1973年,先生仍筆耕不輟,在《教育革命》雜志連載了專論“比喻”“借代”“移就”“襯托”“擬人”“夸張”“形容”“對偶”“排比”“重疊”等的系列文章,為知識的傳承與普及上做出了貢獻,也為自己在“文革”結束后的學術爆發(fā)做好了準備。“文革”一結束,先生就出版了《句子成分論析》《成語·諺語·歇后語·典故概說》等著作,為中國學術春天的到來增添了色彩,為更高層次的人才培養(yǎng)準備了新的養(yǎng)分。
在編輯與重讀中,重溫在先生那得到過的教誨與關心,浮起了更多的感慨與感恩。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多位先生給予過撥云見日般的影響。何師一凡先生在我弱冠懵懂之時,手教口示,從舌根舌齒音到幫旁并明鈕,給了我語言學的啟蒙和定向。李師如龍先生在我羊城發(fā)展春風得意時,審人度性,知我向學之心根固,攜遷于廈門。劉師叔新、何師九盈、葛師本儀諸位先生在我語言學成長中都給予過脫胎換骨般的淬火與提升。而啟運師則是手把手牽我步入語言學大殿的關鍵先生,三年面壁,使我完成了語言學系統(tǒng)的學習。
1982年秋,我負笈南下到廣州就讀漢語史研究生。兩位業(yè)師,一位是吳師三立先生。首次在中文樓師生見面后,我們陪三立師返家,一路上三立師不攙不扶,語輕親,神高揚,八十高齡,仍身板硬朗,精神矍鑠。一位就是唐師啟運。先生時任中文系主任,常來宿舍樓探望新來的學生,噓寒問暖。兩位業(yè)師都有顯赫的學術出身。三立師是舊學背景,曾為錢玄同助手,三十即出任教授之職,首學期開的是“說文段注研究”。啟運師是新學出身,受過嚴格的語言學訓練,第一門課開的是“語言學理論”。這真是極佳的知識結構培育法。一位重傳統(tǒng)重根基,一位重理論重方法,兩兼并俱,相得益彰。那時“文革”剛過,百業(yè)蕭條,學問未成氣候,啟運師親自動手,遴選出十數(shù)篇語言學經(jīng)典范文,綴頁成冊,鉛印若干,發(fā)給我們做教材。在我的處女作《漢語詞義學》中,引用的論文類文獻皆列于各章之后,唯有一篇與著作類文獻列在全書之尾,就是先生在《文選》中所收的李友鴻《詞義研究的一些問題》(《西方語文》,1958.1)一文,里面諸多觀點深深影響著我后來的研究。《文選》還收了那個時期的專書計量研究代表作程湘清的《先秦復音詞研究》等經(jīng)典文獻。現(xiàn)在的世界是書多文多,但讀少用少;那時是書少文少,可精讀細研。那本鉛印手訂的《語言學文選》我仍保留著,油墨已淡去,但讀書時留下的道道深淺畫痕猶著。
那時培養(yǎng)研究生有“游學”制,學生在選題或初稿寫成時,要到全國各地去游學,拜師訪友,求學問道。記得在開學典禮上,學校主管研究生培養(yǎng)工作的“最高領導”研究生科何科長大聲鼓勵,研究生就是科學研究的國家隊,就是要做最好的研究。游學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首次游學就是先生親自帶我們出行,許多前輩都是那次見到的。我們到北大燕園拜見了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到申城拜見了華東師大史存直先生、宗延虎先生,以及復旦的張世祿先生、胡裕樹先生。我的學位論文是《爾雅·釋詁》同義詞研究,還專赴濟南拜見了山東大學的殷孟倫先生,在武漢則是找遍三鎮(zhèn)才找到丁忱先生。丁忱是我國新時期培養(yǎng)的第一位訓詁學博士,他的學位論文就是《爾雅》研究。那時我們是年輕后生,外出走動,興奮有余,細心不足,加上從小受家人關心多,主動關心別人少,游學路上對先生細心照料甚少。先生與我們一起乘火車硬座,卻不知提前排隊給先生買張臥票。初夏之際到北京,住北大南門外的海淀賓館,那時還沒有標間,都是十幾二十人的大通鋪。先生從小生長在廣東,不習慣北方浴池子,那幾天硬是熬著未浴,現(xiàn)想起來真是慚愧有加。先生就是以如此的用心與付出,把我們一步步引入語言學殿堂。
重讀先生論著,對先生的學術生涯與貢獻有了更多認識,也倍感栽培之恩深重。先生溫文儒雅,語無高調,話無速句。對做學問,先生總是說把自己的觀點論證清楚就好了,不要去與別人爭辯,別人說的道理可能你沒體會到,容易產(chǎn)生誤解;你說得有道理,別人自會理解的。先生教而不厲,導而不拘,正是這種于己嚴,對人寬的培養(yǎng),為我們在今后發(fā)展中獲得了更大的學術動力與空間。在編輯過程中,得到世勛學兄的甚多指點,也得到同門諸位手足的關心,大家囑我寫點什么。意難盡表,文當有止,先生與師母的健康長壽,當為弟子們之最盼。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