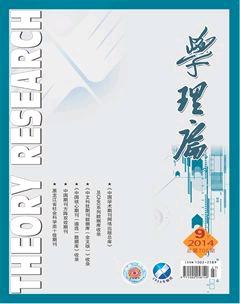略論七三一部隊背蔭河實驗場
陳鵬
摘 要:侵華日軍第731部隊在黑龍江省五常背蔭河地區盤踞時期,修建了大型實驗基地,用來進行活體實驗和細菌實驗。這座龐大的實驗基地和那些秘密實驗隨著731部隊的敗退和歷史實物的銷毀,漸漸遠離了人們的視野。力圖通過解析文獻、對比證詞,努力還原背蔭河實驗場的某些真相。考證背蔭河實驗場的秘密實驗情況,以及實驗場暴動的時間、逃出人數、逃亡路線等問題。從而,進一步證實731部隊在背蔭河地區的活動,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空前的傷害。
關鍵詞:731部隊;背蔭河;活體實驗
中圖分類號:K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27-0121-02
黑龍江省五常市背蔭河鎮是731部隊實驗場的所在地。背蔭河地區于乾隆九年(1744年)建屯,1932年隨著拉濱鐵路(哈爾濱至拉法的鐵路)的建設,背蔭河村迅速成為鐵路沿線的一座小鎮,并建有火車站。731部隊經過細致考察選中背蔭河建立實驗場,首先,這里交通便利,距離哈爾濱較近,可以提供大量實驗器材、給養物資;其次,該地遠離人口密集地區,一旦發生烈性細菌傳染,能夠迅速采取措施,便于控制;第三,當地聚集著相當數量的人口和資源,可以提供廉價的勞力;最后,由于地理位置相對偏僻,731部隊進行實驗具有很好的隱蔽性。
一、背蔭河實驗場的秘密
背蔭河實驗場俗稱“中馬城”,1933年實驗場建成后,一個名叫中馬的日軍大尉負責管理這座實驗場,因而得名。731部隊搞細菌實驗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中馬城”就顯得十分神秘和恐怖了。
“中馬城”非常堅固,規模龐大、管理嚴格、形同要塞。據史料記載:它(指“中馬城”)周圍有三米多高的圍墻,墻頂上架設著兩道鐵絲網,中間還有一道高壓電網,圍墻四角各修筑一座堅固的炮樓,安設兩盞活動式探照燈;墻外挖有兩米半寬的護城壕。它的正門朝北,一座吊橋橫跨在護城壕上;吊橋里側是兩扇黑漆城門,由兩名日本兵持槍把守……火車經過背蔭河站,也要將車窗簾布放下,嚴禁旅客向車外看望。這里的日軍人員禁止一切外出;禁止使用日本真名,即使用化名同國內家屬通信也得經過關東軍司令部審查[1]7。另有文獻記載:到冬天這里已經建成一座陰森巨大的城堡,南北450米,東西230米,共約103500平方米。內外三層套院,三道圍墻,一道護城壕。墻高5米,上安刺線電網,外墻四角相望,各修碉堡型炮臺一座,上置探照燈,壕深5米,寬10米。城周只留西和西南兩個門,西門直通火車站,西南門直通機場,鐵路專用線也從此進入[2]。該文獻講述的“中馬城”與前述有所不同,但均反映了“中馬城”戒備森嚴、堅固龐大的特點。從此,這座與世隔絕的城堡成為731部隊活體實驗的場所。
“中馬城”是731部隊前身“加茂部隊”進行活體實驗的秘密基地,這一點毋庸置疑。在日本人的記載里能夠充分證明。遠藤三郎當時是關東軍作戰參謀,他的日記里描述了他的所見所聞,1933年11月16日他來到背蔭河,親眼見證了兩項活體實驗。“午前八點半,同安達大佐、立花中佐一起到交通中隊(即‘中馬城的代稱)內的實驗場視察實驗的情況。”
按第二班擔當毒氣、毒液實驗,第一班負責電氣實驗分工。分別各用兩名“共黨匪”(日軍對被充作實驗對象的抗日人員的誣稱)進行實驗。使用碳酰氯在毒氣室經過5分鐘實驗,引起嚴重肺炎者,迄至昨日依然生存,而被注射15毫克氰酸化合物者,約20分鐘后即失去知覺。經通過兩萬伏高壓電流進行多次實驗者,仍未使其致死,最后注射毒液始將其殺死。第二個人,通過以五千伏高壓電流反復實驗,并未使其致死,最后連續接通電流數分鐘,始將其燒死。”[3]217-218這種殘忍的活體實驗是違背人類道德和良知的,731部隊從建立之初就開始從事這種罪惡行徑。遠藤三郎的另一篇日記里也記錄了他在背蔭河看到的情形:“被實驗者一個一個嚴密地關在柵欄里,把各種病原菌移植于人體內,觀察其病情的變化。”[3]222這里提到的“柵欄”當然就是監牢了,而那些被實驗者則像動物一樣接受悲慘的結局。
二、背蔭河實驗場的反抗與遷移
背蔭河實驗場的活體實驗需要大量活人作為實驗材料,然而,被實驗者們是不甘忍受這種命運安排的,他們是具有反抗精神的人,是爭取自由生活的人。
731部隊在背蔭河時期曾發生過一起越獄事件,也可以說是一次反抗731部隊暴行的斗爭。關于這次事件,由于時間久遠,事發突然,當事人的相繼離世,產生了多種說法。越獄的時間、逃出的人數、逃跑過程都有不同。首先是越獄時間問題,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有三種記載。第一,1933年說。持這種說法的有《日軍731部隊罪惡史》、《日本軍細菌戰》等著作。認為1933年中秋節是越獄的時間,文中都提到具體的日期是公歷9月30日,但查詢年歷可知1933年中秋節為公歷10月4日。此外這兩本書講述的內容十分相似,且沒有其他材料指出1933年越獄的說法。因此,這種說法存在疑點。第二,1934年說。此種說法是《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苦斗簡史》、《“滿洲第731部隊”罪惡史》等著作提出的。第一本書由馮仲云撰寫,馮仲云是東北抗聯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他曾與趙尚志在五常一帶率領抗聯第三軍反滿抗日,是那段歷史的見證人。他在“八一五”光復后,寫了一系列回憶文章,1946年將這些文章合編出版了《抗聯苦斗史》。該書明確指出1934年中秋節后,有十二名從“中馬城”逃出的人,投奔抗聯隊伍,馮仲云本人還接見他們,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第二本書是日本戰犯原秀夫、荻原英夫等人合寫,愛新覺羅·溥杰翻譯的回憶錄。該書也說1934年發生了越獄事件。這兩本書都是重要的史料,但是他們說的具體時間不一致,《抗聯苦斗史》中說是中秋節后三天,而日方的回憶錄指出1934年夏季的某日。歷法上,中秋節的時候夏季已過,天氣轉涼,當屬秋季。這一點或許是當事人記憶有誤。1934年說的總體時間還是可靠的,因為這兩本書的作者是在不同地點,從不同角度回憶此事,并且是不同國籍,不存在重復對方說法的可能。第三,1936年說。這種說法存于《背蔭河畔設魔窟》(見《偽滿史料叢書?日偽暴行》一書)、《五常縣志》及背蔭河村民的口述記錄等史料。按照《背蔭河畔設魔窟》一文所說1936年農歷八月二十七日夜10時許發生了越獄。這個時間十分準確,甚至精準到幾點鐘,在當時條件下是如何確認時間呢?作者是怎樣知道這個時間呢?可惜,沒有佐證,令人懷疑其時間的真實性。《五常縣志》的記載是“1936年被關押在監獄的抗聯三軍戰士,發起暴動,打死日軍崗哨,用敵人的炸藥炸毀了倉庫,然后越墻逃跑。”[4]這里顯然把越獄事件和“中馬城”“爆炸”事件混為一談了,因為這兩件事的發生時間不一致,“爆炸”事件是越獄事件之后一年發生的。當地村民王濱回憶說“中馬城”建成三四年后,發生了越獄事件,那天是中秋節,背蔭河的百姓還聽到了槍聲。①按時間推算大約是1936年,而1936年的中秋節恰恰是公歷9月30日,同前面論述的1933年中秋節錯誤的公歷時間吻合。這樣可以證明兩種說法或是一對一錯,或是兩個都錯。1936年說的正確與否,可以從日本人供述里得到佐證。日本戰犯荻原英夫供認他的舅父瓜生榮二曾于1933年起在背蔭河“中馬城”工作了一年六個月,瓜生榮二的職務是看守,他的頭部受過傷,留下傷疤,變成禿頭。受傷的原因恰恰是被實驗者越獄時打傷的[5]。這段證詞表明瓜生榮二極有可能親歷過那次越獄事件,并且受傷。而瓜生榮二遲至1934年或1935年已經離開背蔭河,因此,1936年說存疑極大。由于時隔久遠,而當地村民回憶的時間出現偏差是不可避免。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判斷這次越獄事件的時間發生在1934年中秋節期間的可能性最大。
關于這次越獄事件的人數和逃跑過程也有不同的說法。根據馮仲云《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苦斗簡史》的說法是20多人逃出,4人因體力不支死在路上,其余的人走散了,剩下的12人投奔抗聯隊伍。有的文章說是14人逃出,2人跑到八家子屯,被當地自衛團殺死1人,抓回“中馬城”1人。其余12人中,有5人跑到新發屯,7人跑到陳家崗(應為程家崗)[1]12。還有的說是18人逃出,其中3人跑到八家子屯,被自衛團殺死1人,送回“中馬城”2人。5人逃往程家崗屯,5人逃往新發屯,2人跑到閻家洼子屯。另有3人因體力不支,饑寒交迫死在路上。總計12人獲救[6]。此外,按照當地參加營救越獄人員的老鄉吳澤民的說法有30多人。①據吳澤民說他家住在程家崗,他和哥哥一次就看到30多名從“中馬城”逃出的人,并且幫助10多個人砸開了腳鐐子。在當時的危急時刻30多人聚在一起逃跑,顯然目標太大,風險太大。逃出“中馬城”后,眾人一定是化整為零,各奔東西,才能獲得最大的逃生機會。
綜上所述,背蔭河越獄事件逃出獲救的人數至少是12人,而逃出的總人數目前沒有定論,估計在20人左右。
據當地村民回憶,這次越獄后的第二年,“中馬城”發生了“爆炸”事件。①一說是日軍不慎引爆,一說是抗聯隊伍炸的。這兩次事件引起了石井四郎的不安和焦慮,他意識到背蔭河地區不適合進行秘密實驗,開始了搬遷行動。
“爆炸”事件后,石井四郎以“失火”為由,陸續撤走了研究人員和各種設備,轉移至哈爾濱或日本本土。“中馬城”的建筑材料也被運走或賣給當地百姓,此后,經過七十多年的建設和改造,“中馬城”消失得沒了蹤影。
參考文獻:
[1]韓曉,辛培林.日軍731部隊罪惡史[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
[2]偽滿史料叢書·日偽暴行[G].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561.
[3][日]遠藤三郎.將軍的遺言——遠藤三郎日記[G]//黑龍江文史資料第24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
[4]五常縣志[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638.
[5]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第五卷·細菌戰與毒氣戰[G].北京:中華書局,1989:37.
[6]金成民.日本軍細菌戰[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