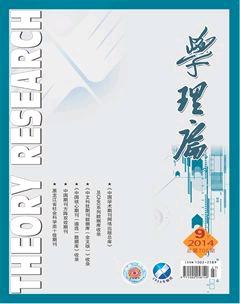金庸小說人物形象摭談
董峻玉
摘 要:金庸小說不僅創造眾多人物形象,更巧妙地安排著這些形象的不斷發展與變化,使讀者在故事情節的起伏跌宕中體會人物本身的感情變化。其總體特征表現在:理想和現實的沖突,并不斷地朝現實人生與現實人格發展。通過對這些過程的分析,掌握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才能更好地了解金庸的創作之路和心理歷程。
關鍵詞:金庸;形象變化;理想;現實
中圖分類號:I2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27-0134-02
人們喜歡金庸的小說,不能不說與金庸塑造的這些膾炙人口的人物形象有著莫大的關系。有的角色為人們所喜愛、敬佩,有的則被人們所厭惡、唾棄,還有更多的角色讓人們感到矛盾、不解。人們之所以會對金庸筆下的人物有如此復雜的理解,就是因為金庸筆下的人物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無論是對比他的十五部作品里人物之間的性格差異,還是比較同一部作品中人物不同時期的性格表現,都有著一定的變化。正是這些變化,才使得人物形象越來越豐滿,給讀者留下的印象也越來越深刻。
金庸小說創作一般被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55年創作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開始,到《碧血劍》、“射雕三部曲”前兩部(《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雪山飛狐》、《鴛鴦刀》、《白馬嘯西風》、《飛狐外傳》;第二階段從《倚天屠龍記》(“射雕三部曲”第三部)、《連城訣》、《天龍八部》、《俠客行》、《越女劍》到《笑傲江湖》;第三階段則是他的封筆之作1972年的《鹿鼎記》。共計十五部,前后時間跨度達20年之久。每一個階段,金庸小說中的人物都體現出了不同的人格類型與審美傾向。
一、郭靖——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
《射雕英雄傳》是金庸早期武俠小說的代表作,著名的“金學”研究者陳墨將“傻小子”郭靖劃為金庸早期小說主人公的代表,儒俠中的俠之大者。但是,郭靖并不是一開始就是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他四歲方才開口說話,終身不善言辭,在柯鎮惡等江南六怪的眼里,郭靖簡直就如孔子門下的宰予那樣“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污”。而帶給郭靖成長為一代大俠轉機的卻是全真教掌門人馬鈺,他因材施教,教郭靖正宗的全真派內功心法。而后,郭靖的中原之行遇見黃蓉,是黃蓉指點江山歷史風物、教他文化藝術經典,然后再巧妙安排他拜師學藝、提升他的武功境界,不僅見識了天下武林中最杰出的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武功,而且在此之外還研習了老頑童的獨創絕技和“九陰真經”,由此步入一流高手的境界也就合情合理、絲絲入扣了。
而郭靖樹立“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思想,則是跟他的武功一樣,一點一滴積聚至充盈處,最后水到渠成。起初,他最大的責任不過是為父親報仇,為七位師父爭面子,好好打贏楊康;但是隨著經歷與見識的增長,他漸漸體會到正邪之間的斗爭,國家大事及民間疾苦需要有人承擔解救。郭靖在意外情形之下領導了蒙古人抗金戰事,經過這番經歷,隨后又經過極艱難的考驗反省,最終成為以“為國為民”為終生目標的仁義禮智信諸德兼備的合乎大眾審美的理想人物。郭靖的人生經歷不是太平坦,但他的內心經歷似乎過于順利,他從未對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產生過懷疑,從而過于理想化,缺乏真實的感人力量。“郭靖的性格雖豐滿,卻總是在一個層面上不同角度的展開,從而少了后期《天龍八部》中蕭峰那樣的深度和震撼力。”[1]
金庸自己也承認,他早期作品不成熟,演繹痕跡過重,缺乏真實感。對人物形象的批判歌頌上也更多停留在政治、倫理層次,從而缺乏對復雜人性的深刻挖掘。儒家正統文化向來倡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己復禮”、“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國家利益高于個人價值的觀念,人們長期在這種思想影響下,也就更習慣于欣賞一切合乎倫理、將社會使命作為個人最高價值來完成的具有儒家風范的完美英雄形象。當然,這并不是說金庸為了商業利益一味地追隨大眾,而是這種儒家英雄典范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也影響著在儒家文化下成長的作者自己。這一方面是因為武俠小說作為大眾消費品,必須符合大眾的期待視野和審美理想。另一方面也與當時激昂向上的時代背景與年輕的作者對理想人格的完美想象有關。總之,這一階段的人物形象過于理想化。
二、令狐沖:“笑傲江湖”的“個體本位英雄”
讀過《笑傲江湖》的人都知道令狐沖是具有真真的叛逆,對整個的儒、道、佛合流的傳統文化進行徹底反叛的一個人。“令狐沖聰明伶俐且機智幽默,隨和可親而又深情固執,熱情沖動又天真可愛,馬虎隨便又自由不羈,其形象的價值更體現在于他所逐漸領會并表現出來的,與政治霸權、文化專制環境和傳統冰炭不能同爐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即‘笑傲江湖——的現代人文精神。”[2]365
一出場,令狐沖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問題“青年”。作為名門正派的弟子,尤其是作為武林中鼎鼎有名的君子劍岳不群的開山大弟子,令狐沖的行為作風非但不能成為同門之中的模范表率,反而明顯有損一般正派子弟的聲譽。但后來田伯光上華山邀他去見儀琳,引出風清揚前輩。風清揚出現的意義不僅僅是教會令狐沖天下無雙的“獨孤九劍”,更在于教育他如何了解自己、相信自己、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這對于令狐沖的人生轉折,無意起到了關鍵性的影響作用。不僅使他成為一位新的武學高手,更使他成為一種自主的新人。
令狐沖蔑視禮法,拒絕權勢,追求自由。當《笑傲江湖》中幾乎人人都在爭權奪勢,希望“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時,令狐沖卻在很多次能得到權勢的時候將其拱手送出。恒山派掌門定閑師太被岳不群在少林寺暗算,彌留之際,將掌門之職托付給他,他遵守承諾,幫恒山派渡過了最困難的時期,但之后他就毅然地將“權力”卸下交給了別人。
這一時期的金庸不再滿足于追求道德倫理的完善,而是著力挖掘真誠、自由、坦率的人性之美,與沉溺于物質和權力不能自拔、不擇手段的人性之惡相抗爭。因此令狐沖不再是如郭靖般的為國為民的儒之大俠,而總是在游蕩與流浪中尋找自由的機會,實現自己的價值,表現自己的天性。這一時期的金庸在理想與現實的沖突面前進行著艱難的抉擇與痛苦的掙扎。
三、韋小寶:求生、縱欲的“反俠”形象
金庸曾這樣說:“《鹿鼎記》和我以前的武俠小說完全不同,是故意的。一個作者不應當總是重復自己的風格和形式,要盡可能地嘗試一些新的創造。”武俠小說寧可無武,不可無俠,而韋小寶則非但無俠,更是一個人格卑微的小人。金庸解釋說:“小說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說的主要任務是創作人物;好人、壞人、有缺點的好人、有優點的壞人等等,都可以寫。在康熙時代的中國,有韋小寶那樣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寫一個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這樣的典型。”[3]1819
與其他小說主人公不一樣,韋小寶沒有生產于浪漫色彩濃郁的傳奇環境里,而是生活在窮困的現實環境之中。生父不詳,母親是揚州城麗春院的妓女而且人老色衰、生存不易,韋小寶的日子肯定不好過,輕蔑、辱罵甚至毆打都是家常便飯,生存一直都是迫切的問題。與生存相比,尊嚴、情誼、獨立的人格等都顯得微不足道,為了生存,他不擇手段。比如他將江湖人所不齒的各種“下三爛”手段都使出來過:石灰撒眼、床下鉆襠、桌下砍腳、胯下捏陰等等,搞得江湖漢子茅十八都對他無可奈何之極;再比如他對康熙的“忠”是有限的,對天地會的“義”也是有限的,對于蘇荃等七位夫人的“情”更是有限的,一旦生命不保,他就要開溜了。小說最后,他正是為了保命而“告老還鄉”。
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最后發展成為反清復明的天地會總舵主大英雄陳近南的得意弟子、清王朝康熙皇帝的心腹,官至遠征大將軍,爵至一等的鹿鼎公,大名士顧黃呂查四人甚至病急亂投醫要輔佐他當皇帝,其形象的變化之大、之奇不禁讓人目瞪口呆。這樣的傳奇經歷不只為滿足讀者對武俠小說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與世人皆有的英雄夢的追逐,更多的是作者借這個不合理想的反俠人物來表達他對荒誕虛無的現實世界、似是而非的價值判斷、失落茫然的精神信仰的深刻反諷與思考,這無不體現了金庸的現代意識與精英意識。這一方面與作者人到中老年更加平和、淡然的創作心態密切相關;另一方面金庸借鑒了西方文藝理論塑造人物的方法,做到了本土與西方相結合、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現實與想象相結合。正如金庸自己把后期作品比前期更好的原因歸于思想與技巧的進步一樣。可見,這一時期的金庸逐漸偏離理想向現實人生挺進。
縱觀金庸小說的創作道路,也通過上文代表人物的分析,不難發現金庸筆下的一系列主人公文化程度逐步偏低。從第一部書中的主角陳家洛是進士出身,到最后一部書中的主角韋小寶卻是出身妓院的市井小混混。這些主角,文化程度變低,卻顯得更加率真、質樸、真實。總之,這些人物的個性越來越突出,現實人性的表現越來越真實,人物的人格力量越來越弱,心理沖突越來越強烈,社會沖突也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不管是文化程度的逐漸偏低還是對傳統大俠形象的漸漸偏離,都體現了金庸筆下的人物在現實與理想的沖突面前,越來越遠離理想,慢慢向現實人生靠攏。
金庸小說創作,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每一階段都有著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不同的是理想和現實所占份額的多少而已。早期的小說創作受到傳統武俠小說及儒家正統入世、救世思想的影響,主人公形象多正面、光明、富有偉大的人格力量和領袖魅力。正是在這樣的思想下,金庸小說開始不斷展現理想與現實的沖突,突破理想不斷地朝現實人生及現實人格、現實人物形象方面發展,其主人公形象越來越遠離理想的正統大俠了。到了1965年,金庸小說創作已經完全是一片新的武俠天地,金庸借鑒了西方文藝理論塑造人物的方法,突破了對理想人格的探索,以日常化、世俗化的人物形象對政治、歷史、文化、道德、文明等方面的負面因素進行了深刻獨特的審視和批判,藝術形式日漸完滿,從而完成了金庸武俠小說創作歷程從暢銷書到經典的飛躍。
參考文獻:
[1]趙華,蔡安延.試論金庸小說人格理想的轉變及意義[J].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4):53-57.
[2]陳墨.陳墨評金庸——人性金庸[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
[3]金庸.鹿鼎記[M].廣州:廣州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