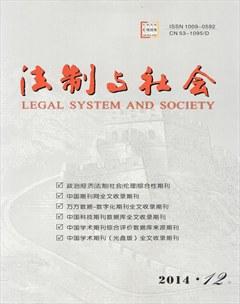涉眾型經濟犯罪防控對策研究
摘 要 通過對重慶2010-2012三年來的立案情況進行分析,重慶市涉眾型經濟犯罪呈現出外在形式合法化、犯罪手段新穎化、受害群體相對固定化、犯罪行為半公開化、犯罪定性復雜化等“五化”特征,并據此提出了提前預警強化預防、強化協同加強管控、完善法制提高犯罪成本等防控對策。
關鍵詞 涉眾型 經濟犯罪 防控對策
基金項目: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委托項目:法制與公民意識教育與重慶市教委人文社科項目“經濟法視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的部分成果。
作者簡介:吳安新,副教授,重慶文理學院教務處。
中圖分類號:D924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文章編號:1009-0592(2014)12-065-02
涉眾型經濟犯罪通常是指受害群眾在三十人以上的經濟犯罪案件,常見類型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組織、領導傳銷,集資詐騙,合同詐騙,非法經營,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銷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生產銷售假藥等。
根據這個標準,重慶市2010 -2012年共立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183起,主要分布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三個領域,涉案金額48億余元,參與人員9萬余人。其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105起,涉案金額約31億元,分別占涉眾型案件總量的57.4%和64.6%;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49起,涉案金額約15億元,分別占總量的26.8%和31.2%;立集資詐騙29起,涉案金額約2億元,分別占總量的15.8%和4.2%。從年度來看,2010年共立48件,破案45件,涉案人數不過2417人,涉案金額9600多萬;2011年立案40件,破案34件,涉案人數8427人,涉案金額8000多萬;2012年立案95件,破案68件,涉案人數8萬余人,涉案金額近46.8億元。本文基于這三年的案件進行剖析,嘗試找出解決之道。
一、重慶市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突出特點
根據分析,重慶市的涉眾型經濟犯罪呈現出五大特點:
(一)外在形式合法化
不法嫌疑人為了獲得受害人信任,通常利用工商部門對企業成立僅進行形式審查的制度設計,依法成立相應規模的公司,完備公司成立各項手續,披上合法的外衣,并具有正規、完備的稅務登記證明,然后通過招聘,齊整部門、崗位。再輔之以相應的“光環”包裝,諸如PS與名人甚至國家領導人的合影照片,或聘請名人做廣告,辦理投保、公證、律師見證(在實踐中,很多受害人并不清楚見證與擔保的區別,把見證等同于擔保而上當受騙)等表面合法的形式,從而騙取受害人信任。比如重慶“億霖公司非法經營16.8億元”案中,就曾聘請葛優等明星為其代言。
(二)犯罪手段手法新穎化
不法分子不斷創新犯罪手法,如林業部門剛推出林權證制度,馬上就有不法分子運用林權證以售后托管方式開展非法經營;還有的利用炒境外黃金期貨、現貨之概念,開展非法經營或是合同詐騙;有的利用售后返租、合作開發、投資商鋪等名義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這些形式,往往最早發軔或“創新”于經濟發達城市,如北京、深圳、上海甚至境外等地,然后蔓延成盛行。犯罪嫌疑人還常利用信息不對稱,特別是相關部門對新手法的認識不充分有誤差之際,做完就走,該類嫌疑人通常以原來涉嫌犯罪公司而未被公安機關成功打擊的員工居多。
(三)受害群體相對固定化
涉眾型犯罪中的受害群體同一犯罪類型的相對固定,如傳銷侵害對象往往是家庭境況較差且不安于現狀的人,通常以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居多;非法集資、集資詐騙、銷售未上市公司股票、擅自發型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的侵害對象則主要針對的是具有一定經濟實力且投資愿望較強的退休老人或者家庭婦女,也包括部分急于尋找生活來源的下崗工人(通常通過借貸來進行投資);投資黃金等現貨期貨等非法經營行為針對的是有一定資產,具有一定程度的炒股經驗的中青年人為主。
(四)犯罪行為半公開化
涉眾性的一個“眾”字便意味著該類行為必然具有相當的公開性,不然不成其為“眾”。該類行為實踐中往往通過報紙、網絡、電視媒體對公司業務進行大肆宣傳,甚至利用名人效應讓投資者確信投資回報的可行性;另外則是通過人與人之間信息相互傳遞進行宣傳,甚至會出現大規模組織客戶或向不特定群眾來宣傳公司業務等情況,這說明了其公開性。但該類犯罪還具有相當的隱蔽性,如江盈投資有限公司涉嫌合同詐騙案中,嫌疑人只在公司前期運作中出現甚至在組建公司中也是委托他人進行,法人代表、實際負責人都是聘用人員或者不相關人員的姓名,出現其本人的情況則使用的是假名,查處時身份的落實都是難點。這類犯罪涉案資金通常采取現金交易模式,或者采取迅速提現轉移到其他無關聯或用他人身份開具的賬戶,造成追贓難。
(五)犯罪定性復雜化
涉眾型經濟犯罪定性難度越發凸顯復雜化,比如該類犯罪一般都披有合法公司的外衣,而其經營的整個過程不過是為了其實施犯罪行為的一個有利“外殼”或“幌子”,但實際操盤人只是個人行為,在定性上應剝去其“外殼”認定其為個人犯罪,但是實踐中由于案件復雜性以及證據的獲取等方面具有復雜性等因素,往往以公司行為論之,導致犯罪分子得不到應有之查處。另外,域外取證的限制有時也使得案件定性復雜化,如公安部查處的香港中天黃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涉嫌非法經營8000余億元案中,盡管明知該公司負責人采取內盤交易模式進行操作,客戶資金也被用于公司其他事項,其行為極有可能涉嫌合同詐騙,但是由于其交易網站設立在境外,取證難導致了只能以現有證據認定非法經營。
二、涉眾型經濟犯罪防控對策
結合重慶市涉眾型經濟犯罪所凸顯的特點進行剖析后,我們認為對該類犯罪的防控主要可通過如下幾個對策。
(一) 提前預警強化預防
對涉眾型經濟犯罪,有效的預防是主要渠道,通過對該類犯罪的通常特點及時進行針對性分析并給予恰當的犯罪預警,則能有效的遏制并減少該類犯罪。我們認為,有效的預防可從三個方面進行著手:
一是建立涉眾型經濟犯罪通報制度,即公檢法機關及時向社會通報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查辦、審判等處理情況,并對頻繁出現的涉眾型犯罪手法、危害,典型案例呈現等方式通過電視、報紙、網絡、宣傳欄等渠道進行披露,從而震懾潛在的犯罪分子,并給公眾以有效的提醒,以達到預防和警示的目的。如果說通報、披露制度主要是一種對普通公眾的一種提醒,那么對犯罪罪名特定、對象基本固定、犯罪場所相對集中的情況,進行針對性的宣傳,如在公眾休閑的廣場對老年人開展宣傳,在勞務市場對農民工開展宣傳等等。
二是對“高危人群、高危行業,高危樓宇”進行重點預防與布控。高危人群是指受害群眾、業務員、經理、公司負責人等積極參與人員,對之應建立涉嫌涉眾型犯罪的專門數據庫,無論其在這類犯罪中處在的地位如何,均一律打指紋、抽血樣、明確身份庫,并適時在該群體中物色信息員及特情。高危行業,主要是容易發生該類犯罪的行業,如股權投資公司、投資咨詢公司、投資管理公司等,做到定期走訪摸排,了解公司的股東、法定代表人,實際負責人,公司經營模式,公司人員架構及工作人員身份情況,及早進行風險判斷;高危樓宇,即容易發生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樓宇,除對樓宇中的高危行業進行走訪摸排外,應在樓宇的物業中,經營者中物建信息員,及時了解情況。
三是積極引導群眾謹慎投資、合理投資,老百姓逐漸富裕后,多又思考讓手里的錢的“更有收益”,正是這種心理才會被不法分子利用,預防也應從此著手,即必須讓民眾清楚知曉高收益必然伴隨著高風險,特別是不規范的投資活動失敗風險更大。另外還應該著手于讓其資金有方向可投,故金融機構應進一步豐富理財產品,開發不同的理財產品應對不同人群之需求,讓民間投資有放心路徑;由于在投資領域的違法犯罪常常是因為是信息不對稱所引發,讓民眾獲知投資方面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則尤為關鍵。對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問題,“應適當放松民間金融管制,打破金融壟斷,鼓勵民營資本參與正規金融”,但需要規范化、公開化,讓資本在陽光下行為。
(二)強化協同從嚴監管
除了預防之外,還需要部門間協同監管有效擠壓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空間。
一是要加大對金融領域的監管力度。涉眾型經濟犯罪,多集中于金融領域,而且該類型犯罪的頻繁爆發,更是暴露出目前金融機構的存在問題,例如一些金融機構出于“家丑不外揚”的思想往往將本系統內的經濟犯罪僅僅視為違規違紀問題加以處理,在一定程度上放縱了犯罪,建議政府金融辦與銀監會有效聯動,對轄區內金融機構進行不定時不定期的巡視與監管,及時發現并移送異常資金流動線索。
二是工商行政機關及稅務部門應加強對轄區內公司的日常監管,尤其對新成立的投資咨詢、股權投資、生物科技等公司情況進行主動摸排,掌握其實際經營地址、實際經營模式,并及時通報公安機關備案或處置;另一方面是嚴防抽逃出資、做假賬、偷稅漏稅行為發生。
三是強化對行政機關責任的追究。相關職能部門的聯動,需要在強化其主動性的基礎上給以一定的責任機制,才能真正推動其認真履職。相關職能部門在辦理業務時接觸到、發現的犯罪線索,應當及時反映或移送,檢察院應針對拒不移交刑事案件的加大責任追究力度,以確保相關職能部門認真履職、積極履責。
四是強化對相關交易信息的協同監管。“在市場交易活動中,交易雙方是根據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制定決策的,而決策的正確性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所掌握的信息數量與質量。”正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很多犯罪嫌疑人才利用民眾信息匱乏但又想獲利的心理,那么監管部門應該協同,從涉眾型經濟犯罪所依托的“空殼”入手,嚴格規定相關類型企業應向民眾公開提供真實、全面的信息及公開信息的渠道。一則減少民眾及監管方的搜集信息的成本,并利于信息甄別;二則能避免“逆向選擇”,讓合法企業少受“劣幣驅逐良幣”之困。
(三)完善法律提高犯罪成本
一在舉證責任和量刑數額方面應進行適時調整。鑒于涉眾型經濟犯罪復雜性,以及查證的困難性上,致使很多此類犯罪難以查清,甚至不能以其本罪進行定罪,所以在此類犯罪中,我們主張舉證責任倒置,這可加大犯罪嫌疑人犯罪成本,也有利于立案及定罪。在實踐中我們采取了一些努力,也已經有了一些立法經驗,如2010年11月22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就在集資詐騙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如規定“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拒不交代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的”可以直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構成集資詐騙罪。這些規定在舉證責任上進行了變化,采取舉證責任倒置,從而可以讓偵查機關無法查清,而嫌疑人拒不交代資金走向或隱匿資金走向即可逃避集資詐騙定性只能以非法集資來定性的怪圈,也有效震懾了集資詐騙犯罪行為。
二是對“公眾”進行細致界定。涉眾型犯罪,首先要對公眾的界定進行完善,不然會導致認定上的困境。在目前的司法解釋中排除了“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在親友或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之情形,其它的則屬于本罪之范圍,那么“親友”的界定是非常關鍵的,但比較模糊的,如“親”是指血親、姻親?要界定到多少代際內等都需要進行明確。而“友”的界定更為復雜,司法解釋也沒有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在“友”的界定上應做限制性解釋,從嚴處理。對于“單位內部”也應該從嚴控制,應限定在獨立法人或同一合伙企業內,在實踐中常有地方政府為“發展”故向應本區域內的公務人員進行集資等情況,如果不進行一定的限制,會引發較為惡劣之影響。通常理解3人以上為“眾”,在個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司法解釋中規定以個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20萬以上或存款對象30人以上的,是入罪標準,但若僅吸收1-2人,就達到20萬以上,就很難入罪,若放縱,其惡性又較大,遇到這種情況,司法解釋上也應具體情況進行具體處理,對“眾”進行限制性的解釋。另外在“眾”的理解上通常界定在個人上,在我國實踐中,很多財產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尤其是在存款方面,受害人并不是單獨的個人,往往是受害人將本家庭之財產進行存入,所以在認定“眾”時應考慮這種社會現實。
參考文獻:
[1]柴艷茹.非法集資犯罪案件的偵查困境與偵防對策探析.犯罪研究.2013( 4).
[2]王俊豪.政府管制經濟學導論——基本理論及其在政府管制實踐中的應用.商務印書館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