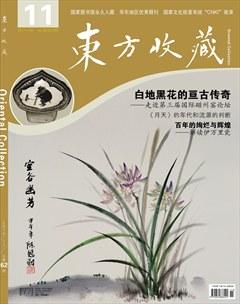瓷器方罍初探(下)



當(dāng)提及五十七種釉彩的具體品種時(shí),這位督陶官再次提到仿古禮器(括號(hào)內(nèi)分別注明的為現(xiàn)今名稱):
“廠內(nèi)所造各式釉水(色)、款項(xiàng)甚多不能備,茲擧其仿古採(cǎi)今宜於大小盤(pán)、碗、盅、碟、瓶、罍、尊、彝歲例貢御者五十七種,開(kāi)列於后以證大概:一仿鐵骨大觀釉(即仿官釉),有月白、粉青、大綠等三種。一仿鐵骨哥釉(即仿哥釉),有米色、粉青二種。一仿鐵骨無(wú)紋汝釉(即類天藍(lán)釉)……一仿嘉窯青花。一仿成化淡描青花……”(注14)。
由上可知,雍正年間,御窯廠確實(shí)燒造過(guò)摹古的“罍、尊、彝”,而且,系奉命燒制!由此還可以想象,藏于上博的底落“大清雍正年制”官款的那件“雍正青花饕餮紋方瓶”,應(yīng)該就是當(dāng)年景德鎮(zhèn)“裝桶解京以備賞用”的“瓶、罍、罎、尊、彝等上色琢器”中的一件。此物雖說(shuō)是目前絕無(wú)僅有,卻印證了史料記載,彌足珍貴。
方罍的主體紋
“雍正青花饕餮紋方瓶”和“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尊”,無(wú)論其外觀造型,還是紋樣裝飾,是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同商周青銅方罍最為接近的瓷質(zhì)方罍。當(dāng)然,不排除還有未被發(fā)現(xiàn)的瓷方罍!
上述兩器,最抓人眼球的當(dāng)屬通體的饕餮紋。
饕餮紋之稱謂,并不是古時(shí)就有,而是金石學(xué)興起時(shí),由宋人起名的。夏、商、周三代饕餮紋,圖案結(jié)構(gòu)嚴(yán)謹(jǐn),繪作精巧,境界神秘,系古代人融合了自然界各種猛獸特征后,加以自己想象,甚至于幻想而形成的。由于饕餮紋經(jīng)常由動(dòng)物的目、鼻、眉、耳、口、角等幾個(gè)獨(dú)立部分組成,故又稱獸面紋。由于獸面紋大多顯得夸張又巨大,便常被古代藝術(shù)家用以作玉器和青銅器上的主紋飾,借以將人們引入到一個(gè)神秘的藝術(shù)境地。饕餮紋中還有多種變形動(dòng)物圖案:有的像龍(夔)、像虎、像熊;有的像牛、像羊、像鹿;還有的像鳥(niǎo)、像鳳、像魚(yú),是商周青銅器上固有的極為重要裝飾。
雍正青花饕餮紋方瓶(罍),除在肩部的窄面兩側(cè)各貼塑青花銜環(huán)鋪首外,通體繪青花紋飾五組:盤(pán)口與底邊,設(shè)對(duì)應(yīng)的絞連紋;頸肩部自上而下飾由云雷紋組合而成的蕉葉紋,并與一組絞連紋相連;腹部的主體紋為饕餮紋,紋樣規(guī)整、對(duì)稱、清晰;下腹至脛部分別繪絞連紋與變形鉤連雷紋。商周饕餮紋大多以動(dòng)物的面目形象出現(xiàn),該罍主體上的獸面紋,形似飛禽之雙目,亦即“獸目交連紋”。雙目之間,用兩豎線條作鼻梁,直通額頂。畫(huà)面上可見(jiàn),目紋所占比例較大,十分醒目。目紋周邊遍飾大小不等、粗細(xì)不一的云雷紋,使整器不乏商周青銅罍的神采與韻味。比照古器可知,雍正之青花饕餮紋方瓶(罍)系模擬商代晚期不帶出戟的鳥(niǎo)紋銅方罍(圖14)。兩者盡管在底部存在明顯差別,但它們的形制與饕餮紋飾,都顯得簡(jiǎn)潔、明快。作為雍正瓷器,就該是這樣的風(fēng)格。否則,不屬雍正瓷。何況,雍正仿古器“仿古而不擬古,不追求逼真而追求神似”(注15)。
“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罍”高33.3厘米,口徑11.2—10厘米,腹徑17.3—15厘米,足徑13—11.3厘米。長(zhǎng)方侈口,高頸微束,溜肩、圓腹下收,長(zhǎng)方高圈足外撇。全器以云雷紋為地,饕餮紋樣系“鳥(niǎo)獸合體紋”。口以下至方足,塑八道出戟,一如青銅罍每面的中線及四角出棱,并以青花雙鉤填色之縱橫短線,在出戟上作分隔,形成青白相間似齒狀的紋飾;肩的窄面兩側(cè),塑對(duì)稱夔龍耳。器身從上至下飾青花紋飾六組,青花純正清幽:唇口繪一周渦形云雷紋,底邊淡描二條弦紋線,紋線在似有似無(wú)之間;頸部飾二組鳥(niǎo)獸合體紋,寬面一組動(dòng)物紋形似虎,窄面一組似由解體的獸面紋組成;肩的寬面于中心處畫(huà)對(duì)稱獸頭,造型頗像動(dòng)物臉譜,兩側(cè)輔以象紋,窄面塑獸耳,形似夔龍,并于夔龍耳兩側(cè)飾似象的動(dòng)物紋,紋樣與窄面相類,但象紋又有變化、身與腹大塊露白;腹部主干紋樣由三層鳥(niǎo)獸合體紋組成,且采取色彩對(duì)比手法,構(gòu)成新穎、極具神秘感的饕餮紋樣。公允地說(shuō),乾隆青花方罍地紋(云雷紋)密布,裝飾飽滿,主干紋樣豐富,較目前所有經(jīng)著錄之商周銅方罍(圖15)似乎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甚或與“皿方罍”(圖16)可媲美!
上述兩方罍,紋樣一為簡(jiǎn)約,一為繁復(fù),卻都呈現(xiàn)一種超脫塵世的神秘氣氛和力量,這便是清代雍、乾兩朝瓷方罍的藝術(shù)魅力。
瓷器文化
比對(duì)瓷方罍與銅方罍,不難發(fā)現(xiàn),兩者在造型上,區(qū)別其實(shí)并不大,唯在頸部,瓷方罍作了加長(zhǎng),并外撇成侈口,而商周銅方罍均為直口、直頸。
原因何在?是因?yàn)閮烧叩牟馁|(zhì)與功用不同。
在商周,青銅罍?zhǔn)峭跏液唾F族在盛大宴會(huì)上必備的酒器。故形體碩大,雕琢精美,雄渾莊重。然而歷史發(fā)展到清代,盛酒器早已今非昔比。彼一時(shí)的青銅罍業(yè)已成古董、成擺設(shè),其功能早就被輕巧又能顯示國(guó)家實(shí)力的瓷器所取代。中國(guó)人所發(fā)明的瓷器,歷來(lái)受到統(tǒng)治階層和文人墨客的重視。也因此,中國(guó)的經(jīng)典瓷器,無(wú)不承載著國(guó)家當(dāng)時(shí)在思想文化、人文心態(tài)和綜合國(guó)力等方面的諸多信息,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載體。從某種角度講,“瓷器文化”所反映的就是“中國(guó)文化”。而且,國(guó)運(yùn)昌盛,瓷器燒造就精美。
“瓷器”與國(guó)力與文化息息相關(guān)?讓人匪夷所思,而事實(shí)就是如此。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生產(chǎn)的瓷器,之所以明顯優(yōu)于清中期之嘉慶、道光與清晚期咸豐、同治、光緒瓷器,原因是康雍乾三朝為盛世,加上皇帝對(duì)瓷器喜好。
中國(guó)瓷器什么朝代的最好?世界公認(rèn)為宋代。
事實(shí)亦確實(shí)如此。中國(guó)最好的瓷器來(lái)自于宋代:除官、哥、汝、定、鈞五大名窯外,還有美不勝收的龍泉窯、耀州窯、磁州窯、吉州窯、景德鎮(zhèn)窯等等。原因就因?yàn)樯鐣?huì)安定富庶[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便是見(jiàn)證:這幅寫(xiě)實(shí)風(fēng)俗畫(huà),讓人清晰可見(jiàn)汴京市民“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xí)鼓舞,斑白之老,不識(shí)干戈(《東京夢(mèng)華錄》)”的富裕生活]、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達(dá)(中國(guó)對(duì)人類巨大貢獻(xiàn)首推“四大發(fā)明”,即造紙術(shù)、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shù),宋人占了三項(xiàng))、文化事業(yè)興旺(以文學(xué)而論:聞名中華的“唐宋散文八大家”,六家為宋朝人;以哲學(xué)而論,則有宋“程朱理學(xué)”,對(duì)中國(guó)人的思想道德觀念起到重大影響)和經(jīng)濟(jì)繁榮昌盛。所以,美國(guó)人羅茲·墨菲在他所著的《亞洲史》中說(shuō),宋朝是“中國(guó)的黃金時(shí)代”,是中國(guó)“一個(gè)前所未見(jiàn)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和文化繁盛期”。英國(guó)歷史學(xué)家湯因比說(shuō):“如果讓我選擇,我愿意活在中國(guó)的宋朝。”最近有資料稱,“南宋后期,中國(guó)(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經(jīng)濟(jì)總量占到全球的75%以上。而今日之中國(guó),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經(jīng)濟(jì)總量?jī)H為4%”。可見(jiàn)宋時(shí)中國(guó)富得流油,經(jīng)濟(jì)實(shí)力乃世界一流。故宋代瓷器最佳,且獨(dú)步于天下。
時(shí)代不同了,器物的形制與裝飾亦隨之變化。再說(shuō),瓷器燒造,原本就有自己的套路。更何況雍、乾兩朝所造青花罍,目的為懷舊,為賞玩,是著眼于當(dāng)下、反映當(dāng)朝文化與審美意識(shí)的產(chǎn)物。因而,時(shí)至清朝,瓷質(zhì)方罍無(wú)須帶蓋,尺寸好似不必那般高大,亦理所當(dāng)然應(yīng)該變直口為撇口,以增添上下呼應(yīng)的韻律。而青銅罍之口部與底邊,原本是不帶裝飾的。為此,雍正方罍上下分別加繪云雷紋,以提高觀賞性。乾隆方罍則更妙,底邊輕描二根極其淡雅的青花弦紋作對(duì)應(yīng),線條又在似有似無(wú)之間:說(shuō)有、便有,說(shuō)沒(méi)有、便沒(méi)有,老古董上反正是沒(méi)有的。上述變動(dòng),皆系服從于藝術(shù)需要,要想表達(dá)的乃是統(tǒng)治者與士大夫的審美情趣、藝術(shù)品位以及當(dāng)朝的人文心態(tài)。
從雍、乾兩方罍的形與紋來(lái)看,兩朝各有各的風(fēng)貌。雍正方罍尺寸不大,瓷質(zhì)瑩潔,造型簡(jiǎn)約,講究線條,以秀麗柔和為美,故選擇商代不帶扉棱的青銅罍為摹本(參見(jiàn)圖14),干凈、利落地顯現(xiàn)古罍之形,并透露出雍正瓷特有的雋秀之美。乾隆方罍形制繁復(fù),器身遍飾青花云雷紋,裝飾不厭其煩層層疊加,系選擇既帶有扉棱,又屬主體紋樣中最為復(fù)雜的商周青銅罍為摹本(圖17)。這兩者的簡(jiǎn)潔與繁復(fù),實(shí)際上是兩位皇帝的藝術(shù)品位與性格使然。
然而,單就仿古而言,不能不說(shuō),乾隆方罍鬼斧神工,極具富麗,令人驚嘆!
乾隆方罍之母本
乾隆仿古最核心的部分,是對(duì)商周特別是對(duì)西周青銅禮器的模仿,“或仿其典型形制,如鼎、尊……或仿其典型紋飾,如獸面紋、夔紋、回紋等經(jīng)轉(zhuǎn)化后所形成的構(gòu)圖元素”。而“青銅禮器是正統(tǒng)思想中理想的禮樂(lè)制度的象征,是古典美學(xué)的凝聚”。所以,崇尚漢文化的乾隆皇帝,懷著“圣王時(shí)代的一種自矜,也是對(duì)古典貴族工藝典范的一種膜拜”,沉湎于商周禮器仿制,且樂(lè)其不疲。
若不算上蓋,青銅方罍的器身高度,通常在30—40厘米上下。譬如,現(xiàn)藏于美國(guó)弗利爾藝術(shù)館的西周青銅方罍(圖18),高度為34.1厘米;1978年于遼寧喀左小波汰溝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登屰方罍”(參見(jiàn)圖15),通高51.3厘米,取掉蓋,也就30多厘米。而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罍高33.3厘米,大小高度與中小型銅罍相仿。然而此高度,恰恰在瓷器的“黃金”尺寸之例,不能不說(shuō)是主觀上的故意。有關(guān)瓷器尺寸,舊古玩業(yè)有句行話,“立件高不盈尺為上”。
細(xì)細(xì)解讀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罍,則讓人肅然起敬!其形貌與特征,居然同商代晚期的青銅“亞方罍”十分相像。目前所知,青銅“亞方罍”有兩件,一件藏于上海博物館(參見(jiàn)圖17);一件由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圖19)。上博“亞方罍”來(lái)自民間,器身高53厘米,重29.68千克,失蓋。北京故宮“亞方罍”系清宮舊藏,連蓋通高60.8厘米,重20.8千克。此一大一小兩“亞方罍”,因精致瑰麗,皆屬國(guó)家一級(jí)文物。尤其上博“亞方罍”,盡管失蓋,其所享盛名,卻不在有蓋銅方罍之下。“關(guān)于其著錄頗多,其中包括紐約1980年出版《偉大的中國(guó)青銅時(shí)代》(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之圖版27號(hào)。”這享譽(yù),顯然與其繁密精細(xì)又極具氣派的裝飾,以及其高度僅次于“皿方罍”不無(wú)關(guān)系。
按常規(guī),清宮舊藏被用以作瓷方罍藍(lán)本的幾率,理當(dāng)高于流散于宮外的同類器物。可乾隆青花方罍的造型,偏偏與上博“亞方罍”十分接近。例如,北京故宮“亞方罍”肩部窄面兩側(cè)的獸首耳是銜環(huán)的。而乾隆方罍肩部窄面兩側(cè)的夔龍耳則無(wú)環(huán),同上博青銅“亞方罍”如出一轍。乾隆方罍器身八出戟之形式,亦同上博“亞方罍”之八條扉棱非常相似。不可思議的還有其腹部主干紋樣,似乎比“亞方罍”的饕餮紋更見(jiàn)復(fù)雜,竟然同“皿方罍”腹部的主干紋樣相類。“皿方罍”銷(xiāo)聲匿跡了2000年,乾隆方罍又如何同“方罍之王”掛鉤?驚訝之余,不得不欽佩乾隆時(shí)期金石學(xué)的精到。
清三代摹古
“仿古瓷作為一種特殊的陶瓷文化,其歷史由來(lái)已久。傳統(tǒng)意義上的仿古瓷最初萌芽于兩宋時(shí)期(注16)。”當(dāng)初,基于金石學(xué)興起,五大名窯之官、哥、汝、定、鈞,出現(xiàn)了不少模擬商周青銅器的杰作。一些地方窯場(chǎng)如龍泉窯、景德鎮(zhèn)窯等,包括元明時(shí)期,亦不乏刻意仿古者。至清代,崇古蔚然成風(fēng),質(zhì)量當(dāng)數(shù)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優(yōu)。
清朝自康熙、雍正起,御窯廠不惜工本從事對(duì)前朝名作的模仿。康熙一朝,喜聞樂(lè)見(jiàn)的是一些以明代器物為摹本的仿古瓷,這與清政府當(dāng)時(shí)所采取的民族和諧政策有關(guān),即:各民族要團(tuán)結(jié),滿人要向漢人學(xué)文化。以致清早期的官窯與民窯瓷器,爭(zhēng)相模仿明朝紋樣,連款識(shí)(包括官窯)亦以明朝的為榮為時(shí)尚。雍正年間,宮中經(jīng)常出示所藏宋瓷供御器廠作母本,致仿宋五大名窯之物惟妙惟肖。此時(shí),“官窯款識(shí)大多為青花篆書(shū),無(wú)款之器,為有意摹古”。乾隆時(shí)期,對(duì)古物的研究更為重視,并在器型與紋飾上,把握得更為準(zhǔn)確。可是,若想要在這三者中評(píng)出最優(yōu)者,則非常難,只能說(shuō),康雍乾三朝,各有千秋!
康熙模仿明代宣德、成化器相當(dāng)有水準(zhǔn)(圖20),所仿嘉靖、萬(wàn)歷青花“與真無(wú)二”,后世極難予以區(qū)別。筆者在實(shí)際操作過(guò)程中,感觸頗深:所謂成弘不分、嘉萬(wàn)不分,其實(shí),均不難加以界定,唯康熙模仿嘉靖萬(wàn)歷青花瓷,須費(fèi)時(shí)地仔細(xì)辨認(rèn)。
雍正皇帝學(xué)養(yǎng)深醇,對(duì)色釉瓷興味盎然,又有創(chuàng)新,故集歷代顏色釉之大成。其燒造仿宋官窯的“那種頗能體現(xiàn)‘紫口鐵足效果、在御窯廠被稱為‘鐵骨大觀”的青釉器,極為成功。試舉一例:臺(tái)北故宮有件“北宋官窯粉青釉筆筒”(圖21),于筆筒足底,鐫刻有乾隆皇帝御題詩(shī):“缾椀官窯亦恒見(jiàn),筆筒一握見(jiàn)殊常,宣和書(shū)畫(huà)曾經(jīng)伴,南渡兵戈幸未亡。火氣全消文氣蔚,今人如挹古人芳,不安銅膽插花卉,拈筆吟當(dāng)字字香。”詩(shī)末署“乾隆癸卯新正御題”紀(jì)年銘(乾隆四十八年),并落“古香”和“太璞”兩枚鈐印。此筆筒系宮中舊物、且底面有乾隆御制詩(shī)為證,于是,對(duì)其為北宋之物,兩岸故宮專家深信不疑(參見(jiàn)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編著《宋官窯特展》之圖62,1996年版)。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中國(guó)筆筒出現(xiàn)的年代并不早,亦即宋朝沒(méi)有筆筒,御題的所謂“宣和書(shū)畫(huà)曾經(jīng)伴”是不存在的!中國(guó)最早的筆筒產(chǎn)生于明末崇禎(注17),至今不足500年。那么,是誰(shuí)作了誤斷?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乾隆爺“走眼”了,亦即雍正皇帝把自己的兒子給蒙了。從這件子虛烏有的宋官窯粉青釉筆筒上可見(jiàn),雍正盡管“仿古而不擬古(形),不追求逼真而追求神似”,但其所仿宋五大名窯之神似,無(wú)疑已達(dá)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特別是在仿鐵骨大觀釉(即仿官釉)上,后朝無(wú)可望其項(xiàng)背,連儒雅博古的乾隆皇帝都真假莫辨!
乾隆制瓷,追求精、奇、巧。所仿古瓷,精于考證,又講究逼真,無(wú)論是工藝技巧還是裝飾藝術(shù),都達(dá)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地步。前述仿商周青銅罍,是為一例。至此,筆者還需累贅一筆。君不見(jiàn),乾隆方罍還有二個(gè)醒目處:即肩部寬面中心(圖22)和器腹主干紋樣之中部,分別以青花繪制一組對(duì)稱的獸面紋圖案。紋樣以留白形式繪畫(huà),形象奇特、極難描述。借鑒銅方罍(圖23)后方醒悟,肩部中心一組,系表示銅方罍之立體獸頭;腹體中部之偏下一組,則象征立體的獸首鋬。在器物肩部設(shè)獸頭鋪首,玩瓷者已見(jiàn)多不怪。又為何要在腹部偏下的中心位置,再添加一獸首鋬?原來(lái),“由于銅罍本身體量頗大,盛滿酒鬯后更為沉重,難以提用,而在下腹部設(shè)一鋬,可將木棍插入其中或系繩,便于將銅罍提起,以傾倒酒水。”乾隆摹古之細(xì)膩,以及追求形似與神似方面之一絲不茍,于此可見(jiàn)一斑。
談?wù)勀」糯煞Q謂
摹古瓷的稱謂,今人常以自己的主觀思維,強(qiáng)加于古人,這似乎已成為當(dāng)今陶瓷界的通病。興許有的因?yàn)榇媪肯∩伲瑹o(wú)可比照,實(shí)屬無(wú)奈,姑且為之。譬如上述稱瓶、稱尊。有的則明顯不靠譜,較器物的本源相去甚遠(yuǎn),譬如中國(guó)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宋官窯投壺”,被定名為“宋官窯貫耳瓶(圖24)”。另一件不同形制的“宋哥窯貫耳壺”,則被北京故宮博物院冠以“宋哥窯貫耳八方扁瓶(圖25)”之稱!實(shí)際上,宋代的崇古器,皆講究考證,它們有本有源,原本就有各自的稱謂,今人妄加新意,實(shí)屬畫(huà)蛇添足!
在稱謂上,相對(duì)而言,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的做法就比較規(guī)范比較嚴(yán)謹(jǐn)。例如臺(tái)北故宮編輯委員會(huì)編《宋官窯特展》中的143件宋官窯器,所用稱謂,“全部沿用故宮博物院原典藏名稱”,即:以“北宋官窯(圖26)、南宋修內(nèi)司官窯(圖27)、南宋郊?jí)鹿俑G(圖28),三個(gè)名稱展示”(注18)。而且,造型亦按原典藏名稱。顯然,臺(tái)北故宮的做法是科學(xué)的、合乎歷史客觀。事實(shí)上,今人的所有研究,只為解讀和破譯古物所承載的歷史信息,以弘揚(yáng)中華傳統(tǒng)文化。為此,起碼要做的亦是最容易辦到的便是在稱謂上,不可有違古物的初衷與本意。
有關(guān)古代青銅器稱謂,青銅器專家馬承源在《中國(guó)青銅器》一書(shū)中解釋道,古時(shí),“金文中稱禮器為尊彝”,尊與彝一樣,原是成組禮器的共稱,宋朝之后開(kāi)始專指一類器物。“現(xiàn)今所稱的尊,約定俗成,乃沿用宋人的定名”(注19)。那么,仿古既然是以宋代或商周之物為摹擬對(duì)象,其冠名當(dāng)然亦應(yīng)以古之稱謂為妥!這樣做,至少在稱謂上,可讓仿古瓷與原件掛鉤,進(jìn)而同古物所處的時(shí)代接軌。
中國(guó)青銅器,尤其是“商周的青銅冶鑄藝術(shù),是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中國(guó)瓷器,尤其是宋代五大名窯,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chǎn)中特別耀眼的瑰寶。悠久的歷史,璀璨的文化,使我們這個(gè)民族有了物質(zhì)與精神上的雙重財(cái)富。搞鑒賞,悟其味,大抵也是繼承精神財(cái)富的一個(gè)方面。古人云:“名不辨物,則鑒識(shí)不顯”。鑒識(shí)不顯,則偏離精神。所以,稱謂亦是十分重要的。
商周青銅器的銘文
回頭再看前述的嘉德拍品“鳳鳥(niǎo)紋青花方彝”(參見(jiàn)本刊上期文章的圖5)。
慶寬家族稱之為“方彝”,顯而易見(jiàn),此稱謂十分到位,開(kāi)門(mén)見(jiàn)山溯源至商周。但該方彝的生產(chǎn)年代則不會(huì)在康熙至雍正年間,當(dāng)在乾隆二十年以后,亦即《西清古鑒》四十卷完成之后。康、雍時(shí)期,由于缺乏金石學(xué)的研究基礎(chǔ),對(duì)于古方彝的認(rèn)知,當(dāng)時(shí)還達(dá)不到如此精深程度。唯在乾隆朝,因金石學(xué)崛起,才使摹商周之瓷,進(jìn)入了絕妙境界。所以,《古銅器考》一書(shū)稱贊當(dāng)時(shí)制瓷業(yè)是“有陶以來(lái),未有今日之美備”。許之衡《飲流齋說(shuō)瓷》(民國(guó)版)則贊美道“至乾隆,精巧之至,幾于鬼斧神工”。因而,但凡把一件仿古器物,能塑造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其本身就是佐證,而時(shí)代大致在乾隆或乾隆以后。
關(guān)于青銅器銘文,商代早期,曾出現(xiàn)過(guò)個(gè)別幾例,既像文字又像花紋的銘文。商代中期,銘文才逐漸發(fā)展起來(lái)。但字?jǐn)?shù)一般只有一、兩個(gè)字,多則四、五個(gè)字,“直到殷末,沒(méi)有超過(guò)五十個(gè)字的銘文,數(shù)十字的銘文也僅有幾例”。至西周,青銅器銘文大發(fā)展,“不論銘文的性質(zhì)、內(nèi)容、形式、數(shù)量,甚或書(shū)體等方面,都較前有了很大的變化。”(注20)
上述方罍、方彝,在其四方高圈足的外底釉下, (下轉(zhuǎn)頁(yè))
(上接頁(yè))皆落有青花銘文。雍正方罍走的是御窯廠瓷器生產(chǎn)的常規(guī)套路,故在方足底下署的是三行六字篆書(shū)官窯款識(shí)(參見(jiàn)圖4)。乾隆方罍和方彝的銘文,皆以金文形式書(shū)寫(xiě)。乾隆方罍足底青花銘,頗似“符號(hào)”(參見(jiàn)圖3—3)。這類符號(hào)為青銅器上特有,稱之為“徽記”,作用是為標(biāo)識(shí)器主。“徽記又有繁簡(jiǎn)兩式”。簡(jiǎn)式徽記,僅為作器者的族徽或族名、官名、私名,如“天”、“史”、“婦好”、“應(yīng)公”等。“這種格式多見(jiàn)于商代,周初也有發(fā)現(xiàn)”。繁式徽記,“除了有作器者的稱謂以外,還有敘述語(yǔ),以標(biāo)明器名、用途、存放地點(diǎn)等”(注21)。乾隆方彝底足釉下的數(shù)十字銘文(參見(jiàn)圖5),便是繁式徽記的一種。繁式徽記通常流行于西周至春秋早期。
對(duì)于乾隆方罍的簡(jiǎn)式銘文,見(jiàn)多識(shí)廣的鑒定專家李彥君考證其為“桂”或“林”,系家族姓氏。而乾隆方彝底面以青花留白書(shū)寫(xiě)的數(shù)十字金文,據(jù)藏家查證,與其大致相類的一段銘文,見(jiàn)著錄于《景朱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shí)》,系源自商周時(shí)期青銅“黹方彝”。由此可知,乾隆朝之摹古,不僅僅形似、紋似,甚至還細(xì)膩到利用商周青銅器特有的“徽記”,來(lái)追溯古物之源與本,這在中國(guó)仿古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由于清代雍正與乾隆兩朝對(duì)宋代五大名窯和“具有古韻的銅器”的重視,遂將仿古瓷的燒造,引領(lǐng)到一個(gè)新的歷史高度。而乾隆《西清古鑒》的纂修及《西清續(xù)鑒》、《寧壽鑒古》的編撰,不但促進(jìn)了乾嘉時(shí)期訓(xùn)詁學(xué)的發(fā)展和考據(jù)之風(fēng)的盛行,還使得景德鎮(zhèn)窯摹古器,在文化內(nèi)涵、造型變化和工藝設(shè)計(jì)等方面得到了進(jìn)一步完善,最終致乾隆及此后的仿商周之器,達(dá)到了一個(gè)新的極致。
上述三件實(shí)物,便是有清一代仿商周之器和考據(jù)之風(fēng)盛行的物證。
注釋:
[14]: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P288-289
[15]:張麗《清宮銅器制造考——以雍、乾二朝為例》,《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
[16]:張佳《我國(guó)仿古瓷的定義及發(fā)展史》,《景德鎮(zhèn)陶瓷》 2012年第05期
[17]:高阿申《明清瓷制筆筒鑒識(shí)》,《收藏》2003年第11期
[18]: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huì)編《宋官窯特展》,1989年版
[19]、[20]、[21]:《中國(guó)青銅器》馬承源主編,上海古籍書(shū)店、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