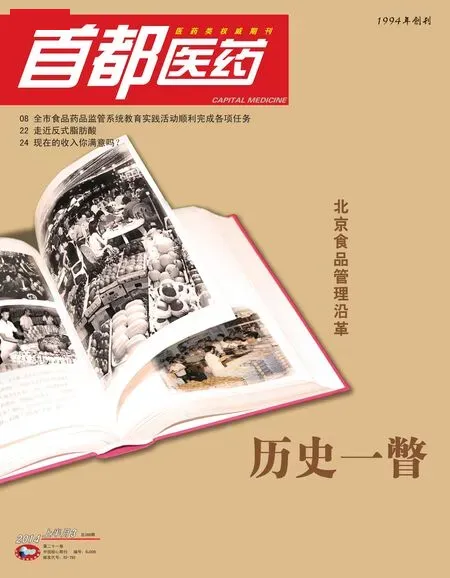鹵煮火燒的由來與傳承
■本刊記者 趙一帆
鹵煮火燒對于北京人來說,實在是再熟悉不過了。鹵煮火燒,又名鹵煮小腸,簡稱鹵煮,是北京的一道傳統(tǒng)小吃,已有百年歷史。其主要原料是豬腸、豬肺、豬肝和豆腐,用大鍋鹵制后,與戧面火燒一同切塊,再放入適量的腐乳、韭菜花、辣椒油、蒜泥、醋、香菜等等,從大鍋里舀一勺老湯往碗里一澆,頓時香氣四溢,待火燒變軟后即可食用。一碗熱騰騰的鹵煮端上來,火燒、豆腐、肺頭都吸足了湯汁,火燒透而不黏,肉爛而不糟,其中味道最厚重的還是小腸,酥軟、濃郁,滿口脂香。就是這樣一道早已街知巷聞的傳統(tǒng)美食,曾幾何時也是只有皇帝才能享受的“御膳”,而鹵煮火燒的由來還要從一位廚師講起。

張東官和“蘇造肉”
相傳,乾隆45年(1780年),皇帝巡視南方,下榻于揚州安瀾園陳元龍家中。據(jù)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弟媳——愛新覺羅·溥杰的夫人嵯娥浩所著的《食在宮廷》中描述,當時,陳府家廚張東官烹制的菜肴很受乾隆帝的喜愛,后張東官便隨乾隆入宮。深知乾隆喜愛厚味之物,張東官就用五花肉加丁香、官桂、甘草、砂仁、桂皮、仁、肉桂等藥料烹制出一道葷菜供膳,乾隆品嘗之后大加贊賞。因張東官是蘇州人,用這種配制香料煮成的肉湯就被稱為“蘇造湯”,其肉就是“蘇造肉”,宮內(nèi)還曾設(shè)了“蘇造局”。《清稗類鈔》有記載:“宮中于五月食椴木鉸……又有蘇造糕、蘇造醬諸物,相傳孝全后生長吳中,親自仿造,故以名之。”
隨著時間的推移,蘇造肉的做法也逐漸傳到了民間。那個年代,出售蘇造肉的小販在東華門外設(shè)攤,專為朝廷官員做早點。
清光緒年間,京東一些農(nóng)戶在農(nóng)閑時就制賣蘇造肉。舊社會用五花肉煮制的蘇造肉成本太高,普通百姓根本吃不起,他們就用價格低廉的豬頭肉代替五花肉,同時加入價格更加低廉的豬下水一同燉制。
京城內(nèi),在紫禁城外西北角城隍廟,有一個專門賣蘇造肉和火燒的鋪子,掌柜姓周,其燒法獨得祖?zhèn)髦兀鉅€湯醇,在北京獨一無二。除了店伙計挑著擔出去賣給南北長街、南北池子、后門一帶住戶外,這鋪子還專門做給宮里太監(jiān)吃。不但如此,宣統(tǒng)帝溥儀和宮中后妃等也都愛吃蘇造肉,御膳房不做,都到鋪子中去取。周掌柜的侄子后來也進宮當了蘇拉(滿語,即宮中打雜),又升作溥儀的隨侍。《燕都小食品雜詠》中有一首贊嘆“蘇造肉”的詩:“蘇造肥鮮飽志饞,火燒湯漬肉來嵌。縱然人稱膩,一臠膏油已滿衫。”并注說:“蘇造肉者,以長條肥肉,醬汁燉之極爛,其味極厚,并將火燒同煮鍋中,買者多以肉嵌火燒內(nèi)食之。”
民國時期,蘇造肉以什剎海一帶的幾家飯館和東安市場的“景泉居”最有名氣。至于蘇造肉是如何演變成如今的鹵煮火燒,故事還要追溯到清光緒年間。
無奈之舉成一方美食
河北三河縣有陳兆恩、陳世榮父子,以制售蘇造肉為生。因五花肉成本過高,出于無奈,父子二人就嘗試用豬頭肉煮,之后又加上了豬下水,沿街擺攤出售。而真正使鹵煮火燒名聲鵲起,還是從第三代傳人——陳玉田開始的。陳玉田從十幾歲起就幫父親陳世榮料理鹵煮小攤,并且邊幫父親打雜,邊認真學習、研究。很快,有心的陳玉田就學會了鹵煮火燒的制作技術(shù),并且推陳出新、精益求精,把鹵煮火燒做得越來越地道。
新中國成立前,陳玉田曾在珠市口、前門、天橋及東單、西單牌樓等處設(shè)攤經(jīng)營鹵煮火燒,最著名的還得數(shù)陳玉田設(shè)在珠市口(現(xiàn)豐澤園飯莊旁)的攤位,因緊鄰戲院,一些唱戲的名角在散戲后都喜歡來一碗陳師傅做的鹵煮火燒當宵夜。京劇大師梅蘭芳、張君秋、譚富英等都曾是陳玉田攤前的常客,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也好這口兒。在經(jīng)營上,陳玉田待人和氣、童叟無欺,有錢沒錢到攤前都能吃上一口兒,落下了一個好人緣。久而久之,陳玉田的鹵煮攤便被越來越多的食客認可,并譽送雅號——小腸陳。

▲陳玉田打破了“傳男不傳女”的規(guī)矩,把制作鹵煮火燒的絕活兒傳給了女兒陳秀芳
在鼎盛時期,陳家的鹵煮作坊也形同于現(xiàn)在的連鎖店,加工作坊設(shè)在虎坊橋老宅內(nèi)。每天要加工上百斤豬下水及豆腐、火燒,到下午再由商販領(lǐng)出半成品,到京城各繁華街道設(shè)攤。“小腸陳”的鹵煮火燒逐漸深得百姓喜愛,在京城名聲大振,成就一方美食。
變革與傳承
1956年“公私合營”后,陳玉田的買賣并入了宣武飲食公司(現(xiàn)北京翔達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國營飯館,在南城的南橫街燕新飯館內(nèi)專門制作鹵煮火燒。當時,京城經(jīng)營鹵煮火燒的只有兩三家,陳師傅精湛的手藝和好人緣使得南橫街的燕新飯館非常有名,加上鹵煮的獨特風味和經(jīng)濟實惠的特點,生意異常火爆,每天都有不少人光顧。雖然當時只是在晚飯時間營業(yè),可一到下午三四點鐘就有人拿著鍋、盆到店門口排隊。其中,有遠道而來的食客,也有周邊的鄰里街坊,排隊買小腸陳的鹵煮火燒成為當時南城的一景兒。
據(jù)一位當年曾親眼目睹陳玉田老人在鹵湯鍋前忙碌的食客回憶:那鍋熱浪翻滾的鹵湯,在陳老先生看來與剛從自來水管子接的涼水并無二致。只見他不時把手探將進去,隨心所欲地在鍋中撈取各種鹵品,其動作之泰然,神態(tài)之平靜,令人嘆為觀止。鹵品置于案頭,切法已在心中:火燒井字落刃,豆腐三角給刀,小腸花樣分斷,肺頭剁爛筋腦……一陣眼花繚亂之后,各種鹵品已然分門別類碼放碗中。最后,陳老爺子舀起一勺濃濃的鹵湯,慢慢淋落在層層疊疊的鹵品之上,開始為自己的“作品”殺青。“可別小看澆湯,這里面學問大了。湯少了,鹵品不能入味吃來味道太淡;湯多了,將‘貨’淹沒,又丟了碗中風景。”這位食客說道。
買賣雖然火爆,但陳玉田在近古稀之年時,還尚未有人接班。北京的主流媒體也曾就鹵煮火燒這一北京名優(yōu)小吃品種面臨無人繼承的尷尬進行過報道,呼吁培養(yǎng)接班人,使這一傳統(tǒng)風味不致失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guān)注。一時間,來了不少人學藝,但最終都因臟、累、熱、苦等困難一一離開,陳玉田也不得不在這家國營餐館一直干到75歲才退休。
雖然陳玉田辦了退休手續(xù)隱居家中,但也時常因這一名吃從此消失而感到遺憾。1989年,他與女兒——“小腸陳”第四代傳人陳秀芳在南橫街中段租用了一間30多平米的門臉房,重新領(lǐng)取了營業(yè)執(zhí)照,亮出了“小腸陳”的牌子。新店剛一開業(yè)便門庭若市,無奈店鋪面積有限,常令眾食客不得不在門外等候,即便如此,慕名而來的食客還是絡(luò)繹不絕。

▲當年陳玉田經(jīng)營鹵煮火燒的燕新飯館

▲“小腸陳”在南橫街的舊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