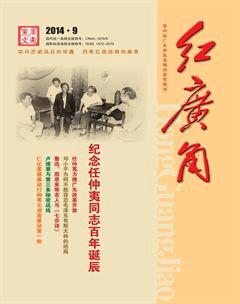中國共產黨在人大設立黨組的前前后后
徐高峰
黨組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重要制度之一,也是當代中國政治體系中一個頗具特色的具體制度。在人大設立黨組,是中國共產黨加強對國家權力機關領導的一項重要舉措。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60周年之際,梳理中國共產黨在人大設立黨組的演變過程,可以從一個側面管窺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脈絡,并從中探求中國共產黨在依法執政原理下建構與人民代表大會關系模式的知識和啟迪。
一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國家政權正式形成,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共產黨與國家關系的正式形成,中國共產黨從一個爭取政權的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如何實現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如何處理黨與國家政權機關的關系,就成為擺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建國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將中國共產黨與國家政權的關系確定為,“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將成立的人民政協作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之下。”①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提出“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手里”,即把權力集中于黨中央。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由人民政協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擁有立法權、選舉權和決議權。在政協的全國委員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中,中共黨員都只占少數。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196人,非中共黨員133人;常務委員會44人,非中共黨員27人。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最高國家司法機關與最高國家軍事機關的“四位一體”,其中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由它任命的政務院、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是民主聯合政府,從人員構成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6位副主席中有三位非中共人士,56名委員中有27人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顯然中共中央不能像對待下級黨組織那樣,直接對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會和中國人民政府委員會發號施令。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國家政權處于初創時期,國家政權還不健全,整個來說也比較薄弱。中共國產黨在處理執政黨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系時,既努力避免黨直接指揮國家機關的工作,又努力尋找執政黨有效領導國家,貫徹執政黨意志的有效途徑。為此,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內組織中國共產黨黨委會的決定》和《關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內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組的決定》,指出黨的領導是通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在政權機關擔任公職的黨員發揮作用來實現的。如果把對國家的領導作用看作是黨直接執掌政權,管理國家,實際上就否定了國家政權機關的職能。據此,中共中央決定在政務院設立黨組,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署成立聯合黨組;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擔任負責工作的黨員中間不設黨組,而由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當時毛澤東作為中央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同時也兼任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對全國政協工作進行直接領導,并對有關的匯報請示親自予以批示。
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大會通過的《憲法》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定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閉會期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來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大部分權力。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也在努力強化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組織領導。這也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和背景有關。從1953年起,為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和社會主義過渡的需要,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人對政府工作的領導大大加強,要求“今后政府工作中的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并經過中央討論和決定或批準后,始終執行”②,并取消了由周恩來任書記的國務院黨組干事會和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干事會,改變了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對政府工作領導弱化的局面,但此后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和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弊端也逐漸形成。自1954年我國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后,中國共產黨直接指揮國家權力機關工作的形式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沒有發生變化。在這種形勢下,黨也在努力強化對人大機關的組織領導。1955年4月,經中共中共批準,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改名為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1956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成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張蘇任黨組書記。
1956年9月,黨的八大黨章對黨組的任務作了具體的規定。指出,在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領導機關中,凡是有擔任負責工作的黨員三人以上的,就應當成立黨組。黨組的任務是在這些組織中負責實現黨的政策和決議,加強同非黨干部的團結,密切同群眾的聯系,鞏固黨和國家的法律,同官僚主義作斗爭。八大黨章還特別規定,黨組必須在一切問題上服從相當的黨的委員會的領導。但是由于八大以后黨內政治生活逐步不正常,黨的一元化領導和黨委的權力集中日益嚴重,八大關于黨組的規定在實踐中并沒有堅持下去。從1957年下半年之后,在近10年的時間內,全國人大和人大常委會會議不能按時召開,人大工作基本上處于一種“徒有虛名,而無其實”的狀態,很難發揮什么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的工作機構和人員也不斷削減,1957年前工作人員為365人,1959年只剩下100人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僅保留一個名義,完全失去了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踢開黨委鬧革命理論的引導下,黨委的作用發揮都成了問題,更不用說黨組了。1966年7月7月,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第二十三次會議,這也是本屆人大常委會的最后一次會議。之后,在長達8年零6個月的時間內,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沒有舉行一次會議。1969年4月通過的九大黨章和1973年8月通過的十大黨章都刪除了關于黨組的條款和規定。直到1975年1月,在毛澤東支持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才得以召開,并通過了1975年憲法。1975年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權力機關”。四屆人大只召開了一次會議,由它產生的常委會也只召開了兩次會議,除了通過特赦決定和幾個任命事項外,沒有決定其他重大問題。但畢竟四屆人大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才開始恢復工作,使我國的政治體制正常化向前邁進了一步。endprint
二
“文革”結束以后,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1977年黨的十一大黨章又恢復了有關黨組的規定,不過這一規定比起八大黨章的規定要簡單得多,僅規定:“在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中,應設立黨組。中央一級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黨組成員由黨中央指定。地方各級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黨組成員由相當的黨委指定。”十一大閉會以后,中央和地方各級國家機關及人民團體中又普遍設立了黨組。1978年3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產生了以葉劍英為委員長的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5月,中共中央設立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以葉劍英為黨組書記,吳德為黨組副書記。與1956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相比,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的規格顯然更高。同時,決定設置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黨組。這是因為,五屆全國人大成立之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沒有成立專門委員會,只是成立了民族、法案、預算、代表資格審查4個委員會,工作人員最多的是辦公廳,約100人。設置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黨組,加強了黨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工作的組織領導。
同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公報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③作為對公報這一要求的回應,1979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成立由80多人組成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1983年改為法制工作委員會),彭真任主任,胡喬木等10人任副主任,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有史以來首次設立的協助常委會立法的工作機構。同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黨組。顯然成立這一黨組,與黨中央加強對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修改憲法工作的領導有關。
1982年9月通過的十二大黨章對黨組作了黨執政以來最完備的表述。十二大黨章第九章專論黨組,對執政條件下黨組設立的原則、黨組的任務、黨組與黨委的關系等問題有了一個明確清晰的表述。1982年制定的《憲法》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并規定了“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社會團體、各企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十二大后的六屆全國人大期間,中共中央繼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分別設立機關黨組和法制工作委員會兩個黨組,分別由秘書長、副秘書長和法工委主任、副主任組成,以加強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和立法工作的領導。這兩個黨組分別直接向中共中央負責和請示報告有關重大問題。當然這兩個黨組與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無論在性質、規格還是地位上都有很大區別,僅僅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1977年至1988年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一級沒有設立黨組。這與20世紀80年代初,中共中央實行“黨政分開”的執政思路有關。1980年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明確提出要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他說:“中央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不兼任政府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這樣做,有利于加強和改善中央的統一領導,有利于建立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管好政府職權范圍內的工作。”④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黨的十二大黨章提出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黨必須保證國家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1986年,鄧小平在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時進一步強調:“改革的內容,首先要黨政分開,解決黨如何善于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⑤1987年黨的十三大將《中國共產黨黨章》第四十六條中“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或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成立黨組”,改為“在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人民團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經選舉產生的領導機關中,可以成立黨組。”據此,黨組的地位和作用在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內的國家政府機關呈弱化趨勢。
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撤銷了黨組的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經濟組織、文化組織許多工作難以開展。特別是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之后,黨政分開的改革實踐基本上停了下來。1989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明確了黨組織的政治核心地位和領導作用。按照這一要求,七屆全國人大后,全國人大常委會恢復設立黨組,由委員長、中共黨員副委員長和秘書長組成,黨組書記由委員長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受中共中央領導,主要職責是:就常委會行使職權中的重大問題向黨中央請示報告;保證黨中央的決策的貫徹落實。黨組根據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由黨組書記召集和主持。隨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的陸續產生和健全,中共中央又恢復設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相應撤銷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黨組和法工委黨組。
三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推進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的有機統一,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法治中國建設。1990年3月,江澤民在參加全國人大、政協“兩會”黨員負責同志會議講話中,對人大黨組作了全面論述。一方面,人大黨組必須接受黨的領導,建立和健全向同級黨委的請示報告制度,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人大工作中貫徹落實;另一方面,黨同政權機關的性質不同,職能不同,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也不同,黨不能代替人大行使國家權力,要善于通過人大黨組把黨的有關國家重大事務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志。黨的十四大黨章將黨組的設置及其任務確定為:“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可以成立黨組。黨組的任務,主要是負責實現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討論和決定本單位的重大問題,團結非黨干部和群眾,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指導機關和直屬單位黨組織的工作。”⑥黨的十五大通過的黨章完全繼承了十四大黨章有關黨組的性質、地位和基本任務的規定。
從黨的十二大到十三大,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委員長還沒有進入最高核心決策圈。以黨的十四大為標志,從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開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建立了相對穩定的集體學習、集體調研、集體決策制度,中國進入了中央集體領導體制的新階段。黨的十六大報告將這種制度概括為:“黨委在同級各種組織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獨立負責、步調一致地開展工作。”“按照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規范黨委與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的關系。”⑦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是通過黨對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來實現的,中國“集體領導制”逐漸完善鞏固。
與之相適應,按照十六大黨章對黨組的新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的任務較之以往,增加了黨組“發揮領導核心作用”的規定,并增加了“做好干部管理工作”的內容。這一修改顯然意味著更加強調黨組要承擔貫徹執行黨的政治意志、履行重大事項決策、干部錄用以及政治協調與溝通等職能。同時,進一步明確“黨組的成員,由批準成立黨組的黨組織決定”,“黨組必須服從批準它成立的黨組織領導”,這就使黨組的地位更加明確,職能更加完善,設立和管理的體制更加理順。十六大黨章關于黨組的規定,十七、十八大黨章相沿未改。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也一直由委員長擔任,黨員副委員長和秘書長任黨組成員。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也一直保留至今,負責領導全國人大機關自身建設工作。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在中國共產黨五年立法規劃綱要之中,《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也在抓緊制定之中。隨著中國共產黨科學執政理念和依法治國方略的推進,人大黨組的運行機制將日益完善,也必將在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程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注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頁。
②《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頁。
③《人民日報》1978年12月24日,第一版。
④《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頁。
⑤《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頁。
⑥《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選編(1978-1996)》,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頁。
⑦《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5頁。
⑧《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