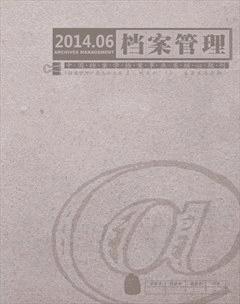公文不蓋印問題之我見
鄭彥離
摘 要:一般公文應在正文之后署發文機關名稱,并在其上加蓋印章。署會議名稱的一些公文無相應印章可蓋和受傳統規范格式限制的會議紀要無發文機關署名沒有蓋印,但仍受人信任。有特定發文機關標志的某些普發性公文因有蓋印不便而未蓋印,由于其普發,使需執行的機關均有,可據以辨明造假公文的真偽。傳真電報因其為事先聯系好后點對點發送,即使不蓋印,也不存在真實性受質疑問題。
關鍵詞:公文;蓋印;效力
張松祥在《檔案管理》2014年第3期發表《論〈條例〉中印章使用規定的不切性》(以下簡稱“張文”)一文,該文認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2012年4月16日聯合發布的《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中關于公文蓋印的規定存在不妥之處,提出“黨政機關公文蓋印應該成為一項鐵律”的觀點。筆者通觀該文,感覺其觀點有一定合理之處,但同時認為其這種“一律”的要求,存在不切合當今公文處理工作一些實際的問題,在此試述管見。
《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第9條規定:“公文中有發文機關署名的,應當加蓋發文機關印章,并與署名機關相符。有特定發文機關標志的普發性公文和電報可以不加蓋印章。”對這一規定,張文推斷出其意指的可不加蓋印章的三種情形:沒有發文機關署名的公文、有特定發文機關標志的普發性公文和電報。但他認為,該條例“把發文機關署名列為公文主體的要素之一”,“沒有規定‘不寫發文機關署名的例外情形,又何以有‘不寫發文機關署名的公文呢”?所以,該條例“規定‘沒有發文機關署名的公文不加蓋印章,缺乏政策規定的嚴謹性”。而“有特定發文機關標志的普發性公文”,其發文機關標志“畢竟是機關的‘標志,不是權力的‘象征,更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其功能作用與印章的功能作用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公文在加蓋印章后始能生效”。“如果一個公文不需要印章,那么這個公文的真實性會受到普遍質疑,在實際運用和指導工作實踐中的公眾信任度會大大降低”。至于電報,他認為“作為一種將電報信息通過專用交換線路以電信號的方式發送出去的通信方式,它不是傳送的紙質公文,而是傳送的電波信號,所以無法加蓋實體印章”。但“作為授受公文電報的雙方,雙方有明確的形成公務契約關系的信號頻段,以此來確定公文的授受關系,二者都要受到國家關于黨政機關公文處理法規的約束”。所以其雖無加蓋實體印章,仍可發揮法定效力。然而,“二十世紀后半期,隨著通訊科技的發展,利用電報手段來傳輸黨政機關公文基本絕跡”。現在,該條例“仍然做出電報不需要加蓋印章的規定,不僅是墨守成規,根本來說就是個多余”。
如果單看張文,會感覺其觀點相當合理,但若聯系前述條例的相關內容和我國現時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的一些實際,則會發覺其觀點存在偏頗。
首先,重點研討公文有無發文機關署名及其是否需要蓋印問題。
應先明確的是,這里所說的發文機關署名,是特指在公文正文后落款處署發文機關名稱,而不包括在公文正文前標題下署發文機關名稱,更不包括公文版頭上作為發文機關標志的發文機關名稱和公文主體部分作為標題組成部分標注的發文機關名稱。按照歷史慣例,在公文正文結束之后,于落款處署發文機關名稱,以示負責,同時在其上蓋印,以示鄭重并預防偽造。所以,前述條例中規定,“公文中有發文機關署名的,應當加蓋發文機關印章”。然而,該條例這樣規定,還有另外的原因,即公文正文后落款處有發文機關署名,不僅需要加蓋印章,而且還便利加蓋印章。有的公文,發文機關署名在正文之前標題之下,雖然從道理上說也需要加蓋印章,但在此處加蓋印章既不合慣例,也不美觀,所以就不在此處加蓋印章。如用決議文種發布的公文,通過決議的會議名稱通常用括號標注在標題之下,不加蓋印章。當然,通過決議的會議名稱也可以移至正文后落款處標注,然后在此上加蓋印章。不過,即便如此,很多決議可能還不蓋章。原因不是不需要蓋,而是無合適的章可蓋。這,牽涉到以會議名義發布的公文的署名問題。以會議名義發布的公文,通常署會議的名稱,但沒有與會議名稱相對應的印章,所以無法加蓋。也許有人提出可以根據會議名稱刻制相應印章,但是,印章制發,一般用于常設機構,會議往往一日或幾日就畢,為其刻制印章,既不合規定慣例,且使用次數少,變換快,有違印章制發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也許有人提出可用相應常設機構印章代蓋,就像某些單位的臨時機構發文,蓋單位印章加括號注明“代章”那樣。這也不合適。原因是單位成立的臨時機構,往往不是法定的權威機構,其發文由單位代蓋印章,如果其發文的有關內容事項出現問題或有問題處理不了,可由代蓋印章的單位做后盾處理。也就是說,代蓋印章要代承擔責任和可以承擔起責任。以會議名義發布公文的會議往往是權威會議,其發文由有關常設機構代為蓋章,既不嚴肅,代為蓋章的機構也承擔不了相應的責任。如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就不適宜由中共中央代蓋印章,否則既看起來不嚴肅,中共中央也承擔不了本應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承擔的責任。與會議相關以會議主席團名義發布的公告,發文機關署名是在公文正文后的落款處位置,但因會議主席團是隨會議設置的,不是常設機構,所以也無印章,并且同會議名義發布的決議一樣,不能借用相關常設機構代為蓋章。可能有人提出以會議或其主席團名義發布的公文不蓋印如何防偽問題,回答是這樣的:權威會議名義發布的決議、公告一般是公開的,公開即意味著幾乎人人皆知,人人可知,作偽則無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說,會議紀要也是一種以會議名義發布的公文。它的現行常規格式為版頭上通用公文發文機關標志位置標會議類型名稱和紀要二字,其下正中加括號標期號,再下左側標注編發會議紀要的機關名稱,右側標注成文日期。主體部分正文結尾之后無發文機關署名和成文日期。由于常規落款處無發文機關署名和成文日期標注,所以不便加蓋印章。如果硬要蓋印在無發文機關署名的常規公文落款處,則顯得很不嚴肅。也許有人提出,可否將會議紀要版頭上的編發機關名稱和成文日期移至主體部分正文之后的常規公文落款處,以便蓋印。這牽涉到會議紀要格式的改變問題,因其屬于長期約定俗成的一個規范事項,且會議紀要在日常工作中使用頻率很高,使用單位很廣,需要國家有關方面認真研究才能確定。即使將會議紀要版頭上的編發機關名稱移至主體部分正文之后的常規公文落款處,可能還有問題。因為會議紀要版頭上發文機關標志位置署的是單位會議名稱,而常規會議紀要在版頭上編發機關位置署的是單位辦公室名稱,不合常規公文的發文機關署名應與發文機關標志一致的慣例。有人可能提出,既然會議紀要不便蓋章,那怎樣預防偽造?筆者這樣回答:會議紀要除了有特定的版頭標志外,還發送給需執行的單位,若有人偽造去謀利,執行單位有依據可辨真偽。
綜前所述,公文需要發文機關署名,需要蓋印,絕大部分公文也按需有發文機關署名,并加蓋印章。但個別類型公文受傳統規范格式限制,無發文機關署名,不便蓋印,或發文機關署名特殊,無相應印章可蓋。然而雖然這些公文沒有蓋印,卻沒有影響其作用的發揮,并沒有多大被偽造的風險。正因為此,前述條例規定中才說,“公文中有發文機關署名的,應當加蓋發文機關印章”,而沒有說公文必須加蓋發文機關印章。使用“應當”一詞,正是考慮了全國不同類型公文格式與處理實際的復雜性,避免了極端。其實,不僅關于公文蓋印使用“應當”一詞是適當的,就是關于公文“發文機關署名”使用“有”一詞,聯系該條例的前面相關內容,也沒有張文說的“缺乏政策規定的嚴謹性”問題。因為前述條例第9條關于公文格式的組成是這樣規定的:“公文一般由份號、密級和保密期限、緊急程度、發文機關標志、發文字號、簽發人、標題、主送機關、正文、附件說明、發文機關署名、印章、附注、附件、抄送機關、印發機關和印發日期、頁碼等組成”。規定中用“一般由”說法,就意味著有非一般情況。事實也正是如此。公文不僅有本文說的沒有“發文機關署名”情況,也存在沒有其他某些項目的情況。上列19個項目中,除公文作為文章必須有標題、正文,因存在生效時間問題必須有成文日期外,其他項目都是因需要或可能而存在。如非保密公文往往不印“份號”,當然也沒有“密級和保密期限”。白頭文件無“發文機關標志”,只有一頁的公文不用標“頁碼”。
下面討論“有特定發文機關標志的普發性公文”“可以不加蓋印章”問題。
這里和前面所述的無“發文機關署名”不便蓋章與發文機關署名特殊無合適印章可蓋不同,而是有“發文機關署名”且有合適章可蓋卻允許不蓋。正像前引張文所說,發文機關標志“畢竟是機關的‘標志,不是權力的‘象征”,“其功能作用與印章的功能作用不可同日而語”,因之也不是公文可以不蓋章的理由。那么該類公文可以不蓋章的理由是什么呢?依筆者之見,在于其是“普發”。“普發”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其需執行的機關均有。而均有則意味著前述的若有人偽造去謀利,執行單位有依據可辨真偽。這就不得不討論一下印章的功能問題。張文說,印章是公文的效力標志,筆者贊同。但筆者同時認為,印章的第一功能是防偽。眾所周知,印章誕生于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最初用于郵遞印封。當時書寫載體主要為竹木,書信郵遞先用繩捆扎,再將打結處用泥封住蓋印,以防亂解偽造。之后官員上任被頒官印,作為權力象征。其實官員行文,署名即可生效,蓋印起證實、防偽作用。現代公文蓋印,表面看是權力象征,其實也首先是證實、防偽,否則就難以理解無蓋印的公文發揮現實效力了。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有特定發文機關標志的普發性公文”“可以不加蓋印章”的緣由了。如果還不能理解,再想想合同上蓋的騎縫章,檔案袋上蓋的密封章會幫助理解。
當然,筆者贊同張文的公文蓋印可提升受眾信任度觀點,因此也不主張凡“有特定發文機關標志的普發性公文”均不蓋章,現實工作中的絕大部分該類紙質公文也是蓋印才發送的。但是,某些單位的該類公文確實存在全部蓋印發送的困難。如中共中央辦公廳2004年12月31日發布的《中央文件發布、閱讀和管理工作暫行規定》第6條規定:“中央文件發布層次一般劃分為‘發至省軍級、‘發至市地師級和‘發至縣團級”。第9條規定:“中央文件的印發分別由中央辦公廳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辦公廳負責”。“發至省軍級以上的文件由中央辦公廳統一印發”,“發至市地師級以下的文件,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所需文件由中央辦公廳統一印發,各地區所需文件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辦公廳按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提供的文件樣本版式統一翻印,并在文件版記中注明翻印單位、日期和份數”。這里,“發至省軍級以上的文件”,加蓋印章沒有問題;“發至市地師級以下的文件”,“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所需文件”,加蓋印章也沒有問題。但“各地區所需文件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辦公廳按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提供的文件樣本版式統一翻印”的,卻無法蓋章。道理很簡單,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辦公廳不可能擁有中共中央的印章。可能有人有疑問,中央文件“發至市地師級以下的”,中央辦公廳為何不統一印發?筆者理解,理由有兩點:一是大多數市地師級以下單位的設置不由中央決定,全國每天可能都有變動,中央辦公廳難精確掌握各地的單位數量,不便確定印制和分發各地文件份數;二是全國各地“市地師級以下”單位數量多,由中央辦公廳統一印發中央文件,造成運輸和中央辦公廳分發文件麻煩。先以“發至市地師級”文件為例。各省一般有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協、省軍區、省紀委、省法院、省檢察院最少8個省部級單位,有100個左右的廳局等“市地師級”管理部門,有100所左右的“市地師級”高校,有數量不少的省屬“市地師級”新聞單位、研究機構、企業等。有十幾個地市,每個地市又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市軍分區、市紀委、市法院、市檢察院最少8個“市地師級”單位。總算起來,一個省需要中央“發至市地師級”文件一般為500份以上,全國累計則需約15000份。由于中央辦公廳不時需發這樣的文件,如其印發全由中央辦公廳負責,勢必需投入大量精力、人力于這種純事務性的工作,而影響對其他重要工作的投入。再以“發至縣團級”文件為例。各省省直“縣團級”單位暫且不數,各地市有50個左右的“縣團級”管理部門,有十來個縣區,每個縣區又有縣(區)委、人大、政府、政協、武裝部、紀委、法院、檢察院最少8個“縣團級”單位,加上市直為數不少的“縣團級”企事業單位,每地市累計有200個以上的“縣團級”單位,而每個省則累計有3000個左右的“縣團級”單位,全國則有約10萬個“縣團級”單位。加上“發至縣團級”的文件必然也要發給“市地師級”以上的單位,這些單位所需的中央文件若全由中央辦公廳印發,對中央辦公廳的正常工作沖擊更大。
正如張文所述,中共中央辦公廳1996年5月3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機關公文處理條例》也曾規定,“印制的有特定版頭的普發性公文”,可以不蓋印章。之所以如此,就是主要由于存在公文需要遠距離異地大量印發問題。如中共中央辦公廳1985年6月10日發布的《中央文件印發、閱讀和管理的辦法》中就有前引該單位2004年12月31日發布的那個文件中的類似規定。筆者這樣列舉,不在于說明這種做法時間長久,而在于強調這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現實,制定公文處理規定,不能忽略這種現實。可能有人認為筆者所舉只是中共中央文件印發一種情況,不具有普遍意義。但筆者要強調的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特殊政治地位,中共中央文件是在全國發送單位性質和地域最廣的公文,影響最普遍,制定公文處理規定,不能不考慮這種特殊現實。
最后簡單探討公務電報是否需要蓋印問題。前文引述張文的話,“二十世紀后半期,隨著通訊科技的發展,利用電報手段來傳輸黨政機關公文基本絕跡”。然而筆者知道的事實是,20世紀末葉,隨著電話普及我國普通家庭,私人到電信局拍發編碼電報基本絕跡;隨著傳真機在辦公領域推廣應用,黨政機關使用編碼拍發電報減少,使用傳真機傳發電報增多。近十幾年來,筆者就每年不時在單位開會,聽單位領導宣讀來自黨中央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及河南省有關黨政部門的傳真電報。用傳真機傳發電報與傳統發報機發送編碼電報相比,傳真機好操作,不用配譯電員那樣的專門技術人員。與發送普通紙質公文相比,減少了遠距離人工傳遞的麻煩。傳真機可根據需要加密或不加密。發送普通電文,不加密即可滿足需要。發送秘密電文,需設置加密,如再使用通訊專線,就更加安全。張文說,使用計算機網絡發送公文能滿足安全需要,那可能是指面對普通人,如果是面對計算機網絡高手,則難有安全保證。正由于此,各級黨政機關規定,不能通過互聯網傳送秘密公文。用傳真機發送電報,有的單位加蓋印章,但如收發雙方非均使用彩色傳真機,收方接到的傳真印文顯示的顏色就不是發報方蓋印的原色。有的單位不蓋印章,因系事先雙方聯系后點對點發送,收報方確信為對方所發,不存在真實性受到質疑問題,所以,《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規定,“電報可以不加蓋印章”。
(作者單位:中州大學 來稿日期:2014-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