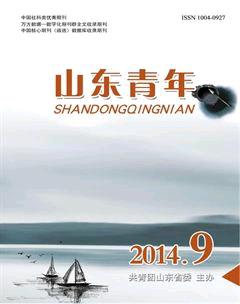中西兩種邏輯的對(duì)話
洪秀
摘要:文章借用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shí)”命題以及孔子的仁學(xué)思想為切入點(diǎn),獲得中西方邏輯對(duì)話的入場(chǎng)券。前者是理性主義倫理學(xué)的奠基者,其道德哲學(xué)蘊(yùn)含著一種求真的邏輯。而后者的倫理學(xué)思想是以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guān)系為核心,彰顯的是一種情理邏輯。當(dāng)今西方科學(xué)的發(fā)展以及中國(guó)社會(huì)的局勢(shì)都詮釋著兩種文化中的兩種不同的邏輯。
關(guān)鍵詞:求真邏輯;情理邏輯;美德;知識(shí);仁學(xué)
如今中西方文化比較話題相當(dāng)熱,各個(gè)學(xué)科都從自身角度出發(fā)進(jìn)行相關(guān)方面的論述。梁?jiǎn)⒊壬凇拔迨曛袊?guó)進(jìn)化概論”一文中提出如下觀點(diǎn):中國(guó)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過(guò)程是一個(gè)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進(jìn)化過(guò)程。該文對(duì)后世學(xué)者具有極大的啟發(fā)性。假設(shè)運(yùn)用梁?jiǎn)⒊壬睦碚搧?lái)分析中西方現(xiàn)狀,那么,文化的差異或者民族精神的差異才是中西方最實(shí)質(zhì)性的區(qū)分所在。很多學(xué)者如魯迅、費(fèi)孝通等人都試圖闡釋中國(guó)人及中國(guó)文化的精髓,間或批判其中的糟粕。本文嘗試著從一個(gè)微小的視點(diǎn)來(lái)探究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邏輯”一詞源于西方,它是指事情所應(yīng)遵循的規(guī)范、條理。據(jù)此意,我們可以借用這一概念來(lái)分析比較中西方的邏輯差異。而從當(dāng)今社會(huì)的紛繁復(fù)雜,我們可能無(wú)法清晰瞥見(jiàn)兩種文化蘊(yùn)涵的邏輯異同。那么,我們不妨回到雅斯貝爾斯所說(shuō)的“軸心時(shí)代”,通過(guò)西方圣賢蘇格拉底和中國(guó)圣人孔子之學(xué)說(shuō)來(lái)回溯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根源所在。兩位大師均為這兩種文化的鼻祖,塑造了兩種不同的民族性格。那么,下文通過(guò)對(duì)蘇格拉底和孔子主要哲學(xué)思想尤其是倫理學(xué)思想的論述來(lái)引出兩種不同的邏輯習(xí)慣,進(jìn)而解釋中國(guó)人和西方人認(rèn)識(shí)世界、理解社會(huì)的迥然不同的思維方式。
一、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shí)”及求真邏輯
在西方哲學(xué)史中,蘇格拉底是一位轉(zhuǎn)向式的人物。如果類比人們常賦予近代哲學(xué)“認(rèn)識(shí)論轉(zhuǎn)向”的桂冠,那么,蘇格拉底的哲學(xué)可冠以“倫理學(xué)轉(zhuǎn)向”之名。蘇格拉底是一種精神象征,如同近代哲學(xué)家斯賓諾莎,他們的偉大是一種哲學(xué)學(xué)說(shuō)與生活實(shí)踐的并行不悖。從天上回歸人間的古希臘哲學(xué),從此開(kāi)啟了一條美德倫理學(xué)的道路。
蘇格拉底出身于雅典民主制衰敗之際,日益腐朽的城邦、日漸式微的美德必定給他的心靈造成一種沖擊。而作為智者學(xué)派的一員,蘇格拉底同樣認(rèn)為早期古希臘哲學(xué)家所提出的宇宙觀都是建立在感覺(jué)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因而都是不可靠的。即便如此,什么是可靠的呢?蘇格拉底認(rèn)為從外在的宇宙萬(wàn)物出發(fā)無(wú)法推出一般性的東西或者說(shuō)可靠的知識(shí),那么,只有回歸人本身,從人的心靈出發(fā)才能得出不變的法則。蕓蕓眾生差異萬(wàn)千,但人之為人總有其共性,即心靈中的美德。它們不同于外在的自然界,后者變動(dòng)不居,前者永恒持久。美德才是真正絕對(duì)的東西,才是人們應(yīng)該追求的真理所在。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也依賴于心靈,因?yàn)樯系圪x予心靈最高的法則,這種最高法又是與萬(wàn)事萬(wàn)物相一致。因而,人只有先認(rèn)識(shí)到自身內(nèi)在的美德才能去認(rèn)識(shí)外在的自然界。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是一位道德哲學(xué)家,他的哲學(xué)主要闡述的是關(guān)涉心靈的美德問(wèn)題。
從詞的原意上來(lái)說(shuō),“美德”一詞并非單指人的德行。它最初意指盡顯人和物固有的本性[1],如馬的本性便是跑得快,耳朵的本性便是聽(tīng)得清楚。隨著人類社會(huì)的發(fā)展,人和物的界限越來(lái)越明朗。“美德”漸漸演變?yōu)槿说膶S忻~,包括勇敢、節(jié)制、正義等等。在此基礎(chǔ)上,蘇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識(shí)”命題,后世學(xué)者大都以此為據(jù),將其倫理學(xué)命名為理性主義倫理學(xué)。這一論點(diǎn)是蘇格拉底道德哲學(xué)的核心命題,體現(xiàn)了一種別樣的倫理學(xué)進(jìn)路。他將“善”與“真”等同起來(lái),求善便是求真。善是人的一種價(jià)值追求,真是一種事實(shí)判定。因而,蘇格拉底是將人的價(jià)值追求建立在真實(shí)可靠的知識(shí)理解的基礎(chǔ)上。[2]只有當(dāng)人們認(rèn)識(shí)了何為善,才能去行善。如果連善都不知為何物,那么即使做了善事還不如有意為惡。這樣的論述是令我們中國(guó)人驚訝的,在這里,知識(shí)成為一種準(zhǔn)則。而蘇格拉底正是憑此成為西方理性主義精神的奠基者。當(dāng)然,這里的“知識(shí)”是否是如今所說(shuō)的科學(xué)知識(shí),我不置可否。但據(jù)亞里士多德對(duì)這一命題的闡釋,他認(rèn)為這里的知識(shí)應(yīng)包括技藝,是一種廣義的知識(shí)。無(wú)論如何,知識(shí)是美德的前提,只有擁有最廣博的知識(shí)才會(huì)有最高尚的美德。
從上文可以看出,蘇格拉底追求的最高的美德即“善”是一個(gè)類概念。它并非指某一種具體的善行,而是一類事物或者行為的統(tǒng)稱。人所具有的善包括友愛(ài)、勇敢、智慧等都是普遍的概念。不同于普羅泰戈拉宣揚(yáng)的“人是萬(wàn)物的尺度”,蘇格拉底以論辯的形式引導(dǎo)人們?yōu)橐活愂挛锘蛘攥F(xiàn)象下定義。也就是說(shuō),人們并不是隨意約定世界上的萬(wàn)事萬(wàn)物,而是運(yùn)用所謂的“助產(chǎn)術(shù)”得出普遍的概念。這是憑借人的理智作出的判定,而并非感覺(jué)臆斷。因而,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shí)”這一命題,無(wú)論受到后世哲學(xué)家何種程度的批判,其中蘊(yùn)含的不同于前蘇格拉底時(shí)期哲學(xué)家的理性追求無(wú)愧為一種真正的創(chuàng)新和突破。這種理性主義倫理學(xué)彰顯的是一種真理的邏輯,和中國(guó)人常遵循的情理邏輯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論淵源。開(kāi)啟中國(guó)倫理之先河的孔子,在其仁學(xué)思想中對(duì)這種通感式邏輯進(jìn)行了有效的佐證。
二、孔子的仁學(xué)思想及情理邏輯
在中國(guó)思想史中,孔子學(xué)說(shuō)影響最為深遠(yuǎn)。他身處春秋末期,當(dāng)時(shí)禮崩樂(lè)壞,君不君、臣不臣,社會(huì)混亂。在這種社會(huì)環(huán)境大背景下,孔子提出了他的仁學(xué)思想。“仁”的概念在孔子之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孔子是第一個(gè)以“仁”來(lái)統(tǒng)攝其整個(gè)思想體系的倫理學(xué)家。許慎在《說(shuō)文解字》中將“仁”解釋為:仁,親也,從人從二。即二人之間的親愛(ài)之情、人與人之間的親愛(ài)關(guān)系就是仁,仁字本身的基本含義就是相親相愛(ài)。[3]
“仁”是孔子追求的道德理想,也是其道德哲學(xué)的精髓。在《論語(yǔ)》中有一百多處論及“仁”,可見(jiàn)其重要性。而究竟何為“仁”?孔子就其門(mén)下弟子各自資質(zhì)的差異作出了多種不同的解釋。《論語(yǔ)·里仁》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話: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mén)人問(wèn)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馮友蘭先生解讀這段話時(shí)指出,忠恕之道就是仁道。如上文所論述,“仁”就是指人與人的相互友愛(ài)關(guān)系。那么人何以表達(dá)這種相親相愛(ài)之情呢?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人們存在著很多種具體的辦法和行為,曾子便用“忠恕”二字概括之。“忠”和“恕”都從“心”。人心不偏不倚,沒(méi)有一己私心,這就是忠;待人如己,推己及人,這就是恕。孔子還將“仁”的否定意義表達(dá)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相比于蘇格拉底的“善”,孔子的“仁”更加注重道德修養(yǎng)。通過(guò)內(nèi)在的修持,以中庸之道行之。
在《論語(yǔ)·學(xué)而》中,有子說(shuō)道:“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4]“孝”是“仁”的根本。“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jǐn)而信,泛愛(ài)眾,而親仁。”[4]孔子從孝順父母、尊敬兄長(zhǎng)的骨肉親情出發(fā)外推到“泛愛(ài)眾”,這便是一條行仁的道路。在血緣關(guān)系的親情基礎(chǔ)之上,孔子教化啟發(fā)民眾。而孔子的道德規(guī)范不同于蘇格拉底的美德,具有深深的情感因素。“仁”體現(xiàn)的是一種情理邏輯。“仁”關(guān)涉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guān)系,強(qiáng)調(diào)情感體悟。它以情出發(fā),將心比心,達(dá)到一種通感式的道德境界。
“知”在孔子的倫理思想中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知”既不是人的特殊本質(zhì),也不是行仁的前提和依據(jù)。在《論語(yǔ)·里仁》中,有這樣一句話:“仁者安仁,知者利仁”[4]。聰明有智慧的人認(rèn)識(shí)到行仁對(duì)于其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是有利的,于是便施行仁德。“知”非體而為用,不是為知而知,是為用而知。而且這里的“知”也不同于蘇格拉底所說(shuō)的知識(shí),后者隸屬于理性的范疇,前者更多的是一種情感的通達(dá)。“知”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并非人類關(guān)于美德的概念、定義。在孔子那里,“知”的地位也不如“情”。在《論語(yǔ)·雍也》中,孔子說(shuō)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lè)之者。”[4]顯而易見(jiàn),情感的因素遠(yuǎn)遠(yuǎn)高于理性的因素。相比于蘇格拉底求真的理性精神,孔子更青睞于情感原則。
三、西方科學(xué)詮釋下的求真邏輯
求真或者說(shuō)理性是自蘇格拉底以來(lái)傳承至今的西方主流思想。“真”是事物的一種本然狀態(tài),而非應(yīng)然狀態(tài)。西方人追尋的便是事物自然而然的東西,是歸屬于其本身的東西。人只能盡自己理智之最大可能去認(rèn)識(shí)事物,而不能隨意界定事物。無(wú)論蘇格拉底倡導(dǎo)的美德倫理學(xué)是否已在21世紀(jì)復(fù)興,其中蘊(yùn)含的知識(shí)本位或者說(shuō)求真精神都是規(guī)范倫理學(xué)所無(wú)法匹敵的。我們不為目的、義務(wù)去行善。我們是依知識(shí)而行善。即如果我知道什么是善,那么,我必定會(huì)踐行。這是種理論化的倫理學(xué),也是種理想化的境界。西方先進(jìn)科學(xué)技術(shù)的誕生便是這種求真邏輯的最高附加值。只有了解了事物的本性,擁有了事物相關(guān)的知識(shí),我們才能有更豐富的想象力和更原始的創(chuàng)造力。
西方科學(xué)獨(dú)攬全雄,成為了“唯一的”科學(xué)。那么,依照科學(xué)知識(shí)社會(huì)學(xué)的某一派觀點(diǎn)來(lái)說(shuō),西方科學(xué)只是一種科學(xué),是世界上眾多不同的文化范式下孕育出的地方性科學(xué)。那么,西方科學(xué)為什么會(huì)成為世界主流,而其他的科學(xué)比如說(shuō)中國(guó)科學(xué)都淪為邊緣科學(xué)呢?學(xué)界認(rèn)為西方科學(xué)的核心在于實(shí)證,即理論與經(jīng)驗(yàn)相符合。西方科學(xué)或者說(shuō)科學(xué)成為事物本然性的探究。經(jīng)驗(yàn)成為檢驗(yàn)科學(xué)理論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只有準(zhǔn)確有效地作出預(yù)測(cè)的理論,才能稱之為科學(xué)。從中,我們不難看出西方科學(xué)便是求真邏輯的絕佳例證。這種求真精神是自蘇格拉底伊始,歷經(jīng)兩千多年的歷史洗禮,仍深深烙印在在西方文化中的民族精神。雖然現(xiàn)今的西方倫理學(xué)也已淪陷于功利主義、工具主義的框架下,但蘇格拉底開(kāi)創(chuàng)的求真精神卻體現(xiàn)在西方人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方方面面。李約瑟曾說(shuō)過(guò),科學(xué)是人類唯一進(jìn)步的事業(yè)。求真也成為人類至高無(wú)上的世界精神。
四、中國(guó)社會(huì)詮釋下的情理邏輯
中國(guó)社會(huì)形勢(shì)相對(duì)復(fù)雜,這一方面歸之于地理、氣候等客觀因素,另一方面得歸之于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與人有關(guān)的因素。從我們本篇文章的主旨大意來(lái)看,作為重要文化傳統(tǒng)的孔子仁學(xué)思想對(duì)我們中國(guó)國(guó)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與我們國(guó)家社會(huì)格局的形成更是息息相關(guān)。孔子認(rèn)為,人倫關(guān)系是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中最根本的關(guān)系,沒(méi)有人倫整個(gè)社會(huì)便無(wú)法延續(xù)。[6]人倫關(guān)系又以血緣關(guān)系為基礎(chǔ),因而,以孝悌為核心的道德體系成為維系整個(gè)宗法社會(huì)的根基。簡(jiǎn)而言之,“仁”的踐行是社會(huì)得以安定和諧的保障。
歷經(jīng)兩千多年的積淀,這樣一種仁學(xué)思想根深蒂固。其中彰顯出的情理邏輯更是融入了人們的日常行為中。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調(diào)節(jié)不是靠宗教或者法律的強(qiáng)制約束,而是靠道德或者情感的制衡。我們不苛求事物的本然姿態(tài),而去尋求事情的應(yīng)然狀態(tài)。我們不擅長(zhǎng)探究宇宙萬(wàn)物的生滅,而更傾向于道德實(shí)踐。我們并不以“知”為最高準(zhǔn)則,而是以“情”為核心理念。近些年來(lái),我國(guó)逐漸凸顯的種種社會(huì)問(wèn)題一定程度上歸咎于這樣一種情理邏輯。我們?nèi)狈ξ鞣绞降摹八稍瓌t”,很多社會(huì)問(wèn)題還是依靠人情關(guān)系的調(diào)節(jié)得以暫時(shí)規(guī)避,并沒(méi)有行之有效地解決。
五、結(jié)語(yǔ)
究竟是何種要素造就了現(xiàn)代人,是理性抑或情感?而理性高于情感嗎?這些問(wèn)題都源于西方文化帶給世界其他各個(gè)民族的生存危機(jī)。作為一種地方性文化,我們中國(guó)人應(yīng)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心態(tài)來(lái)迎接西方優(yōu)勢(shì)或者說(shuō)強(qiáng)勢(shì)文化呢?我認(rèn)為,中西方擁有不同的邏輯思維方式。時(shí)間年輪轉(zhuǎn)到21世紀(jì)的今天,無(wú)疑西方式的求真邏輯占了先機(jī)。“真”是對(duì)事物最細(xì)致的描述、最直接的轉(zhuǎn)譯。而我們的情理邏輯是對(duì)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提煉。如果說(shuō)理性精神的張揚(yáng)得益于歷史年輪的滾滾向前,那么情感因素應(yīng)被視為更原始更顯見(jiàn)的人類本能。內(nèi)在心靈的感通,確是人與人之間保持親密友愛(ài)關(guān)系的良方。
然而,無(wú)論是求真邏輯還是情理邏輯,二者本身都是客觀歷史過(guò)程的產(chǎn)物。我們只能說(shuō)西方人更注重求真,中國(guó)人更講情理。中西方并非絕對(duì)的不可貫通。如果對(duì)比蘇格拉底和孔子其人及學(xué)說(shuō),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有很多共通之處。他們的社會(huì)背景、歷史使命、道德追求、人生信念等都存在著相似點(diǎn)。“真”本身無(wú)所謂好與壞,可一旦涉及到人,便有了價(jià)值評(píng)判,情感因素?zé)o法忽略。傳統(tǒng)的情理邏輯也給現(xiàn)代中國(guó)社會(huì)拋擲了很沉重的包袱,孔子時(shí)代的人情關(guān)系也許早已不再純正。因而,兩種文化的會(huì)通、兩種邏輯思維方式的相互借鑒便顯得至關(guān)重要。
[參考文獻(xiàn)]
[1]李石.重溫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shí)”命題:反駁與辯解[J].道德與文明,2003(1):45.
[2]許娜,保偉.“美德即知識(shí)”的道德解讀[J].法制與社會(huì),2007:921.
[3]梁婭華,趙建.論中西傳統(tǒng)倫理思想的理性精神與情感因素——蘇格拉底與孔子倫理思想對(duì)比研究[J].黑龍江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9(8):26.
[4]楊伯峻.論語(yǔ)譯注[M].中華書(shū)局,2006.12.
[5]趙敦華.孔子的“仁”和蘇格拉底的“德”[J].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3(4):89.
[6]雷紅霞.孔子與蘇格拉底道德哲學(xué)的比較研究[J].武漢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0(3):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