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霧霾”如何突圍
鄭秋軼++覃柳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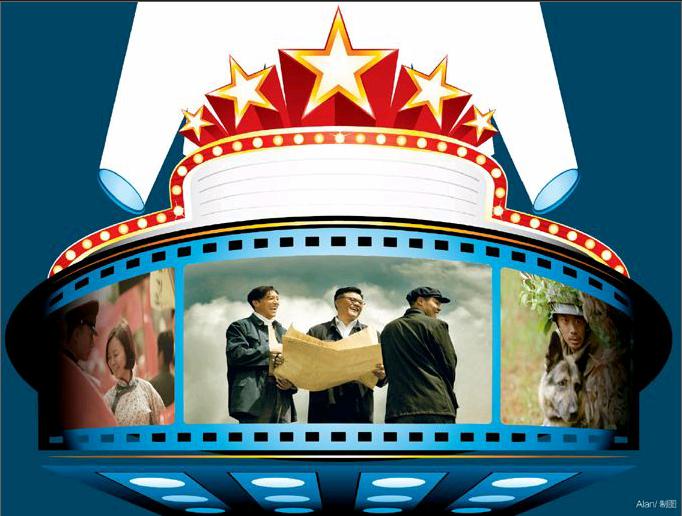


參加10月15日文藝工作座談會的一些人士感到,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的有些話講得比較重。
比如,價值觀缺失,什么勾當都敢做,沒有國家觀念、集體觀念、家庭觀念,不講對錯、不講美丑,渾渾噩噩,窮奢極欲,良莠不分,笑貧不笑娼,這樣的社會,人們的精神會淪落到什么程度?
同時,習近平也有一系列既傳統又創新的提法:從“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能被市場牽著鼻子走”到“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娛樂”,等等。
十八大以來,在全社會努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背景之下,習近平在此次座談會上對文藝界提出了嚴峻而急迫的要求。
正如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孫家正所說,其實談的很多問題都是老話題,但置身于新的境況之下,習總書記有新的表達。
又或者說,座談會希望解決文藝界一些持續未能攻克的難題。
有些人在砸主旋律這個牌子
習近平對文藝作品“叫好又叫座”的要求,令中國影協副主席王興東感受頗深。
這位《離開雷鋒的日子》《孔繁森》《蔣筑英》《建國大業》等主旋律影片的編劇對《瞭望東方周刊》說:“現在很多人一聽是主旋律就不看,以為是單純的宣傳片。網上水軍抵制,放都沒地方放,其實他們看都沒看。”
王興東說:“過去聽說‘五個一、精神文明建設還支持你,現在不愿投錢。有的領導公開說,不賺錢靠邊站。現在總書記說不做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染銅臭氣,我豁然開朗,我堅持的方向是正確的。”
他總結的“主旋律電影創作三點規律”是:尊重生活;尊重藝術,要引人入勝;尊重市場,人無我有、人有我轉。
“我寫許海峰、寫雷鋒、寫國旗設計者,就是循著這些規律。”在王興東看來,符合規律的主旋律影片是有人看的,“有些人急功近利,不認真,他們是在砸主旋律這個牌子,抄美國的片子韓國的橋段,有幾個深入生活了?”
他以自己的新作《黃克功案件》為例——描寫了1937年延安發生的一起干部逼婚、槍殺女學生的惡性案件,當事者最后被判處死刑。
2014年9月,這部影片在蘭州金雞百花電影節上放映,“老百姓踮起腳尖看”。“最高法院周強院長看了這個片子后,認為沖擊力很強,因為這是寫法制,寫平等民主,不是假大空。”王興東說。
“美國的片子經常講外星人侵略美國,美國人如何抵抗,還有像《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單》,都是他們的主旋律電影,但好看。”曾打造過《人間正道是滄桑》《康熙微服私訪記》《漢武大帝》《楊善洲》等經典影視作品的浙江天光地影影視公司董事長嚴從華對本刊記者說。
在10月15日的座談上,中國文聯副主席李雪健曾批評文藝圈的“怪現象”:爛片邊拍邊罵邊寫。
王興東認為這是教育不到位造成的。“現在有兩種作品,一種是雜耍,快餐;一種是酒,有余味。很多人跟風,分不清好壞,文藝作品是潛移默化的。”
“天天讓你吃肯德基,可能就習慣了。當然也跟投資方有關系,任何資金都希望盡快回籠,而且一個好的創作團隊不容易碰到。”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編劇蘭曉龍覺得,爛片受歡迎,既怪也不怪。“打個比方,一個書店五層樓,肯定有好書,但大部分是爛書,信息時代就是這個樣子。”
作為《士兵突擊》《我的團長我的團》的編劇,蘭曉龍的秘訣是:主動。“我是個方法論者,從我的職業感受出發,創意者如果足夠主動,是可以改變資本方向的。”
在他看來,文藝座談會更多是為一線文藝工作者開的。“有時候就要比資本想得多,讓他明白,原來事情還可以這樣做。”
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王洛勇也遇到過這類“怪現象”。他拍《焦裕祿》時,一個電視臺領導說,拍那破戲干啥?再拍國內沒人找你拍戲了。“我很震驚。我知道他沒有惡意,能理解他的提醒。因為長期以來,我們一切以數據說話,以收視率說話,使藝術家、決策者沒底了,在市場潮流中有點迷失。”
王洛勇是2012年作為“千人計劃”引進回上戲的。他說,美國的任何一個劇團和大學都有一個共識,即:人民就是市場,人民歡迎就是水平。
“那么為什么跟主流價值觀、優秀傳統相背離的作品會有市場呢?”他認為問題出在“人才培養的源頭”——教育。
他說,“我們的老師,會拿一個名牌包,一把奔馳車的鑰匙,不經意地甩在桌上,跟學生說,這個我是花6個小時掙來的,這個是我花了不到3個月掙來的。我們的老師在校園里開著路虎奔馳,已經把潛臺詞說出來了:看,我多牛!”
用當代話語回應當代話題
珠江影業董事長、中影南方院線總經理趙軍認為,總體來說中國影視業是在進步,并取得了3份成績單:在美國大片20年輪番進攻下,占住了50%的市場;完成了從大片到話題電影的轉型;涌現了一批優秀導演。
中國電影每年增長30%,高于中國經濟的增幅。“但中國電影還在探索階段,不能要求所有探索都成功,焦裕祿精神是時代需要,但要找到一個與市場和人民結合的辦法。”他說。
如何找到這個辦法?“很簡單,就事論事。”嚴從華說,“像《建國大業》就是走明星路線,但主旋律都按這個思路來拍,投資上實現不了。”
在細節上下功夫是辦法之一。嚴從華擔任制片人的重大題材電影《鄧小平登黃山》目前正處于后期制作中,該片試圖表現偉人平常的一面。
以往作品中的鄧小平,基本上處于戰爭年代,性格描述上大多以果斷為主,具有震撼人心的光環。而在這部劇中,鄧小平“是一個走向群眾的老人,他想了解群眾,只有如此才能感受群眾的生活,明白群眾的需求”。
嚴從華也很清楚這部戲的局限性,“主要觀眾是40多歲、喜歡看政治劇的,光在電影院上映不會有多大票房。年輕人熱衷美國大片,所以還要通過機關團體、學校營銷。”
這類重大題材劇還要注意拿捏好。“像張靈甫,應該說他是抗日英雄,但要是拍《紅日》《孟良崮》,那他就是對人民犯下了罪行的人物。”endprint
正如正在熱播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講的是國民黨反腐。“這個劇要是我拍,我要拍那個年代共產黨反腐。從20年代槍斃貪官肖佳碧,到解放以后槍斃天津的那兩個。共產黨不是一直在打擊腐敗嗎?”曾經策劃過同類題材劇集《人間正道是滄桑》的嚴從華說,“這個劇挺好看的,戲里大量還是共產黨,這是主流。”
文藝作品如何反映“陰暗面”,歷來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對此也有論及,“現實主義的精神和浪漫主義的情懷去關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好戰勝丑惡。”現在,對于“陰暗面”,不是要不要反映,而是該如何反映。
反映“陰暗面”還有一個尺度問題。王興東覺得這個話題并不敏感,“四中全會,主題就是依法治國,那就要依法治文藝,所以我提過多次分級制的問題,光有審查制度,文藝是不能繁榮的。”
對于審查,“其實是一個有彈性的東西,不是非要你去做狹義上的主旋律。”蘭曉龍說。
至于如何像美國大片那樣名利雙收,“我們現在就要研究這個問題。應該把精力放在研究文藝規律、研究市場上。”趙軍說。
蘭曉龍也不希望看到主旋律創作簡單地一擁而上。“我覺得所有一擁而上的東西都缺乏理解,希望能沉下去,做自己的事。”
“說到底,主旋律就是用當代的話語回應當代的話題,必須是正能量。”趙軍說。
文化上的霧霾更嚴重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王一川注意到,座談會上“人民”、“中國”、“中華”這樣的詞匯出現頻率相當高。
有些話在思想文化界已經被廣為傳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還有習近平在此次文藝座談會上講的“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
這樣的修辭頻率說明了什么?“說明非常關心中國精神傳播。對文藝批評提出了新的要求。”王一川說。
趙軍認為,要領會“中國精神”,必須厘清一個背景,即:巨大的時代差距。“現在與30多年前相比,變化翻天覆地,必須意識到‘巨大的時代差距7個字,否則就會陷入迷茫。”
蘭曉龍則認為愛國主義是應有之義,“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愛國者。”
他不介意別人說他是“愛國賊”,覺得在這個時代愛國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我的愛國來自于我看了很多近代史,國家遭遇的坎坷波折,讓我沒有安全感。”
這種不安全感表現在,“我會擔心我的女兒會在一個什么環境下長大。”
這也是他的創作動力之一。“實際上可以把我做的都叫做主旋律,我個人完全不排斥。好萊塢寫的是不是主旋律、愛國主義?我們需要向好萊塢甚至韓國學習,把一個國家好的東西和商業結合起來。”
在蘭曉龍看來,目前文化上的情況比霧霾嚴重,“因為信息的傳播速度比霧霾擴散更快。”
“其實這些年我擔心的不是影視上的霧霾,是整個文化上的霧霾。中國的壓力很大,比以前大,挺過去就有前途,那么必須有脊梁骨,就需要一種精神。當然,這種精神遇到商業環境是有些吃虧的,不像那些軟骨的、媚俗的那么容易。”
蘭曉龍自認是一個“比較物質的人”,會衡量工業、經濟的數據。“但我也喜歡讀史,發現真的需要民族精神,光是GDP沒用。”但這種精神究竟是什么,他覺得是一個“好大的問題”。
“其實是一種廣義的主旋律。我愿意用一個戲劇的邏輯來解釋,放在那里讓觀眾自己去看,不是強迫的,但是要讓人理解,至于能不能理解,看創作者的本事。”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