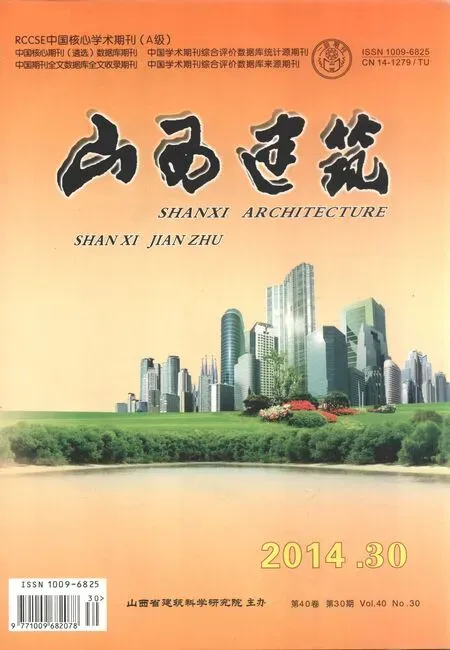高墩大跨連續剛構橋施工過程抗風舒適性分析★
段瑞芳 聶存慶 郝憲武
(1.陜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陜西 西安 710018;2.西安市交通運輸管理處,陜西西安 710065;3.長安大學橋梁所,陜西 西安 710064)
0 引言
采用懸臂澆筑的高墩大跨連續剛構橋,橋墩越高懸臂施工的穩定性越差,尤其當橋梁位于風力較大的山口時對風作用尤為敏感。本文將采用數值模擬方法分析結構懸臂施工過程工作人員的振動舒適性。
1 西北溝谷地形風場基本風速推算方法
在西部地區,多數橋址處地形復雜,而這些地區有的沒有設立氣象站,進而缺少橋址處的氣象實測資料,橋梁的設計風速就比較難以確定。但是在這些地區的基本風速“不受地形、地貌的影響”的特性依然保持不變。這就給山區溝谷地形的橋址的基本風速的確定帶來較大的困難。在這樣的情況下,就需要根據橋址附近的氣象站測得的風速資料,來推算橋址處的設計風速。橋梁設計風速推導流程圖見圖1。

圖1 橋梁設計風速推導流程圖
本文參考2009年徐洪濤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推導出的該處的橋梁結構設計基準風速的公式[5]。計算得出實例工程橋址處“虛擬氣象站”的基本風速為27.4 m/s。橋址處風速的平均地形修正系數a=1.15,本文依托工程的設計基準風速為:Ves=30.68 m/s。
2 結構懸臂施工過程工作人員振動舒適性分析
對于高墩大跨剛構橋在風振作用下的懸臂施工過程中施工人員的舒適性及安全性研究比較少見。本章就高墩大跨連續剛構橋在懸臂施工過程中,分別以墩高、懸臂長度、風速為參數,分析施工人員結構懸臂施工過程中,在動風荷載的作用下人員振動舒適性問題,并分別以加速度和Diekemann的舒適度指標K對結構的振動舒適度進行評價。
2.1 結構模型建立分析
本節利用有限元分析軟件midas/civil2010中的時程分析,對結構進行簡化的動力分析。溝谷地區的風環境分布比較復雜,高墩大跨連續剛構橋在其懸臂施工過程中,由于墩高高度、懸臂長度以及風速大小的不同,結構對作用在其上的風荷載的響應也不同。即將作用在橋梁結構上的風荷載簡化為類似的沖擊荷載。
本文選擇如圖2所示的荷載模型[9]作為實例工程的動風荷載模型,并將此風荷載以多周期形式反復加載在結構上。

圖2 簡化的動力荷載
且有:1/2×FM×t2=Fwh×t2。
其中,t1=10 s;t2=20 s;t3=25 s;FM為動力風荷載時程函數最大值;Fwh為根據橋址處結構抗風設計風速,計算得到的風荷載靜力值;t1為動力風荷載達到最大值FM的時間;t2為動力風荷載達到最小的時間;t3為動力風荷載作用一個周期的時間。
2.2 基于Diekemann舒適度指標K的舒適度評價
目前,歐洲大多國家分析結構振動對人體的影響時,多采用德國學者狄克曼Diekemann舒適度指標。其指標K的計算公式以及評定標準見表1,表2[8]。

表1 Diekemann指標K計算公式

表2 狄克曼指標K評定標準
結構分別在墩高h=30m,50m,70m,90m以及懸臂長度x=30m,50m,70m時的舒適度指標K計算,如表3所示。

表3 各參數下的Diekemann的舒適度指標K值
根據狄克曼舒適度指標K評定標準:計算舒適度指標K值基本小于10(見圖3)。即:結構上工作人員的舒適度在“能忍受短期振動”的范圍。

圖3 舒適度指標K值隨墩高變化趨勢圖
2.3 基于加速度指標的舒適度評價分析
由國內外的醫學、心理以及工程方面的專家多年的實驗研究結果得知:結構的振動頻率、加速度幅值以及振動持續時間是能否使人體感覺舒適的決定性的因素。其中振動持續時間決定于陣風自身的特性,而振動頻率調整又比較困難,比較容易掌握的是結構的加速度幅值。加速度對人體舒適性的影響如表4所示。

表4 加速度對人體舒適性的影響
1)在不同的墩高、懸臂長度下結構的振動分析。分別以不同的橋墩高度、懸臂長度為參數,對實例工程進行簡化的動風荷載時程分析,結構的豎向、橫向的加速度及位移變化曲線見圖4,圖5。

圖4 結構橫向及豎向加速度的變化趨勢

圖5 結構橫向及豎向位移的變化趨勢
2)在不同的風速作用下結構的振動分析。橋梁懸臂施工過程中的工作人員多暴露在外部環境中,沒有遮擋。根據風級、風速和征象對照表:在8級大風下“迎風步行感到阻力甚大”。同時,在JGJ 215-2010建筑施工升降機安裝、使用、拆卸安全技術規程中指出,塔吊、升降機安裝過程中的風速不得大于13 m/s,施工升降機頂部風速大于20 m/s時不得使用施工升降機。綜合可知在風速超過20 m/s時,大風對暴露在外部的人員的安全影響很大,尤其是處在高空作業的人員,在此風速下,結構需停止施工,工作人員盡快撤離到安全位置。
選用在前面推算得到的橋址處的抗風設計風速U1=30.68 m/s。根據基本風速等級得出:在六級風速下的最大風速U2=13.8 m/s以及八級最大風速U3=20.7m/s,在這三種風速下討論結構的橫、豎向加速度以及橫、豎向位移的變化。詳細結果見表5。

表5 不同風速對T形剛構的影響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顯示:結構在施工階段中,不同的橋墩高度、懸臂長度以及風速狀態,在動風荷載作用下,結構在最大懸臂處產生的橫向、豎向最大的加速度以及位移均不同:隨著懸臂長度及墩高的增加,結構的最大橫向、豎向加速度以及最大橫向、豎向位移呈現逐漸增大的趨勢,且結構的橫向加速度及位移影響比豎向的加速度及位移要更為明顯。
基于加速度為評價指標的分析結果:結構在簡化的動風荷載作用下最大的橫向加速度為(3.16E-2)m/s2,最大的豎向加速度為(7.62E-3)m/s2,根據加速度對人體舒適性的影響:二者均小于0.5%g,即針對實例工程的懸臂施工階段,結構的振動對工作人員的影響較小,沒有使人感到不適。
3 結語
通過采用簡化的動力風荷載計算結果顯示:隨著墩高的增高、懸臂長度的伸長以及風速的增大,結構的橫向、縱向加速度及豎向、橫向位移呈現增大的趨勢。且橫向的加速度和位移變化更顯著。結構的最大加速度小于人們能感受到的限值,即結構的振動對工作人員的影響較小。但Diekemann舒適度評價指標K值接近“能忍受短期振動”的限制,若出現大風天氣,建議停止施工,安排工作人員盡快離開施工現場。
[1]陳啟新.風速的“狹管效應”增速初探[J].山西水利科技,2002(2):62-64.
[2]楊德江.狹管效應與氣象災害[J].城市與減災,2010(4):41-43.
[3]JTG/T D60-01-2004,公路橋梁抗風規范[S].
[4]劉健新,李加武.中國西部地區橋梁風工程研究[J].建筑科學與工程學報,2005(4):32-39.
[5]徐洪濤.山區峽谷風特性參數及大跨度桁梁橋風致振動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學,2009.
[6]黃海彬.高墩大跨連續剛構橋極限承載力及抗風性能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2011.
[7]馬保林.高墩大跨連續剛構橋[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
[8]王進軍,李 杰.橋上行人對車橋振動的可容忍性(或舒適度)的判斷[J].鐵道建筑,2003(7):6-8.
[9]李衛華.大跨徑連續剛構橋梁施工控制仿真計算及抗風分析[D].武漢:武漢理工大學,2005.
[10]王 淳,徐曉波,田常兵.高墩大跨連續剛構橋抗風及P—Δ效應分析[J].中外公路,2009,1(29):1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