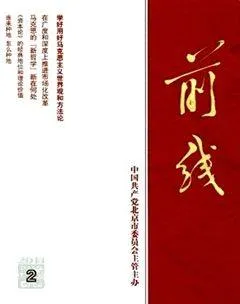黨創建前后開展學習的經驗
江大偉
縱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重視學習、善于學習一直是優良傳統。回溯歷史,這一優良傳統可以追溯到建黨時期。學習奠基、思想先行,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一大鮮明特色。
創立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團體為建黨作準備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讓在黑暗中苦苦求索中國出路和前途的先進分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有力推動了中國的有識之士去了解和接受指導俄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從而出現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在當時的北京大學,就聚集了一批這樣的先進知識分子。為了更好地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倡導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于1918年底在北大應運而生。“它既是中國最早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也為建黨作了重要準備。”李大釗所領導的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代表了中青年馬克思主義先進知識分子群,正是這種組織力量,成為此后爆發的五四運動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領導者和骨干力量。上海的建黨步驟,與李大釗在北京大學走的道路如出一轍。陳獨秀于1920年2月一到上海,就投入到一邊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組織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小組,一邊籌備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工作中。為開展建黨的準備工作,陳獨秀首先于1920年5月秘密組織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個研究會成為上海先進知識分子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陣地。研究會譯介了很多馬克思主義著作,其中被譽為社會主義運動“圣經”的《共產黨宣言》的中譯本,就是由該研究會成員陳望道翻譯并出版發行的。它對中國一代又一代先進分子的思想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為早期黨組織的組建以及后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此后,全國各地的共產主義者也都先后成立了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組織。正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馬克思主義學習團體的成立,凝聚了一批思想上傾向于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這批最早沐浴馬克思主義光輝的研究會成員,積極投身到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研究和宣傳中,并有一批精英成為后來中國革命的領導人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人才上的準備。
學習與建黨緊密結合,為黨的創建奠定組織基礎和思想基礎
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出現,加之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任務被提上了日程。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工作是從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入手,從翻譯、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入手,思想建黨為先,理論建黨為先。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建之道的一大特色。
在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立,加快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研究會成員邵力子曾回憶說:“我們一面覺得只做宣傳、研究工作是不夠的,有學習布爾什維克的作風,建立嚴密的組織的必要,同時也看到時機已經成熟,青年中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人也不少,應該組織起來。”1920年8月,由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時在日本)、楊明齋、李達8人發起,正式成立上海共產黨組織。上海共產黨組織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從其組成來看,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陳獨秀擔任書記。
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在李大釗的直接指導和籌劃之下成立起來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立,是李大釗把“對于馬克思派學說研究有興味的和愿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聯合起來的最初嘗試。據研究會成員朱務善說,從主要方面看,成立研究會“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結合,企圖建立共產黨”。經過籌劃準備,1920年10月,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正式成立,當時的名稱為“共產黨小組”。
此后,武漢、長沙、濟南等地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從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情況來看,幾乎都是在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或者相類似的學習團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其成員主要來自研究會和進步團體的中堅分子,都是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作為建黨的第一步,建黨是和學習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黨創立后著重加強思想建設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十分注重思想建黨。在黨初創時期,黨員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普遍不高,對馬克思主義還缺乏比較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尤其是受到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許多黨員的思想認識很大程度上模糊不清。這也是后來黨組織內部有些成員發生分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在黨成立以后,迫切需要提高全體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以便加強團結,提高全黨的理論素養。
黨成立后十分重視理論刊物的出版發行工作。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就對刊物出版的原則性及刊登內容的方向性作了明確規定。一大后,黨中央把原有的《新青年》雜志和《共產黨》月刊作為黨的理論刊物繼續出版,并且內容更加充實、豐富。1922年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不久,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了自己的政治機關報——《向導》周報。這份刊物有力地宣傳了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在革命斗爭中起到了重要的輿論宣傳和思想指導作用。
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普遍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所能接觸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十分有限。所以,在黨成立以后,組織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成為一項重要任務。1921年11月,陳獨秀即以中央局書記的名義簽署并向全國黨組織發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這是中央領導機構成立后下達的第一份文件。通告提出了“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于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為了能夠更好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出版發行,黨的一大后不久,即1921年9月1日,中央局在上海秘密創辦了人民出版社,由時任中央宣傳部主任的李達負責。在創辦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先后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列寧的《勞農會之建設》等著作以及“共產主義叢書”五種。在這些著作中,除《共產黨宣言》是重印陳望道的譯本以外,其余都是首次以單行本出版的新譯本。這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出版,為初創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寶貴的精神食糧,“對思想上有很大的影響”,成為許多共產主義者的啟蒙讀本,提高了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對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也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黨成立初期對于理論教育和宣傳工作的指示與活動,充分表明在黨的建設中,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裝全黨,提高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進而擴大共產黨的影響,是黨始終著重重視與強調的。
向實踐學習,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
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中,高度關注社會現實,注重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五四運動爆發后,尤其是上海工人階級的罷工斗爭,充分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進一步使中國的先進分子認識到,只有到工人中去宣傳、發動,走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道路,中國的革命才能成功。鄧中夏領導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多次來到北京長辛店的鐵路工廠進行調查,了解實際情況,并在工人中間積極進行革命宣傳。為此,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積極創辦了各種勞動補習學校。北京早期黨組織在長辛店成立了勞動補習學校,上海的早期共產黨組織在小沙渡創辦了工人半日學校,其他地方的共產黨組織也相繼創辦了補習學校、工人夜校、識字班等。通過這種學習組織,教員們在教授工人文化知識,提高文化程度的同時,也積極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普及和宣傳活動,以啟迪工人們的覺悟。這種組織培養了一批工人中的先進分子,成為發動工人、開展工人運動的基地,為工會組織的成立打下了基礎。
在努力與工人建立密切聯系的同時,黨也十分關注農民的問題。為了啟迪農民的覺悟,早期共產黨人開始深入到農村中進行革命宣傳。為了培養農民運動的骨干,經共產黨人提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抽調農運骨干進行理論學習和教育。從1924年7月起,在廣州先后由共產黨人澎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舉辦了六屆。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影響和帶動下,其他地方也紛紛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和農訓班。據統計,廣東、廣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陜西、福建等省共辦了40多個農民運動講習所和農訓班。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后,在武昌又創辦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由毛澤東主持,全校共有學生700多人。農講所十分重視對學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選聘了一批著名的共產黨人和左派國民黨人來給學員講課。通過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了一大批既具有一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又能開展宣傳、組織農民運動的骨干分子,極大地推動了農民運動的發展。
此外,當時的早期共產主義者中也有人親身赴俄,以求得“實際的結論”、“真實的智識”。瞿秋白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他于1920年10月從北京啟程,輾轉50多天,于1921年1月抵達莫斯科。此后在蘇俄的兩年時間里,他深入考察了蘇俄的社會生活,訪問了工廠、農村、學校、機關,還擔任東方勞動大學教員,參加蘇俄黨和共產國際的會議,并幾次得到列寧的當面教導。他以親身的經歷以及所接觸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對蘇維埃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報道,寫了數十篇政治通訊。同時,他還堅持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對革命理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后來,他把這段經歷寫成了兩本散文雜記《餓鄉紀程》《赤都心史》,真實地向國人介紹蘇俄革命后的現狀,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正如他所說:“只有實際生活中可以學習,只有實際生活能教訓人,只有實際生活能產生出社會思想”,也正是通過到蘇俄的實地考察活動使瞿秋白更快地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決心“為共產主義之人間化”奮斗終生。
以上種種充分表明,無論是共產黨的早期組織還是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后,都始終注意在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走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正如毛澤東所說,理論“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當然由于時代發展和理論認識的局限,早期的共產黨人對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認識還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但無論怎樣,早期共產黨人所進行的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這種開創意義的偉大探索是不容否定的,為后來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作者單位: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
責任編輯:鄭 建